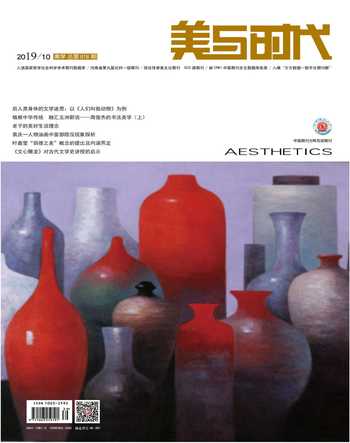身体:当代书法美学的一个新议题

摘 要: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当代书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被凸显了出来,即身体。其中一个最为引人关注的身体现象要数网络上一些热传的书法创作视频,其中夸张的身体动作及其表演性,曾引起书法界以及众多网民的热议。但批评界对书法中与身体相关的问题仍缺乏深入、全面的思考。书法的身体维度是指身体以体验、意象、表现三种方式在书法实践中的呈现。通过对书法身体维度的思考,对书法作品及具有身体现象的创作实践的总体批评应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其一便是这种身体现象对表达时代精神、抒发个人“情性”“哀乐”是否有助益;其二便是作品本身的优劣;其三便是作品的生成与身体之间的主次关系以及和谐程度。
关键词:身体;书法创作;书法美学;表演性美学
一、 身体凸显的背景:书法美学从美的本质到审美活动
书法美学在我国学术界讨论得比较早,其基本与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相一致。简单来说,20世纪30至50年代,西方美学著作广泛的译介引进阶段基本结束,宗白华等老一辈美学家开启了中国书法美学研究成体系、重逻辑、去功利的现代之路。60、70年代,书法受当时现实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以及机械的唯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进入了沉寂期。随之而来的是,80年代书法美学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书法美学大讨论将人们对书法美的认识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90年代,中国书法进入到了反思时期,着重对书法美学大讨论进行评述与再思考。随后,学者们不再围绕着书法美的本质打转,以金开诚、邱振中、郑晓华、丛文俊、王岳川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书法美的研究呈现出了语言和文化转向的特点。进入21世纪,书法美学再度遭受冷落,姜寿田将这近20年呈现出的史料考据片面繁盛大有取代书法理论研究全部之势总结为:“在书学研究中,以国粹主义的心态,沉迷乾嘉路径,排斥抵制西学也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整个人文学术潮流背道而驰。而即使将其衡诸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背景审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观念上的自闭狭隘和倒退。”[1]
当然,短短数语难以详尽描述几十年来中国书法美学的发展历程。但是从大概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十年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一)成体系、重逻辑、去功利的现代之路,已经成为当代书法美学研究努力的方向,这一点基本已成共识,为书法当代学科建设、有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对书法美的本质进行的大讨论是在中西美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不但使书法巩固了其独立的审美地位,而且也使得人们对书法美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下书法美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一)当代书法理论的研究,正如姜寿田所言,史料考据片面繁盛。书法美学的研究遭到冷落,书法美学研究又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特点,即在文化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之下讨论书法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等。但是,在文化层面讨论书法是不能取代书法美学的,这存在着使书法陷入“国粹主义”窠臼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书法不仅仅是东方文化的构建之物,书法自身的艺术特征势必需要回到中西美学的大背景下来揭示。(二)对书法美的本质讨论是美学界对于美的本质大讨论的延伸。书法美的本质大讨论最终在实践美学的调和中沉寂了下来。那么,除了书法美的本质,还有哪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关注呢?我们认为是审美活动。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学界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就具备了“从本体论的基础研究转向了以审美现象为基础的研究”的特点。其实,审美现象和本体论的基础研究就是美学的两翼——经验与逻辑。正如刘成纪所言:“就美学而言,其关注对象起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这使美学研究始终保持与时代同步的现场感;一是由固有理论推导出的问题,这使美学研究在与传统的接续中获得历史身份。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逻辑的。成熟的理论往往是将经验现象赋予逻辑的形式,用逻辑形式为经验建立秩序。”[2]那么,我们可以说书法美的本质和书法的审美活动二者也是这样的关系,前者注重思辨试图寻找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首先要到书法本体中寻找,因此这一阶段对书法美多有表情性、象形性的争论;后者便是关注审美经验的存在和发展,即不但要关注作品,还要关注主体的审美体验,这为书法美学中身体的出场提供了可能。
二、 当代书法中身体的出场
一旦将目光从书法美的本质转向了书法的审美活动,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在这样的活动中展开了自身。可以说身体在任何艺术中都是审美活动最基础的承担者。“身体最直接的审美表现是在各种形态的艺术之中。有些艺术样式本身就是身体的直接呈现,如人体雕塑和绘画等;有些艺术样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身体的运动,如舞蹈、杂技、戏剧、唱歌、电影、电视等;有些艺术样式虽然既不是身体的直接呈现,也不是借助身体的运动,但也描述和表达身体的活动和感觉,如文学和音乐等。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种艺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关涉人的身体的。没有对于身体的刻画,也就没有了关于人的艺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身体自身的揭示。”[3]所以,“从身体看艺术”成为美学界一个可能的新议题,这有别于过去受西方意识哲学影响,将艺术完全看作是精神性的,歧视身体在艺术中的作用。
身体,这一范畴在书法美学中略显陌生,这主要还是因为书法中的身体是隐晦的,传统书法美学中也没有专门对身体的深刻讨论(这与中国古代身心合一的整体的身体观有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身体不重要。对书法中身体的忽视,将会导致我们对于一些当代书法现象中的身体问题失语。例如,随着媒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和平台可以自由地发布书法家现场书写的视频,以及对书法教学进行网络直播。使得我们从过去面对作品的欣赏范式丰富成为面对整个创作过程的欣赏范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其实隐含着一种变化:过去书法欣赏的意向性只是由作品想象书写动作的单向还原,现在对书法的欣赏可以通过视频及直播将书写动作和作品生成过程同时呈现,这样的书法可谓更加完整,使得整个审美活动更具有现场感,而这种现场感的承担者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身体。如果说身体的出场对于书法传播、教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情况要相对复杂得多,即书法创作中夸张的身体动作在网络传播中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比如某些当代名家的“吼书”“射墨”“盲书”等视频以及一些“江湖大师”的夸张创作视频都在网络上红极一时。我们知道这些视频不仅仅在书法界内部传播,也曾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其实这些网民的关注更多指向了创作过程中夸张的身体动作所带来的娱乐效果。那么,书法美学对此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当下很多声音单单通过对作品的品评来判断其价值和意义,例如将其作品归结为丑书,得出或褒或贬的结论。但视野狭隘地禁锢于作品所得到的结论是无法解释和批评其中的身体现象的。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一现象的品评必须打开视野,不仅仅关注作品還要关注已经出场的身体,并且还要在书法美学、艺术美学等多个层面做出判断,不能不加思索地片面推崇或抨击,否则只会带来更多的误解和误导。除此之外,身体还以另一种面貌出场并值得关注。中国美术学院博导王冬龄教授曾在其现代书法中多次引入身体这一审美对象,其将书法书写在人体画册图片上或在书法创作表演时引入舞者等,以期使得身体的形式与书法的形式形成对话,可见,书法中身体的出场是多样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书法美学对于身体的关注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实践已经抵达,书法美学却鲜有涉及的领域,所以身体是当代书法美学亟待思考的新议题。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三、 书法美学中身体的三种类型
在当代美学界,身体美学已然成为显学。诸多身体美学的文章对于考察当代书法美学中的身体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中,方英敏《什么是身体美学——基于身体美学定义的批判和发展性考察》一文认为:当代身体美学这一大概念至少有三种话语或者说分支。第一种便是人体美学,人体美学主要是对身体的外在形式(主要指裸体)作为对象进行审美研究形成的话语。第二种便是消费文化中的美体之学,即当代大众在消费文化的诱导、教唆下采用从物质到技术的一切手段形塑身体外观的审美实践。美容美体、整形、服饰、健身、广告甚至暴力、色情的身体实践都属于这一美体之学的范畴。最后是培养、改良身体意识的身体感性学。这是指舒斯特曼对身体美学的定义。“舒斯特曼的身体感性学实质是关于身体的感受之学,探讨的是‘身体本身的内在感知与意识能力。”[4]18方文梳理的三种身体美学的概念其实涉及到的是两种身体。一种是身体的外观;一种是身体的体验。而这两种身体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张力,正如方英敏在文中所说:“对于现实个体身体的外观与体验来说,视二者间的统一性大于对立面则是现实的、可能的,否则,他要么意味着个体自身的分裂,要么就是病态。”[4]21“总体而言(极端、个案情形除外)在现实身体审美实践中个体身体的外观与体验是统一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审美事实。”[4]2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方文试图通过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将这三种话语和两种身体统一起来。经过论证和梳理,他认为所谓身体美学就是人类以身体美的塑造、欣赏和展现为中心的审美实践。
方文的贡献是明显的,其确定的身体美学之内涵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匡正这样的错误——将身体的外观或者体验,其中的一个分支看作是身体美学的全部。另一方面,从审美实践出发,能够很好地将身体的体验和外观统一起来,使得身体美学内部形成有机的整体。但是,这样的理论体系(身体美塑造论、身体美欣赏论、身体美展现论)并不能直接地套用到书法中,这是因为身体美学必须是围绕着身体美而展开的。而书法要展现的中心是艺术美而非身体美,我们要考察的是在书法审美实践中,身体所承担的角色。但这并非意味着方文的体系对于书法身体维度的理论构建是无用,我们可以借鉴这样的结构来对书法进行一番围绕身体的考察。首先从书法中对身体美的欣赏来看,对书法的欣赏与对身体外形的欣赏似乎有着云壤之别。但是,“文字的创制方式只能是‘观‘鸟迹或‘鸟兽之迹时那‘仰观俯察的姿势。‘仰观俯察,这种意味深远的造字姿势,对书法起了关键的影响。”[5]可见,由于书法或者说文字始创之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方式,已经将身体的意象(外形、节奏、功能等)植入到了书法、汉字的最深沉的意味当中。另外,对于人而言,身体是先人最熟悉的对象。不但熟悉身体的外观,更熟悉各个身体部分的功能。因此,由身体推及自然、宇宙万物,山具有了山口、山腰、山脊,壶有壶嘴、壶身等。与此同时,汉代人们逐渐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身体的差异性以及人的外形与内在品格的统一性,这也就使得骨相法逐渐繁盛,并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官方的人才荐举制度中。由此,对身体更为丰富的认识,使得身体的范式进入到了艺术领域,书法也不例外。到了魏晋时期,对书法的品评,肥瘦、筋骨等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评价标准。因此,对书法的欣賞其实潜在地包含着对身体意象的匀称、和谐等方面的欣赏。正因为如此,书法中这一类型的身体维度,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体意象论。其次,方英敏文章中所谓的身体美塑造论即体验论,一方面是指对身体外形的塑造;另一方面,是指对身体意识的塑造。前者一般是指传统文化背景下习书对人的身体美的补充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在这里塑造指向了对“作为感觉的身体”的身体意识的塑造,这里身体承担了体验主体的角色。身体参与到了书法美的构建当中,使得书法美建立在最现实、最感性的身体体验的基础之上。这包含了对“公孙大娘舞剑”“担夫争道”“锥画沙”等命题广义的身体体验。也包括叶秀山所言的欣赏体验:“‘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一下,要知道‘什么是书法,只有亲自去‘看作品。一切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都不能代替你亲自去‘欣赏艺术作品。”当然,书法家的体验更重要的还有“挥运之时”的书写体验,因此,书法的这一类型的身体维度我们称之为体验论。最后,便是展现论,这指向了作为感性活动的身体,这在身体美学中包含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仪态以及艺术中的身体表演。很显然,书法并不是身体必要出场的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在书法表现无足轻重。书法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身体的参与。“字形要适应人书写时的生理条件,其中主要是手的运动生理。适合手的书写条件,写起来才顺畅、才迅速、才美观。正因为如此,人们是根据书写时的生理要求去改造字的。从原始的图画文字起,字形就在书写的生理要求下不断接受改造。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字不断由描绘客观外物的线条变为书写方便的类型化线条;不断由曲线改为直线,乃至于把直线变为流线,这一改造过程不断变易着字的外貌。汉字由大篆而小篆,由篆书而隶书,由隶书而楷书,以及从隶书与楷书演变出来的行书、草书,都是有书写条件参与的,都是部分地或主要地由书写生理决定的。”[6]可见,书写生理正是遵守着身体现实给予的规定性(自然性的身体),而对书法技法的练习便是对书写生理超越的活动,即文化性身体的构建,二者之间的张力在书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感性活动的具有文化、自然二重性的身体及其具有表现性的动作,对赋予书法具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功不可没。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身体维度指向了书法实践中具有表现性的动作,对于这一类型的身体维度我们称之为表现论。
综上所述,身体问题在书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跨越或者无视书法中的身体问题,都会使书法片面化:存在方式上或将完整的审美活动完全被狭隘地等同于对书法作品的欣赏,审美类型上或将之完全局限于艺术美,从而造成对书法中一些问题的失语。因此,关注书法的身体维度是有意义的,明确其所指更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认为:书法的身体维度就是指身体以体验、意象、表现三种方式在书法实践中的呈现(如下表)。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四、 对当代书法中身体现象的反思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身体在书法艺术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体验论、意象论和表现论三者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书法中的身体现象。我们能够知觉到,随着当代书法艺术以及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书法中身体的维度逐渐凸显了出来,特别是表现论中的身体。这一身体在当代指向了书法创作中出现的身体,其身体动作与书法作品的生成是同步的,身体夸张的动作、吼叫成为了作品生成过程中的一部分。这种身体现象十分吸引眼球,且在当代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我们将对这种现象展开分析,试图确立这一身体现象在书法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由此判断其自身的意义及价值。
对这一现象的解读,诸多书家往往要到张旭、怀素那里去寻找合法性。我们知道,张旭、怀素书法的表演性曾经引起过当时诸多诗人的赞誉,但也曾受到过苏轼的诟病,指责其有炫技的成分:“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这是因为,这种身体表演性的发生是诸多时代因素耦合在一起所带来的,脱离了那个时代的背景便会显得突兀和做作。“当时的大诗人如高适、李白、杜甫与张旭等有交往,除了因大草书家如张旭、怀素书写时的表演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艺术风格张扬了时代精神,而诗人所关注的也往往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7]表演性的身体在唐代其价值正是时代精神所赋予的,这一时期是人的“情性”与书法美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在张旭、怀素之前,书家们热切地希望找到更为狂逸、自由的书法形式来沟通、揭示和表达“情性”,而这一理想和目标在张旭和怀素那里终于达成了,身体的表演性也就成为了沟通“情性”和书法美的渠道。这种表演性是“情性”外化的结果,而这种“情性”正是在这种表现性的动作中获得了形式,又更进一步地被注入到了狂逸、新奇、师心的狂草之中。可见,这种身体的表演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激发出来的。因而,随着宋人将文人的情感体验、价值观、世界观等注入到书法之中,书法的文化内涵大大增加,宋人不再满足在形式中寻找书法的价值,而要到形式之外去寻找,对韵、意、趣以及萧散简远的追求便是这一時期书家审美趣尚的写照,这使得身体表演性这种外在形式相形见绌,从而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苏轼、米芾要对张颠醉素恶语相向;另一方面,目光从时代背景转移到个体创作实践上,提及书法的表现性动作我们往往会提及姜白石的一段书论:“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可见,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是能够在具有鉴赏能力的欣赏者那里被还原为表现性动作的,这无疑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在书法传统中身体表演的合法性是具有条件的,即身体的表现性与作品之间的高度和谐,如若二者并不和谐统一,那么这种身体的表演性便是多余和没有价值的;并且两者之间书法作品才是主导力量,再精彩的身体表演最终完成的也是一幅低劣的作品,那么这种创作无疑也是失败的。过分强调身体而忽视作品或者身体与作品之间的不和谐都会导致书法本身价值的贬损。因此,在看待当代书法中的身体表演现象时,我们至少可以从传统中得到两条原则:一、从边界上看:书法必须是用毛笔书写汉字;二、从等级序列上看,创作必须以作品为主导,身体表演不能逾越作品之上,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随之,对书法作品及具有身体的表演性的创作实践的总体批评也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其一便是这种身体性的表演对表达时代精神、抒发个人“情性”是否有助益;其二便是作品本身的优劣;其三便是作品的生成与身体表演性之间的主次关系以及和谐程度。
那么,以非毛笔的工具进行所谓的“书写”或者以毛笔书写非汉字,甚至为突出身体的表演性而损害书法作品本身价值的艺术实践,都难以得到传统书法美学的支持。虽然这样的现象在书法美学中不能找到其合法性的根据,但是其在艺术这一大领域下还是具有合法性的可能的,这种合法性不但来自于美学的自由本质还来自于艺术家的个人审美理想的达成。因此,对于当代书法中种种身体的出场,我们应该借助以上的理论判断出,哪些是具有传统书法合法性的,而哪些是突破了书法的合法性的,突破了书法合法性的“表演”我们只能将之看作是利用书法创作这一形式而进行的“行为艺术”。通过以上的判断和批评原则,来捍卫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和传统、守卫书法的界限和底线。
参考文献:
[1]姜寿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转型与中西学碰撞融合背景下的现当代书学[J].中国书法,2016(6):30-36.
[2]刘成纪.身体美学的一个当代案例[J].中州学刊,2005(3):247-248.
[3]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J].中州学刊,2005(3):241-243.
[4]方英敏.什么是身体美学——基于身体美学定义的批判与发展性考察[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6-25.
[5]丘新巧.姿势的诗学:日常书写与书法的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78.
[6]王凤阳.汉字学: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8:37.
[7]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62.
作者简介:姜文,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美学。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