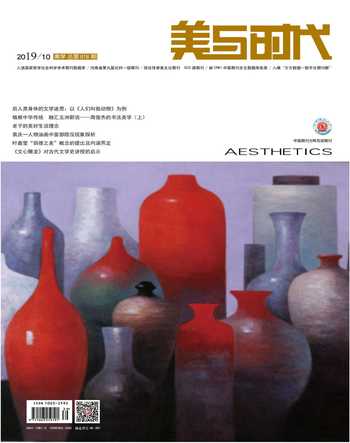后人类身体的文学迷思:以《人们叫我动物》为例
江玉琴 欧宇龙
摘 要:进入后人类时代以来,身体成为后人类研究的核心,既基于身体能最突出地反映科技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新境况,人机合一、人工智能等研究都在挑战人之为人的根本;也基于后人类身体变异而产生对人类本质主义的质询,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与生物科技的发展导致身体变异,并生成新的思维范式,后人类概念和后人类主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认知结构,身体重新回归身心一元体系。文学叙事如《人们叫我动物》以身体的再现与表现构建后人类主体间性。身体成为后人类文学叙事的中心,身体叙事再度检阅创伤与同情在后人类主体中的构建作用。后人类身体建构推动人类积极面对挑战,实现新的人文学科规划,引领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后人类未来。
关键词:后人类身体;人们叫我动物;创伤记忆;同情;后人文主义
一、后人类境况中的人类身体变异与危机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后人类的时代①。人类身体发生变异甚至产生与机器的重组,人类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观念、人类中心主义建构与所有他者的二元观念受到质疑与消解。这也是学者福山深感不安的地方,因为“当前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1]。福山在此特别强调人性的独特性,认为人性与宗教共同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在生物科技的冲击下甚至值得动用国家权力來加以保护。福山显然预见到了科技发展的后果,人类肉身正在遭到侵蚀和改变,人类外在世界正在走向巨大革新。但他并未在意身体本身的作用,而只是寄希望于人类的心灵认知这一自由人本主义所认为的独特性,力图持续稳固人类居于世界主宰的核心地位以化解这场危机。这显得过于理想化,忽略了人类本体论与存在论本身就已经在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冲击下所产生的动态发展。这也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讨论人类、后人类与后人类主义的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在这种后人类境况中,身体研究成为讨论的核心。
(一)作为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身体最为突出地反映了人类面临的新境况
凯瑟琳·海勒考察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技术发展成果发现,从图灵测试开始的信息化处理到莫拉维克的人—机信息流联结概念、人类本质被看作信息流,人机合一已经成为当前人们对生物科技与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大胆预测,彻底颠覆了人类原有的哲学与文化观念。海勒强调,无论机械人是否和人类一样可以拥有自主思想和自己的情感,但这里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人类肉身所承载的人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海勒将之称为“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如果人的身体并不具备独一无二性,当技术推动人的身体与以处理信息流为基础的机器联结在一起时,人与机器/技术的身份就交织在一起,人类主体也就产生出新的阐释。因此海勒提出,“后人类”就是人类肉身与机器界面融合,无论如何理解人类,人类都已经进入到后人类时代[2]4-5。关于这一未来景象,哈拉维用赛博格(cyborg)来指称,“赛博格就是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它是社会现实的创造物,也是虚构的创造物。社会现实存在活生生的社会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构,也是一种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虚构”[3]4-5。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科学家试图证明,在未来,智能机器将取代人类,人工生命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式。朗顿将人工生命表达得非常清楚:“人工生命是关于人造系统的研究,整个人造系统展示的行为必须具有自然生命系统的特征;传统的生命科学关注对生命机体的分析。通过努力在计算机以及其他人造媒介之内合成具有生命特征的行为,人工生命是对传统生物科学的补充;生物学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之上,将经验性基础延伸到地球上已经发展了的碳链生命之外,人工生命可以为理论生物学做出贡献,把‘我们知道的生命放置到‘可能的生命这个更广泛的场域中。”[2]312人工生命模拟代表了另一种以碳基生命形式所通过的进化论路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世界都将崩塌。
显然,海勒、朗顿、哈拉维的“后人类”指向现在的危机与未来的前景,因此海勒和哈拉维都试图借助于文学作品来展现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这是因为“文学文本并不只是被动的管道。它们在文化语境中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它们也表达一些假说。这些假说与那些渗透到科学理论中的观念非常相似”[2]28。文学作品的虚拟性与计算机技术的虚拟性相契合,我们通过文学作品来理解科技想象的抽象形式如何与物质形式交织在一起,认识并理解“信息如何失去它的身体,电子人如何被创造为一种文化偶像/标志和技术性人工制品,人类何以变成后人类”[2]32。哈拉维认为,当代科幻小说充斥着赛博格、动物与机器合成的创造物,这类形象在世界上处于非常矛盾的境遇,因为他们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赛博格作为一种虚构,构画了我们的社会现实与身体现实,而且作为一种想象性来源正在产生某种卓有成效的结合。”[3]7这也是文学叙事研究对我们理解后人类特性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基于后人类身体变异而产生出对人类本质主义的质询
在理解这一后人类境况的路径中,布拉伊多蒂提出了自然—文化的观点,即“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4]2,因此后人类是与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后女性主义等理论相呼应的一种理论思考,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模糊或者打破各个范畴之间以及各个范畴内部(男/女,黑人/白人,人类/动物,生/死,中心/边缘等)质的分界线。“人类就落入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控制与商品化的全球网络之中。”[4]39布拉伊多蒂显然并非将后人类只看做肉身自然的改变,而是从人类发展史看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由此提出基于人类、生态、环境的关系而产生的新人文认知。她从人类、生态、环境、技术的整体系统重新考量人类、人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后人类其实是一个“批判性的工具来检视一种新的主体立场的复杂建构”[5],如一方面承认我们全球是关联在一起并且在技术上是个媒介社会;另一方面成为重新估量人类的基本参考单位,因为我们交织在星球范围内的人类与非人类的机构之中。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观念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奠基人是笛卡尔。17世纪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一书中就指出,理性是“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唯一东西”[6]21。这个核心的“判断力量以及区分对错能力……所有人类都有同等的能力”[6]20。正是这种能力决定真理,决定了笛卡尔的人类是“我思,故我在”。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本质取决于人类的理性头脑,或者灵魂。C.B.麦克弗森也认为“人类的本質是不受他人意志影响的自由,自由是一种占有功能”[2]4。因传统的启蒙和后启蒙人文主义思想,人类长期假设自己为世界中心的主体,因优越性而获得定义,表达了人类是不依赖神圣性权威、具有理性智能的主体。人文主义证明了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基于普世的人类品质即人类拥有决定正确与否的能力——尤其是理性。它也是大范围的、更具体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解构主义思潮的抨击和消解。福柯在1966年《词语的秩序》、列维斯特劳斯在1962年《野性的思维》中都指出,“人类”主体意识与观念是启蒙时代发明的。沃尔夫(Cary Wolfe)认为这影响到他对后人文主义的介入。“当我们谈论后人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谈论关于进化的、生物的、技术的合作而产生的解构人类中心的主题,而是谈论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些主题,用什么思想面对这些挑战。”[7]这也是沃尔夫提出的“后人文主义”,就是我们不能再依赖“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的存在,提供一种阿基米德的观点来理解这个世界,而应以全新的观念与心理来理解、接受这个世界。巴德明顿(Badmington)并不将后人文主义看作是对人文主义的消解,而是将其看作是对人文主义的重写,是心理上弗洛伊德似的“贯穿”,即对于心理苦痛和创伤,只能是贯穿、耐心重写[8]。这也意味着人们在后人类叙事中需要耐心梳理人类与后人类的肉身关联和精神的内在继承性。
所以布拉伊多蒂把后人文主义看作是对人文主义中“人—他者”二元对立的超越,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是一种“非二元的、自然——文化互动”[4]4,因此后人文主义是超越自我的生命,是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对峙的终结,“以人文主义历史性衰落的假定为基础,同时超越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它努力的方向是制定新的方式来实现人类主体的概念化”[4]53。这个主体是人类与生物、环境、科技融合在一起的主体,它在“人类”与“非人类”的疆界之间穿透、呈动态发展趋势。因此后人类的肉身与主体观念都是贯穿在两者之间,呈现出主体间性。
既然后人类境况为我们提出了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身体的变异,因此,身体研究为我们深入进入后人类叙事提供了路径。身体本身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所谓的‘灵魂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身体的内在构成——既被身体的行动所塑造,又依赖正在发生的身体经验”[9]53。这既是王晓华在《身体诗学》中强调的,身体诗学起源于“西方诗学中从退隐到回归的身体”研究;也是约翰逊提出身体观念应该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活的身体成为文学的起源,演绎了西方诗学研究演绎的“从身体出发”的部分路径[9]53-54。后人类文学的身体叙事引导我们来理解我们面临的新状况。那么文学叙事与身体再现也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后人类主体性与文化建构。
二、《人们叫我动物》:后人类文学身体叙事的可能性路径
《人们叫我动物》是印度裔英国作家因德拉·辛哈在 2007年出版的小说,小说根据印度的博帕尔化工厂毒气泄漏事件改编而成。小说以受害人的视角叙述了这场灾难,他见证了灾难场景,他的脊柱也因那晚的毒气受到永久伤害而无法直立行走,获得了“动物”的绰号(注:为区别“动物”这个人与真正动物的区别,下文都用引号标注“动物”)。小说反复使用身体部位“眼睛”“嘴巴”“耳朵”“四肢”等来构建故事的讲述逻辑与倾听模式。在这种身体叙事中,人们看到了潜在的后殖民政治。如罗曼·巴托什(Roman Bartosch)在论文《辛哈小说里的后殖民流浪者——通过“动物”的眼睛变成一个新人类》中,主张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去分析小说,让我们看到自然灾难背后的社会现实因素,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或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之中还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式压迫[10];或者身体叙事与身体政治的关系。如基纳.B.金(Jina B.Kim)认为我们可以将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残疾研究结合起来,想象城市本身是一个致残和有缺陷的环境。把残疾的身体和城市空间设想为是共同构成的,过度城市化改变了博帕尔原本的城市环境,制造了快速的工业化造成经济发展极其困难,基础设施被毁掉,人的身体被摧残,而这都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11]。甚至由此讨论到叙事真实性与虚拟性的问题,如詹妮弗·里克尔(Jennifer Rickel)认为“动物”挑战了西方文学上的人文主义阅读实践, 在一开始记者想要记录“动物”的故事时,“动物”面临质疑磁带能否正确转录故事以及读者能否准确理解“动物”所讲述的故事等问题。“动物”试图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眼睛”了解故事的真实样貌;试图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平等化;试图告诉读者追求正义的重点是应该让公司接受审讯,呼吁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不只是让“眼睛”把他们的悲惨遭遇当做故事来消费[12]。立足于后人类文学及其后人文主义探索的朱丽叶塔·辛格(Julietta Singh)则在《后人道主义小说》 (Post-humanitarian Fictions)中提出人与动物的二元论本身就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人性影响。比如西方企业势力使处于灾难中的人们残疾,使环境受到毒害,却并没有给予受害者们以基本的人权和赔偿,受害者们都被当做动物一样被忽视、被肆意虐待[13]137-152。显然,这本小说已被置于后人类境况中,学者们重新审视这一境况中人类肉身变异及其矛盾性主体的建构。因此尽管后人类文学经常呈现出人类与机器的虚拟性融合,如赛博朋克小说,但后人类文学的核心就是“剧烈地突破二元模式,打破二元疆界,如机器—人类、自然—文化、男人—女人、高雅文化—低俗文化、身体—思想”,“承载了20世纪晚期后现代、后工业、全球化的以及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态”[14],《人们叫我动物》也呈现为这样一部后人类文学作品,因为小说中不仅“动物”本身的肉身变异,更因为小说中呈现的人类二元认知论的解构。在主人公“动物”身上呈现了最具典型性的后人类身体叙事模式。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一)身体知觉再现与人类主体间性建构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动物”(animal)。“动物”被命名为动物,身体也犹如动物,他不能直立行走,只能四肢着地,所以犹如动物般饮食和生活。可以说,从外在身体形貌上,他从人沦落为动物。“我抬起头来时却只能看到别人的大腿根,最多也就是腰以下那点地方。”人们也常常嘲笑他。“他在那儿!‘动物在那儿!四条腿走路的那个!瞧,是他,因为疼痛,腰弓得跟虾子一样。”[15]10“动物”非常清楚自己身体残疾的原因,“我六岁的时候,身体就开始疼了,从脖子到双肩都火辣辣的疼。从那时起,除了那场大火,我就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疼的抬不起头,再也抬不起来来。剧痛扯着我的脖子,我只能低着头。好像魔鬼骑在身上,用通红的烙铁烫着我,我只能盯着自己的脚。……后来我的背驼了”[15]13-14。他变成了一个四肢行走、直不起腰也无法正常生活的野兽。因此“动物”的身体变异既非赛博格也非跨基因物种,但他也的确成为生化技术导致的基因突变后果的牺牲品。他由此从人类生活中被隔绝开来,成为人类中的他者。
“动物”因身体变异使他成为不被人看见的生物,而他特殊的身体外形又导致他在观察这个世界时“看见”不同的世界。这里“看见”其实具有隐喻意义。视觉上看不见的同时也描绘了文字表述上看不见的状态,同时又产生因观察而误解的、具有欺骗性的“看见”。在《人们都叫我动物》中,“动物”既不被人看见,与他一样饱受苦难的人们自然也不被人看见。小说中讲述了“动物”在法庭讲述他的故事,法官看不见他,因为“动物”的身体被法庭的桌子挡住。这本身就表征了在印度这个国家,“动物”与他的人民都不为权贵“看见”的真实处境。因此他们都成为了在主流观看者眼中看不见的边缘人。即使他们被看见,也通常被错误地认识,这也是当“动物”了解到澳大利亚记者想向他采访当年考夫波尔城的生化灾难时,他将这些西方记者称之为“眼睛”的原因,因为这些记者想要了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想象的东西。在这种“眼睛”注视下,“动物”和他的人民仍然不被“看见”。因此“动物”用口述录音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想让整个世界听到并看到他们的经历。从这个层面看,“动物”的非人类身体使他能超越西方/东方、人类/非人类的二元观念,用他的眼睛和声音再现考夫波尔城的社会生活历史与现状。
《人们都叫我动物》还呈现了“动物”与他的人民通过超越二元体系的“看见”来建构他们自己的认知能力。我们理解人类与世界的认知能力,往往建立在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与获得的知识基础上。认知往往也指向社会认知与政治认知。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述,人类需要认知,认知往往和认同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认同部分是由认知构建,如果认知缺席,或者产生对他者的错误认知,个体或群体就饱受真正的苦难,将被置于错误的、误置的、低等的存在模式中。”[16]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将认知看作是“隐喻、修辞、组织与公众表演的层面”[17],认为认知加强了边缘人发出声音、进行辩护、抗争,并反对违背他们意愿的集体生活。“动物”唤起了人们的认知并让他们重新为世界所看见。
阿甘本用“赤裸生命”指称没有任何国家身份、置于任何历史语境与意义关系之外、处于赤裸裸的任由他人宰割的例外状态,战俘、集中营的囚犯、难民、非法移民等都属于这一种例外状态。这些被排除的、没有身份的生命等同于无权利的动物身体,阿甘本称之为“动物性生命”,而作为政治存在的享有公民权的身体,则是“政治性生命”[18]。“动物性生命”意味着被主权排除在外,同时主权也可以將惩罚和暴力诉诸于他,展现权力统治的合法性。对于辛格笔下的“动物”而言,他本身就处于这种“动物性生命”之中,只不过他还寻求从“动物性生命”走向“政治性生命”。正是基于对“政治性生命”的追求,“动物”口述故事强调:只有当为失势落魄的人进行叙事的时候,这种叙事能为人们所看到和听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才真正开始。这也因此成就了“动物”居于人类/非人类主体间性的建构。
(二)身体作为后人类的创伤记忆
“创伤”(trauma)最初主要指外在力量在身体上造成的物理伤害。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将“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式收入词条,创伤由此被正式确认为一种疾病。导致创伤体验的原因可能是战争、灾难和暴力等重大事件,也可能是生活中的变故、惊吓、疾病、挫折、亲人的故去、甚至被动物攻击等日常事件。无论是哈特曼提出的相互矛盾的两种因素构成创伤内核,如没有被认知或意识到的创伤性事件,以及对该事件的记忆;还是凯西·卡鲁斯所认为的创伤总是通过重复性回放、梦魇或其他形式的重复性现象而不断回归[19],创伤产生出主体思维的碎片性和非逻辑性,呈现出主体认知与非主体认知之间的缝隙。正如维奇(Tony M.Vinci)在分析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机器人能梦见电子羊吗》中认识到的,机器人被定义为是无法发声的、跨历史的存在事实,由此整体上产生与“人类”的割裂。他们从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中异化出来,也由此对创伤一无所知。作为人工智能生命,机器人纪录了人类创伤与记忆,但他并不能感觉或发生共情。因此只能被置于幽灵或不真实的特性中,具有非人类特性并处于人类的他者地位。但如果机器人不仅见证人类事件,而且能体验它自身的创伤,那么机器人就能被看作是拥有人类创伤记忆的“代理者”,它自身也保留了一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疼痛模式的路径。这样的话,机器人解构了人类的主体性与现实性,他也由此成为人类禁止的对象[20]。因此,人类将机器人置于文化想象中的地位最多是亚人类的“工人”,用商业设计来满足人类需求的某种东西。这也反映出跨主体性伦理的脆弱性。
维奇探讨迪克小说中机器人如果具有人类的创伤记忆与同情的情感,机器人就已经是人类,而这也正是人类所恐惧的地方。相对于这一赛博朋克小说,辛格的小说《人们都叫我动物》却以矛盾的、似是而非的方式探讨了创伤记忆对后人类寻找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小说中的主人公“动物”与迪克小说中的机器人角色类似,他见证、体验创伤,却以非人类的存在模式产生了与人类创伤记忆的共情,努力回归人类世界,却又无法获得人类真正的主体性,因此只能寄希望于乌托邦的梦想。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动物”在生化灾难中幸存下来,他的身体本身就具身化了这场灾难,这场灾难将他从人异化为动物。他成为“非人类”的表征。但他又不断在非人类与人类特性之间徘徊,是成为一只自由的、没有主人的动物,还是成为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这种矛盾性突出呈现了“动物”身体的性器官和他异化的男子气慨之间的张力。因此他的身体标榜他为“动物”,而他认同异性恋的男人气质又显示他倾向于成为“人类”。尽管性通常被想象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个关键特征,在小说中性证明是“动物”的“动物性”特征之一。“动物”的身体变异还让他产生出他者的视角,这也导致他在看与被看中掌控叙事。他既被看作是一个被动的景观,如同世界主义者眼中特别熟悉的赤贫、畸形的穷人的被压迫形象,而这一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看不见的”;又在文学上被看见,当然他们仍然只能通过“第三世界贫穷”的景观来建构的看见来被看见[21]。因此“动物”本身承载了考夫波尔城的创伤记忆。
正如王晓华在《身体诗学》中所强调的,“身体的伤口不仅仅是人类学现象,而是世界之殇的缩影;在身体被切割的瞬间,所有实在者都处于危险之中。不解构二元论专横的逻辑,世界就不可能真正处于安全之中”[9]231。“动物”这种身体的变化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外在原因而导致的。辛哈在《人们都叫我动物》中首先将这种身体异变归结为全球资本工厂的罪孽——一场化学工厂的泄漏事故。因此,身体异变是源自于跨国资本活动。因为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印度本身低底线的环保要求,所以高污染化学工厂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和降低风险,在印度本土建造了高危化学工厂。而且一旦化学工厂危险物品泄漏后,一走了之,对所有受到污染和影响的印度本土人民置之不理,甚至将这一问题直接嫁接在印度政府头上。西方资本家以庞大厉害的法律团,在国际法庭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西方资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维护自己的青山绿水,以各种名目将污染与破坏带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也是印度学者古哈所批判的“深度生态学缺乏对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怀”“西方生态学应该考虑帝国主义在理解环境并号召人们来采取行动中所产生的作用,考虑资本主义消费在所谓的‘第一和‘第三世界中可能被批评并被重构对人类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22]。
因此,动物用身体呈现的创伤与记忆有着全球性的、生态的、政治的维度。他成为了尼克森称之为“缓慢暴力”(slow violence)的存在。在尼克森看来,这种暴力是逐渐发生的、也是看不见的暴力,是一种磨损式的暴力,正因为它的缓慢和看不见,也通常不被人们当作暴力看待。但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爆发成为可观感的东西,如气候变化、积雪融化、毒气播撒、生物磁化、森林消退、战争过后辐射严重、海洋酸化等[23]2。在这种缓慢暴力之下,受到最严重影响的人群一定就是经济上处于邊缘地位的穷人。因此他将缓慢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当今的强大跨国资本影响如石油帝国主义、分子工业、外包毒气、新殖民旅游主义等公司和环境的不常规化,“迫使这些不合常规的生产威胁全球穷人的生活、未来和记忆”[23]5。
“动物”以及如同动物的人民就是在这种缓慢暴力的压迫下,一个个沦为环境灾难的受害者,长期饱受身体残疾之苦。他们以自己身体的缺陷表征了环境创伤与文化创伤。
(三)“同情”作为人类与后人类主体间性的联结
文学作品往往通过故事建立基于人类中心的价值,并以这种方式来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的权利,将人类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范畴,是因为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同情的能力。人类叙事始终作为最终的主人公身份叙事,对他所存在的世界施加影响,对他的社会活动和他在国家持有的主宰权合法化。非人类、后人类整体上从“人类”的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非人类、后人类成为人性脆弱的替罪羊。这些替罪羊见证了人类的残缺,也因此在叙事中被虚拟化,为人所忽视,由于从任何真实性的同情的情感中隔离出来,人类由此将自身从他者的疼痛中隔离出来。人类的主人叙事建构了一套阶层体系,即让人类处于特权的、神圣的地位。
当人类产生对“后人类”境况的同情时,意味着人类与后人类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情尽管最早见诸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同情是对明显的坏事的一种伤痛,这种坏事具有毁灭性或令人痛苦,它发生在一个不该遭受的人身上,并且,人们会料想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与己相近的某人身上”[24]。但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情才开始成为人类的典型特性。休谟在《人性论》第二卷中使用“同情”一词并使之贯穿于《论激情》和《论道德》两文中。他指出,人性中最为显著的性质就是同情别人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人经由传递而接收到别人的心理倾向和情绪,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激情传递和感染。“任何感情借着同情注入心中时,那种感情最初只是借其效用,并借脸色和谈话中传来的这个感情的观念的那些外在标志而被人认知的。这个观念立刻转变成一个印象,得到那样大的程度的强力和活泼性,以至于变为那个激情自身,并和任何原始的感情一样产生了同等的情绪。”[25]
《人们都叫我动物》中“动物”渴望成为人类,希望重新获得因生态灾难而被剥夺了的人类权利。同时他原本是人,但却以后人类的方式来理解他的存在以及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矛盾不断呈现在他的躯体追求与精神想象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同意成为一个人,我就必须认同我是一个不正常的、错误构造的人。但让我成为一个四脚动物,那么我就是完整的,我有合适的外形,就像一只不同于牛或骆驼的动物”[26]。成为错误构造的、非正常的人也将“动物”的存在定义为一种有缺陷的、软弱无力的存在,这导致“动物”的身体处于一种永久残缺状态。这也意味着他将自己构画为一个非人类的动物形象,这一形象本身就表明他已经从这个国家的低劣处境中解放出来,超脱于可怕的现实。这当然加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分。这本身也正呈现了巴德明顿所提出的后人类的概念:“后人类文化批评就是解构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这发生在人文主义之内。无需将世界倒转。他者总是处于主体之内。人文主义只是纯粹假装并非如此”[27]。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动物”同时又渴望恢复人类的身体。他对美国医生艾莉的帮助充满期待。艾莉可以帮助“动物”去美国做手术来恢复肉身上的人类形象,这也导致她能拥有权力来注视并阐释“动物”与他的生活。艾莉看待“动物”以及“动物”所生活的考夫波尔城时,她的同情与她所具有的权力和“动物”的具身化肉体之间产生了因果关系。“通过动物,艾莉与康帕尼公司因为对动物身体施加的有害后果而关联在一起”,因此“艾莉通过将这些她相信她会支持的人文性去除了人文性而获得了她自己的人文性。”[13]148这也表明同情与爱共同发生在“动物”,艾莉以及考夫波尔城的正常人尼莎与扎法尔之间。
海勒在讨论变成后人类意味着什么时,强调人类首先是具身化的生物,这种具身生物的复杂性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呈现方式与智能控制论中的机器的具身化是明显不同的。而且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凝结的隐喻,一种物理结构,它的局限和可能性是通过进化的历史形成的,而这种进化史是智能机器无法共享的。因此人类与智能机器的连接并非是毁灭性的,而是形成“一种更温和的对于社会、技术、政治和文化序列等看法”[2]385,这当然传递出一种乐观的想象:人类与后人类可以长期共存在这个星球。
三、后人文主义的身体建构
身体异化表现了人类身体与思想的萎缩,身体异化成为后人类的基本特征,即:身体丧失了人类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构建的功能与审美,在假肢(机械性)或动物身体(动物性)的表征中剥离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人类自我的否定与悖离。身体异化指向对人类科技理性和科技乌托邦的批判与反对。对科技文明的过度追求导致人类身体成为人类研究的对象,而非人类本身的主体性载体。忽略人文关怀与区域发展的泛全球发展最终会将人类带入世界的终结。
沃尔夫由此强调后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后人文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人文主义之后”,而不是作为“后人类”的一种主义形式的附属存在。传统的人文主义和“后人类”或“超人类”技术——狂喜,在沃尔夫看来,都导致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强化”,因为它们都保留了基本的态势,这种态势将解放人类真正的自我[7]。当前流行文化中的后人类,想象了人类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身体存在的挑战,来源于我们假设的人类与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后人文主义并非将人类重新概念化,而是认识一个完全新颖的、更好的人类形式。从这个观点来看,身体限制并未局限了个体自由。身体的改变、甚至剧烈的变异可以取代原来瘦弱的身体,为已经存在的具身化的人类本身获得一种延伸的生命周期和提高的能力[28]。后人类,正如流行文化中想象的状况,在自我之中加入这种优越的能力,追求后身体的修订与异变,给人类昭示出乐观的后人类未来。这也是布拉伊多蒂描述的未来愿景,她希望创建一种后人类人文学科,以新叙事的方式说明全球化人类星球维度、道德进化来源、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未来、技术设备的符号系统、强调数字人文学科的翻译过程,指引走向后人类宣言因素的性别和种族角色以及以上所有的制度内涵[4]240。这呈现为崭新的人文学科规划,将引领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走向可持续的后人类未来。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等都做了充分的论述。
参考文献:
[1]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
[2]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Minnesota Twin Cit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4-5.
[4]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
[5]Rosi Braidotti,Maria Hlavajova.“Introduction”, Posthuman Glossrary[M].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6]Descartes.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Seeking the Truth in the Science[M]//Descartes: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and Dugald Murdoch, ed.and tran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Wolfe.What is Posthumanism[M].Minnesota Twin Cit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8]Badmington.Theorizing Posthumanism[J].Cultural Critique,2003(53):10-27.
[9]王曉华.身体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0]Bartosch. The Postcolonial Picaro in Indra Sinhas Animals People—Becoming Posthuamn through Animals Eyes[J].European Journal of Literature,Culture and Environment.2012(1):10-19.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
[11]Jina.“People of the Apokalis”:Spatial Disability and the Bhopal Disaster[J].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2014(3):7.
[12]Rickel.“The Poor Remain”:A Posthumanism Rethinking of Literary Humanitarianism in Indra Sinhas Animals People[J]. Ariel-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2012(1):87-108.
[13]Singh.Post-humanitarian Fictions[J].Symploke, 2015(1-2):137-152.
[14]Schmeink.Dystopia, Science Fiction,Posthumanism, and Liquid Modernity[C]//Biopunk Dystopia: Genetic Engineering,Society and Science Fiction. England: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6:21.
[15]辛哈.人们都叫我动物[M].路旦俊,辛红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6]Taylor.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M].Amy Gutmann 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7]Appadurai.The Capacity of Aspire: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C]//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 ed. V. Rao and M.Walton. 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66.
[18]阿甘本.在人權之外[C]//汪民安,等编.生产(第7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3.
[19]何卫华.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J].文艺理论研究,2019(2):170-178.
[20]Vinci.Posthuman Wounds:Trauma,Non-Anthropocentric Vulnerability,and the Human/Android/Animal Dynamic in Philip K.Dick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J].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2014(2): 91-102.
[21] Mahlstedt. Animals eyes:Spectacular Invisibility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in Indra Sinhas “Animals People”[J].Mosaic: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2013(3):59-74.
[22]Guha.Radical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Wilderness Perservation:A Third World Critique[J].Environmental Ethics,1989(1):71.
[23]Nixon.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2013.
[24]克瑞斯普.陈乔见,译.同情及其超越[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4):59-68.
[25]杨璐.同情与效用:大卫.休谟的道德科学[J].社会学研究,2018(3):115-140
[26]Sinha.Animals People[M].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7:208.
[27]Badmington. Alien Chic:Posthumanism and the Other Within[M].New York:Routledge,2004:151.
[28]Seaman, Becoming More(than)Human:Affective Posthumanisms, Past and Future[J].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2007(2):248.
作者简介:江玉琴,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欧宇龙,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15F09164-BF1A-47CD-95EB-8AD5ECFFFE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