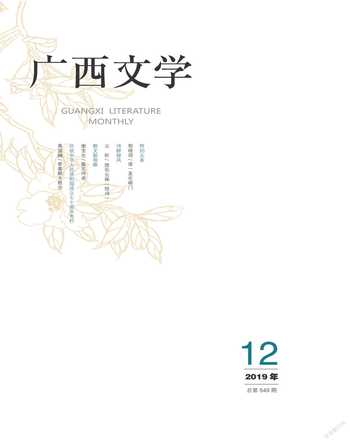陆石桥传奇

土匪烟
在老城,五爷算个异类。
并非说他长得有多怪异,异,单指五爷手上夹着的那根令人闻风丧胆的烟。
烟有名,不然怎能令人闻风丧胆呢,连陆石桥边玩泥巴的小孩都能脱口喊出两句,土匪,土匪!
烟有名,名曰土匪。
这就有点意味了,搁外来人耳边,真以为是来土匪了呢,晃晃头,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下,哪有土匪的影子,只有陆石桥畔的泥水在夕阳的映射中闪着浑浊的光。
五爷的眼也浑了,用他的话说,和三十年前不能比,人都是会老的嘛。
老话在那放着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时光面前,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像接受礼物一样欣然。五爷叼着烟,侃侃而谈的模样宛如一个哲学家。
末了还不忘问上一句,你说是不?
是。
而是的背后,老城人总爱默默加上一句慨叹,五爷的确老了。當然,皆以画外音的形式。
老城人心善,当面说伤人话的促狭鬼,不会在陆石桥畔出生。
说起来,五爷出生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陆石桥呢,这一切,得推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现在人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石河水的湍急,老城的各种宣传片以及县志上留有这样的文字:五十年代,陆石河全长一百公里,发过数次洪水。
而今,数字苍白,这些年出生的年轻人早对数字单位没了概念,凭五爷这张嘴就算能形容出个天花乱坠,于他们亦是波澜不惊,他们只关注兜里的钱包鼓胀和手机版本的升级。
变了。世道变了,唯独五爷和原来一样,爱在陆石河边钓钓鱼侃侃山,唯有五爷还抽着呛鼻子的土匪烟。
唯剩下河水听他讲述了。
跟个前朝遗老似的。
老城人爱在背后拿这话戳他。叼根烟以为自己还是爷呢,异类。
这年头,足够称之为爷的人差不多已经死绝了,但这刺耳的词儿丝毫不妨碍五爷活得风生水起,五爷不是一个活在别人议论中就低头的人。
咱不在乎!五爷说着,从兜里掏出盒洋火,刷地将被风刮灭火的烟重新点燃,老了,谁都能欺负我了。
五爷打着哈哈,对着夕阳,上午发生的那一幕在烟雾中慢慢复活。
——是谁在卖假冒伪劣商品?
来的人气势汹汹,愣不知道这是五爷家的门面,五婶赶出来,小本经营赚个吆喝,待要递烟,却给身后的咳嗽声给制止了,不消说,是五爷。
五爷瞪着来者,一副同样不消说的土匪模样,在老城,没人敢对五爷吼吼。
把你们队长叫来!五爷伸手夺下五婶手中待要递出的烟,呼呼抽了起来,却没料,正是烟出了问题。
五爷,我们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可是您这土匪烟,不是合法烟企生产的,属于三无产品,现在上面抓假冒伪劣可严了!队长六生抱歉道,自己是五爷带大的事连陆石桥边雨天抢生水的鱼儿都知道,小时候承蒙他老人家的许多好。
但六生心里更明白,什么叫法不容情。
如今,老城公然叫卖土匪烟的可就剩五爷一家,得一视同仁不是。
个狗日的,烟雾散去,轮到五爷不明白了。一想到三天后就要将剩余的土匪烟上交,且来执法的是自己从小带大的孤儿六生,五爷就气得直喘粗气,以为我就单是想制作贩卖假货,财迷了心窍?
才不是,说起来,土匪烟可藏着五爷的光彩呢,时间退回到1949年前,五爷只是个愣头青,唯一能和如今搭上边的就是手中那根烟了,那是一个土匪横行的时代,据说当年,五爷就是凭借一支土匪烟装腔作势吓跑刚入城走到陆石桥边另一拨土匪的。
难怪咧,六生挠了挠头,嘴角撇出一丝笑来……
三天后,六生孤身一人准时到达,颇有点当年五爷一人吓退土匪的架势。
小子!五爷摆了摆手,一堆土匪烟码放整齐,就待六生收走,五爷最后看了一眼这见证过自己辉煌的老兄弟,一言不发闭上了眼。
不愧是五爷,大气!围观者都竖起了大拇哥。
六生接下来的所为,则更加出乎大伙的预料。
他没有去碰烟,反是一把握住了五爷那双常年叼烟的大手,从包里掏出一张红头文件。
五爷接过一看,竟是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通知。
六生跟着又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上面印着明晃晃的大字,土匪烟传承人申报资料……
传承人的名字嘛,不消说,是五爷,当年单凭一根烟便吓退了土匪的五爷。
洗 米
过三遍水,米才变得白净。
米白,用老城人的话来讲,如女孩尖尖的十指,淘洗后,泛着白玉般的光泽。
说白玉,一点都不含夸张的成分,前提是,你来过老城,你见过老城的米。
或者更直接点,爱过老城的某个人。
淘米是老城的传统了。也是家家户户、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特长,有人可能不屑,淘米算什么玩意的特长。
哪家做饭不淘米?
呵,问的人显然是没来过老城,做饭都得淘米不假,但洗米,您总没听闻过吧?
洗?
呵,一看你就没去过老城。
老城人都讲究,和北京旧时那帮八旗子弟一样,各种讲究,就好比说饭到了他们这就不是饱肚子的功能那么简单,有人完全可以为了一摞叠新买的青花瓷碗特意去做一顿饭。
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做饭。
那得多俗呀,老城人看着路边落下的槐花,把日子就这么活成了诗,活成了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模样。
慢生活,需要的是耐心。
拿最简单的洗米来说,米要好的,起码得是附近乡里农户自产的米,春耕秋收,得看见秧苗是怎么插到水田里,得看见稻花在风中如何扬起,得看见谷穗怎么含苞抽穗,得看见谷子怎么变黄低头,这米才用得放心。
尤其新米,成色会更好。
水和米各取一半,如恋爱中互补的情侣,水同米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米好水不好,不行,水好米不好,同样没戏,用桥畔水加上正宗的自产米做出来的饭,才叫个香。
香气四溢,就算不配菜,也能吃上两大碗。
再者说,那青花瓷碗,正是一道养眼的菜。
只不过,米再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如同家家厨房顶袅袅飘起的炊烟,被天然气煤气渐渐替代。
倒也不至于彻底消失,但要找到那种米和米香,着实要花费点工夫,进老城往南走,上赤水巷,再由南去,上得现已更名为三三零桥的陆石桥,在桥的尾巴处,或许能寻到她的踪迹。
呵,忘了说,得是晚上。
白天你是寻不到她的。
入夜,月亮升至半空,映在河里,被过路的游船撩碎,化作颗颗白米时,她就来了,推着老城独有的小推车,车上的物件油腻却整齐,酱油、香油以及各种调味料,若看得仔细,便会发觉那是最具老城特色的香米。
米在锅中,通常这个时候,她都会去河边舀上一瓢水,依旧是水米各半,如老城人不变的生活。那饭,却是众口难调了,在各种新生味道的刺激下,就算是老城人都不满足于之前的一箪食一豆羹了。饭当然不能是白饭了,总不能为了怀旧而影响生存吧。
她需要这样的一种生存,她一直没忘记多年前男人离开时的那句承诺,洗好米,等我回来吃一碗。
饭,就是这么变了味的,饶是如此,她的饭却还是老城最正宗的味道,老城人常在茶余饭后讨论,像她这般坚持传统的洗米方式,坚持用桥畔水做饭,真可谓是珍稀濒危了。
这年头,节奏越来越快,一路狂奔,把老城人存在心头的那点慢也给一阵风般裹挟了。
女人却还在坚持,推车上手写的摊名要给自己明志似的,“正宗洗米饭”。
不知道能不能撑到男人回来的那天……
一切都是未知数。
邻镇的疗养院里,每到饭点,一群老人都会议论着与他们一城之隔的这段故事。
开始是一个人讲,大家听,后来就变成了大伙都能参与进来的饭后谈资。
有人质疑过故事的真实性,但总被那个沉默寡言的轮椅老头反驳,故事最开始就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
洗得那么白的米饭,他高位截瘫后就再没品尝过,那么用情至深的女人,以后怕是再难寻觅了。
老人是腊月走的,走之后大伙才曉得,老人户籍所在地,是老城。
老人来疗养院前,老城暴发过一次特大山洪,武警部队某舟桥旅的一个官兵,在抢救陆石桥下洗米的一个女孩时,被急流冲下的木头打断了双腿。
那个武警部队的番号,叫三三零。
→ 刘博文 1998年出生,湖北省作协会员。先后在《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小说月刊》《天池小小说》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阅读试题,并多次进入年度排行榜。出版作品集《至尊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