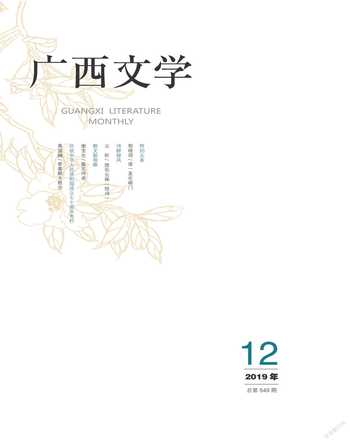亘古不变的壮族乡土
张燕

一
走进广西桂中地区北部壮乡山寨,村周边到处是芭芒。世代在这居住的覃大哥说,看见芭芒就有着一种自然的亲近。芭芒极贱,但生命力极强,极具韧性。岭南的黄泥土、红泥土不论干旱瘠薄、丰腴肥美,它们同样生长得欢实迅速。哪怕石头缝隙一小抔泥土,都能把根扎下来,地上的草被火烧了、牛吃了、镰刀割了,只要草根在,甚至根被锄头挖断,它都能再长出嫩芽、绵延一片。最初的山岭总是芭芒率先生长,经过几年的肥力积累,然后树木开始扎根。芭芒实际站在比树木、比山头更高的高度。
春天来临,最先钻出地面的是火烧地上的芭芒草。秋天烧荒的草灰,为它们铺上一层营养充足的暖被。当惊蛰的雷声滚过,天空云海饱满的乳汁簌簌滴落,山野湿润。小草探出娇嫩的叶片,在尚存凉意的春风中摇头低吟。最初的叶片是鹅黄的,与身旁深绿浑厚的树林形成鲜明对比。在远处眺望,四面山岭的绿色一道深、一道浅、一道凝、一道亮。而生活在这一方水土以覃大哥为代表的一方人,他们极具芭芒的顽强、坚韧。
覃大哥的房子建在那高高的山上,离天很近。那房子有着壮族明显的特点,沿着墙脚,总要填起来,做一级长长的坎梯,这就是阶沿。有了阶沿,就不用担心墙脚会销蚀。下雨的时候,地上有了积水,有了鸡蛋样的一个个水泡,那鸡蛋样的水泡流过来,遇到阶沿拦住了,又一个个靠着阶沿流走了。下再大的雨,墙也不会浸湿,屋里的地面也很干燥,不用担心那还堆在地上的一堆小山似的谷子上了潮。
房子盖起来,刚安上白色的木门、木窗,新墙一片黄润还来不及粉刷,阶沿就要砌起来了。先是做墙似的,用石头围着墙做一道护坎,然后就在里面填上泥土,再用一个拍耙把填进去的松土夯实。拍耙是用木墩做的,像巨人的一只脚,人们往往是在等着吃饭的间歇,一点儿时间做不了别的活儿,就拿着拍耙去拍阶沿的新土。
阶沿围着墙,并不宽,也就是屋檐遮挡的那一点儿空间。下雨的时候,从檐上瓦沟里落下的雨,刚好滴在阶沿坎的外面。
阶沿上还印着一个个脚掌似的拍耙的印迹,人们就忙着搬进新房了。墙壁也还是一层蜡黄,窗子和门,白白的木质也还没上漆,但是已贴上了红色的对联,这新砌的阶沿与新房及房主人覃大哥一道,在迎接乡亲们的贺喜了。一阵阵鞭炮噼里啪啦,飞来的鲜红纸屑,梅花似的散落在阶沿坎上,这是对新垒的阶沿坎最好的装点。为躲避鞭炮,捂着耳朵跳上阶沿坎的孩子,一个个脚印也印在拍得平整的阶沿坎上。接着,手脚麻利的覃大嫂把几个妇女烧水弄饭的炉子、放茶壶的凳子、几把椅子和其他一切在屋里被嫌占地方的东西,全都摆在阶沿坎上。在新房开门纳客的时候,阶沿坎也开始了跟它的主人同样繁忙的命运。
每次覃大哥、覃大嫂劳动之后,锄头、铁锹、钎担、犁耙……用过的农具放在阶沿坎上,油菜、稻禾、豆秸……收割的庄稼也放在阶沿坎上。它是一个露天展台和贮藏室。只要看一看那沾在农具上的泥土,就知道主人在做些什么农活;只要看一看那码在上面的庄稼,就知道主人是怀着丰收的喜悦,还是凝结着淡淡的歉收的忧愁。
下雨的时候,阶沿成了鸡鸭们的避难所。一只母鸡蹲在阶沿坎上,张开了翅膀,一只只小鸡偎在母鸡的翅膀下,叽叽地叫着,伸出头来望着那冲下阶沿坎去的雨帘。这时,如果覃大嫂在家,就会扯起嗓子喊:“覃小弟,你快点回来,不见下雨了吗?”覃小弟边回答“哦”边伸出手掌,小鸭子似的站在阶沿坎上,用长喙承接那阶沿外的雨。从檐上瓦沟流下的雨水,把阶沿下面的泥巴甚至青石冲出了一个个的凹坑。水滴石穿,阶沿坎见证了太多的岁月风雨。
砌阶沿的石条,成了放学回家孩子覃小弟的书桌,覃小弟趴在那阶沿坎上做作业。而那一条狗,也趴在阶沿坎上,望着路过的人,不时冒出几声吼叫,肯定是有生人从门前路过。突然从屋角的阶沿坎上跃起一只鸡来,大声地叫着离开鸡窝,翅膀从鸡窩里扑打出的几根稻草,闪映着傍晚黄澄澄的夕阳的光辉,蜻蜓似的在空中飘荡。
劳动之后的覃大哥坐在阶沿坎上,沐浴黄澄澄的夕阳的光辉,不时吸一口烟。不知什么时候,皱褶开始爬上他的脸颊,淡淡的烟雾缭绕脸颊上的沟壑,夕阳下有了沧桑的感觉。那平整的阶沿坎也起了泡,地上变得高低不平。望着伏案做作业的覃小弟,凳子已歪向一边。覃大哥站起来捡一片瓦砾,将歪斜的凳脚垫正,并意味深长地看着覃小弟。相信时间会让覃小弟明白父亲眼光的含意。
“吃饭啰!”覃大嫂的一声召唤,父子俩的目光一对,温暖就在眼中荡漾开来。
二
屋檐下的墙壁钉着许多的钉子。覃大哥站在板凳上,招呼覃大嫂把收获的庄稼挂上,常常是一捆黄色的苞谷,一串红色的辣椒,或者用线串着的一串串晒干的豇豆、四季豆,用篾条串成一个个花环样的萝卜条,几袋子装在塑料袋里的蔬菜的种子。不小心,板凳有点打晃,覃大嫂一声惊叫,赶忙扶住。覃大哥还有点满不在乎,“本来我没有事,你一喊反倒吓到我了。”“好心无好报,好柴烧烂灶。”覃大嫂一脸的委屈。一看天气不对,覃大哥赶快转笑脸、赔小心,“怪我,怪我。今天晚上我煮饭、洗碗。”“谁要你洗,猫舔似的。”覃大嫂嗔道。
来了客,实在没有其他的菜肴招待了,覃大嫂就用一根顶叉,仰着头,把挂在墙上的干货取下来。阳光照在墙上,也照在挂在墙上的苞谷、辣椒以及那些枯黄色的干菜上。伸出墙的一排屋檐,将投在粉白的墙壁上的日光切了一条阴影,而那些一捆一串的苞谷辣椒,也在墙上投下一团团的影子。于是这些黄色、红色,以及其他挂在墙上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就像浮雕似的立在这面墙上。一只鸟站在苞谷上低头啄食,一声轻微的声音,一颗苞谷米划着一路金线,顺着墙掉下来,像是滴下一滴阳光。
屋檐下的墙上,成了勤快的覃大哥、覃大嫂展示色彩丰富却并不富裕生活的地方。
为了方便晾挂东西,覃大哥在屋檐下吊上一根竹竿,一头系在一根檩木上,很像简陋的学校里的那根单杠。不过这根单杠很高,吊在大门的上面。平时这根单杠是空旷的,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吹得它一摆一摆。在覃小弟的目光里,会疑心是不是有看不见的精灵在那里打着秋千。偶尔会有一只喜鹊,飞到这根竹竿上,急切地叫着。这时便有拿着升子准备去米缸舀米的覃大嫂,从大门里探出头来,心想这又是哪个客会来呢,而这米却是要多舀些了。年关到,年猪杀了,这竹竿热闹起来。上面挂满了一条条的猪肉、一串串的香肠,来的客人仰首一望,不免要发出一阵羡慕的赞叹。覃小弟更是写一个字都要抬起头来望一眼,好像作业的答案就在那竹竿上。
是的,覃小弟的人生答案就在那竹竿上。
傍晚,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墙上,还有那吊在檐下的竹竿上的一切,都褪去了它们的颜色,也变得昏暗而模糊了。一团团的,像是附在檐下的巢穴。飞出去又飞回来的一两只鸟,不停地绕着屋檐上下翻飞,似乎在寻找它们的归巢。有从野地里提着一篓猪草回家的孩子,见了翻飞在檐下的轻盈的鸟,心想这不正是昨夜模糊而灵动着的梦吗?
此时,屋内已响起劳作一天的覃大哥的鼾声,以及覃小弟梦见美味的磨牙声。
三
覃大哥房子外面的田边有石围砌。尤其是冬天,山上已没有什么绿叶,更不见什么青草,山坳里的那一片田更成了饥饿的牛们关注的对象。勤快的覃大嫂给了菜园一园丰腴的油菜,苍翠的菜秧,全成了一望便忍不住要拔腿而去的欲望。
为了防止牛吃庄稼带来的纠纷,有田的田边就砌了一道长长的石墙。
像细心种植庄稼一样,人们一丝不苟地围砌这道围墙。依着山势而筑,山坳高低不平,围墙也蜿蜒迤逦。围墙是用岩石砌的,一片片,一层层,每一层排列整齐的岩石都是一条蜿蜒的曲线,层层的曲线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道袅绕而去的围墙。围墙那一道道袅绕的曲线,就是它凝固的年轮。
围墙确乎很古老了。风吹日晒,围墙上的块块岩石已成了灰色,如同天空一样色泽苍茫。惜地如金的覃大哥、覃大嫂们,会在它的墙根下种上一些南瓜冬瓜,让瓜蔓茎藤爬上去。秋来的时候,一个个红红的老南瓜便像一路的灯笼坐在围墙上。一年又一年,围墙上枯萎了一层又一层的茎藤,就像缝补了一道又一道针线。人们在田里劳动,一群赶上山坡的牛从田边经过,不再担心它们会头一扬,一脚踏进田来。从围墙里看过去,只见一个个牛头带着光滑的脊背平着围墙浪似的滑过去。
田里的油菜割了,田要耕;田里的苞谷收了,田要种。每到耕种的季节,人们就会拉开墙门,让牛走进围墙里面的世界。这个时候,人们放心地让它啃食丢弃在田头的稻草,或是堆在田边的红苕叶。但更多的时候,是牛拉着犁,又在围墙里翻涌出一道道黄色的波澜,季节的生命又再次诞生。牛耕种着季节,围墙保护着季节顺利成长。季节在围墙里轮回,变换着四时不同的颜色,只有围墙一成不变,在灰色的蓝天下,蜿蜒成半山一条灰白的云带。
有时山洪暴发,从山顶扑下来的一条恶龙似的水,会将围墙冲坍。蹿进围墙的洪水将田冲出一条槽,苞谷苗冲倒了一片,露出的禾苗根须和田底里新鲜的黄土,像割裂的一道道伤口。这时覃大哥的父亲就会再找来岩石砌上去,新砌的岩石颜色鲜润,像一块伤疤。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时间就会像消除人们的痛苦似的消除这道伤疤,你就再找不出哪里是新砌的岩石了,那些围墙早已浑然一体。痛苦不会拿出来示人,而会永远被自己埋葬。
围墙也有它的脸,那就是墙门。墙门十分简陋,就用几根木棍钉在一起,上面的一根横栏,由于长久的抚摸已变得光亮。牛进出被碰擦,会让粗糙的门栏上沾着几根牛毛。覃大哥的老父亲在门栏上写一行很粗糙的字,过去一看,那是在提醒进出田园的人们要“随手关门”,否则就会让牛产生误会,进去吃了庄稼。为了防止野物的入侵,上面还别着几根荆棘,露着一行行如牙般尖锐的刺。
然而就是这扇简陋的门,路过的牛们头一低,就可听见围墙里的庄稼四季成长的消息。
四
用了几个月时间,覃大哥带领村民终于在山里水源林建好了大水池。从此,每天清晨人们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用破开的竹子连成的水枧在屋前屋后,像一条条的青龙盘踞在小村里。连接处装上水龙头,从此山里人用上了简易自来水。山上的大水池,维系着竹管道的水流量,维系着村里人的日常生活,维系着一方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所在。
自从有了大水池,有了简易的自来水,人们用水便可足不出户了。但男人还是会到水池边去打水,也有女人会来这里洗菜。大水池旁边是个小水池,大水池的水常常會溢出到小水池。洗菜的女人会在小水池边用一个木耙在竹篓里捅进捅出,篓里切碎的白菜似白色的蝴蝶,从篓子的边缘扑出去,随着水波一荡一荡地散去。还有小女孩来这里洗衣,从水池里提起一串串白花花的水花,又啪啪掉进水池里。牛们也会来喝水,如果是夏天,还会几步抢进水柜,埋下头去,伸出头来的时候,噗噗地从鼻子里喷出两股清凉的水柱来,山上的生命因此而汇集在一起。这时有人唱起山歌:
种田要种弯弯田,一弯弯到妹门前。
半夜三更来看水,一看田水二来连。
坡上水池架竹枧,清水流到妹门前,
哥想变成长流水,直接流进妹心田。
韭菜无盐莫打汤,旱田无水莫插秧。
妹你无心莫哄我,莫来哄哥枉思量。
见哥心好妹才连,不是贪图哥有钱。
煮个苦瓜来送饭,无油无盐也清甜。
山歌,在快乐中,以歌传情成就了又一对年轻人。田里撒下了种子,水池发挥了大作用。竹子做的水管道直接落进了田里。庄稼苗长出来了,水顺着竹管道流向了油菜田或者禾田里。水池仿佛有固定的水源,常常会自然而然地自足。它的来源有一部分便是那苍茫的蓝天。乌云四起,狂风大作,雷鸣电闪,骤雨铺天盖地,天空中的鸟在仓皇地寻找避难之所的时候,便是水池准备饱餐之时。雨点打着树叶,又汇成奔涌的山水,扑向堰塘那张开裂已久的怀抱。
一方水土,养活了人、家禽野兽、果蔬草木。
五
“没有盖过房子的男人不算真正的壮家人。”对于盖过房子覃大哥总有一种终于过来人的感慨。覃大哥建房恪守壮族人的习惯,内部结构是木头的,神龛放在整个房子的中轴线上。前厅用来举行庆典和社交活动,两边厢房住人,后厅为生活区。屋内的生活以火塘为中心,每日三餐都在火塘边进行。覃大哥的房子仿如他的性格,沉稳内向,外表文静、谦和、礼让,但极其顽强,有一种不露锋芒的锐气和韧劲。覃大哥吃苦耐劳,却是封闭而保守。覃大哥、覃大嫂如祖祖辈辈生活在房子里的先人,壮语是他们传承下来的母语,并祖祖辈辈在母语中生存,又在母语中死去。覃大哥、覃大嫂他们传承了母语也传承了壮族的文明:无论如何的贫困,有客自远方而来,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客人以最好的食宿,对客人中的长者和新客尤其热情。用餐时须等最年长的老人入席后才能开饭,长辈未动的菜,晚辈不得先吃。给长辈和客人端茶、盛饭,必须双手捧给,而且不能从客人面前递,也不能从背后递给长辈。先吃完的要逐个对长辈、客人说“慢吃”再离席。晚辈不能落在全桌人之后吃完饭。路遇老人,男的要称“阿公”,女的则称“阿婆”……
平凡而又普通的覃大哥,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在依此写着母语传承下的世代文明……
站在山下仰望覃大哥、覃大嫂,他们在劳作的间隙偶尔拄着锄头歇息,似乎只要手一伸,就会触摸到蓝而柔软的天空。而劳作过后的覃大嫂望着快要落山的日头,眼前的覃大哥变得青春活泼起来。他们俩依偎在夕阳的草垛下,“那个日头像只金瓜(即南瓜)。”“你想不想要?”“难道你还能把它摘下来?”“为了你我什么事都能做。”覃大哥站起来,爬上草垛伸出手,谁知脚下一滑跌了下来。覃大嫂骑在他身上,边胳肢边说道:“看你能、看你能”。那清脆的笑声把漫天的星星吸引着探出头来,把他们包围。那一颗颗剖开的石榴子般鲜润晶莹的星子,如果他们想要,也会一摘就摘一大把来。
更老的房子零星地长在光秃而裸着许多岩石,或是长满了青枝绿叶隔断了人们视线的山坡上。只要山上有田,即或是贫瘠的梯田抑或荒凉的山坳,就不难找到房子的踪迹。它们的主人有着因整日劳作而无暇顾及的衣冠不整的形象,以及沾着汗水和草屑的有些肮脏的脸,见了生人就会露出拘谨而诚实的笑容。
就是这一张张黝黑沧桑的脸,却让那一块块田地无比生动活泼。
如何荒芜的黄土地,在覃大哥、覃大嫂双手中,到春天也会滚着一坡油菜花的金黄,夏天涌着一片稻禾的翠绿。流转的季节在这一块坡田上呈现不同的色彩,而那离田不远处,一幢坐落在山坳间低矮的房子,守护的模样永远是一张不露声色的平静的脸。
不知是有了这块田才有了这幢房,还是因为有了这幢房子才有这块田,这连覃大哥的老父亲都不知道,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现在,房子就像是山坡上长出的物件,和田地同样古老。茂盛的季节走过了收获,沿坡而起的蓝天下,铺上山顶的是一片黄土的沉默:玉米伸张的枯叶在秋风中飘动;还留着秸桩的厢田,厢田里长出的一盘不知名的野草,一只觅食的蚂蚁站在小草的顶端晃动着两只茫然的触角。田地恢复于和房子一样黄色的宁静。喧嚣是短暂的,平静才是永恒的。
这丘陵地带,多数不是连片群聚的房屋,常见的是散落着的单家独户,在起伏的山间,如同孓然掉队的部族。在离群索居的沉默中,这些房子骑在山坡上,和连绵的山脉一同起伏。
覃大哥原来的老房子静立在田旁,简陋而质朴。墙面斑驳,窗户狭小,屋檐下的阶沿坎上,永远堆放着犁耙、板车架、粪筐、锄头及一些沾着泥土与岁月的农具,一副清贫而不息劳作的景象。在覃大哥的记忆中,如果说这守在田旁的房子还有一些活泼鲜亮的颜色,那是在叔叔娶婶子的时候。灰暗的墙壁粉刷一新,露出了一片耀眼的粉白,像人穿上了一件夺目的新衣,贴上的红对联似壮家衣服绣上的花边。帮忙的亲戚、邻居川流不息,覃大叔腼腆地坐在那等他的新娘进屋。覃大哥和一帮小朋友兴高采烈地跑进跑出,不时汇报:“新娘到田垌了。”“新娘上坡了。”伴随着孩子欢快的叫声,就有山歌唱起:
双双红烛照华堂,照见一对美鸳鸯;
天上七仙配七子,人间淑女配贤郎。
锡壶摆在八仙台,手拿锡壶把酒筛;
夫妻换杯和气酒,百年团圆又和谐。
富贵灯花两朵开,夫妻二人提拢来;
今日提灯吉星照,又添丁来又添财。
夫妻双双拜祖堂,拜完祖堂入洞房;
今日洞房花烛夜,鸾凤和鸣百世昌。
搞得覃大叔急切而又拘束地扯着衣角。旁边的大嫂和婶子们都在笑话他。随着时光流逝,年关的气氛会如白雪渐渐消融,娶进门的女人也如田里过季的庄稼不再光鲜。过了一年两年,那面粉刷过的墙壁,搬迁的农具将它碰起了几条槽,春天的土蜂将它钻了几眼孔,瓦上的漏雨在上面爬了几条蚓痕,溅起的雨水更将墙脚点成了一片五花脸。于是房子又回复到它往日的面目,灰暗而又陈旧。
春天到来,布满小孔大眼的土墙上,固然有爬出墙孔的土蜂飞绕着金线,让它不至于太寂寞,但是在喧闹的季节里,葱茂的枝叶和绽放的鲜花围绕的这一幢幢土房仍是副守望者肃穆缄默的模样。灰暗与陈旧,并不代表生命的停歇和枯萎。覃大哥的父母总是在屋角的空地植上桃李、枇杷树、板栗树,感受四季的征候。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一株暴灼的桃花,一树栗树的嫩芽,便在土房苍老枯黄的墙根下安然开放。人们的新生活因为平淡陈旧的背景更加踏实稳重。
如果放眼都是贫瘠的岩石,田旁的房子就更简陋了。没有土,没有泥,整个墙壁都是用一块块的岩石片砌起来的,周边盖的也是一片如鳞的岩块。摸着那些砌成墙壁的岩石,就像抚摸一个个堆砌起来的平淡无奇的日子。
在这平淡无奇的房子里,住的就是这些离天很近说着以壮话为母语的人。这些人似乎都是一个样子,整日都是一副忙碌的身影:低头背着一大捆柴草,四面虬张的柴草便淹没了他的身影,似乎有长了脚似的大草堆在缓缓移动,分不清那负着移动的柴草的是男是女。或是努力佝伸着头背着一年的收获,背稻禾,一袋大米,沉重的粮食压弯了他们的腰。常见的是忙碌而沉重的背影,极少看见他们的脸庞。如果想仔细看一看山里的人们,就去望一望那铺展在天空下的田地,守护在田地旁的土房,黄色的泥土就是他们的脸庞。
春天是一坡油菜花的金黄,夏天是一坡稻禾的翠绿,这一坡的田地成了一方天地美丽的脸庞,而那田旁的房子和建在房子下的猪牛圈,就是让它四季美丽的心脏。到了秋天,田旁的屋场上就会堆晒一地的稻禾草,还有颗颗黄润坚实的苞谷米。会让人想到,在漆黑的夜晚,这些苞谷米准会像星星一样闪光。
六
山歌时不时在山间回荡,覃大哥说:我们这的壮族一直有“一家挖地,百家相帮”的习俗,因为单家独户,劳力有限,不能大面积开荒造林,因此,要想大面积开荒造林,就得需邻里乡亲的支持,打锣挖地就是这样兴起来的。挖地那天,主家请来既会打锣又会即兴编唱山歌的师傅,在工地打锣唱歌鼓舞士气,推进挖地进度,扩大战果。这时劳动场景就成了歌海,有山歌傳来:
蚂蚁牵线长又长,挖地的人来四方,
扛把锄头三斤半,齐心协力垦山荒。
金鼓一敲响咚咚,挖地犹如打冲锋,
老年赛过黄忠将,后生猛如赵子龙。
一声鼓来一声锣,众人挖地南山坡,
锄头挖断几多把,后生个个打赤膊。
下米挖到午时边,又想茶来又想烟,
主家茶米眼也到,叫声大伙歇困先。
锣鼓一响又开工,四处山头摆长龙,
锄头落地山打颤,泥土翻起地皮红。
声声锣鼓声声喧,挖地挖地日西偏,
想拉日头莫落岭,可惜没有绳来牵。
金鼓停音锣停声,感谢乡亲父老们,
今日劳累辛苦了,回家路上慢慢行。
告别覃大哥走出山寨,山歌声渐行渐远中给予了一种力量。亘古不变的桂中壮族乡土,生活着壮民族的祖祖辈辈。那流传已久的壮族山歌,那传承世代的民俗,那离天很近的房子,那房檐下的阶沿,那方人赖以生存的山坡水池,那长长的石围墙……是壮族亘古不变的生活元素,它写着壮族人的智慧、勤劳、质朴。以覃大哥为代表的一方人,他们的一生,在沿着祖辈生活的轨迹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 韦 露
点评:《亘古不变的壮族乡土》有浓郁的民族风情,涵盖了壮族鲜明的民族文化元素。覃大哥、覃大嫂等继承了壮族血脉中勤劳、顽强、隐忍、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在这方水土安身立命,劳作不息,艰难的生存中依然有着朴素的诗意。每个场景都蕴含着丰富的乡村细节,通过一帧帧鲜活的画面,为我们缓缓铺开一幅壮族乡村生活的真实画卷。(韦 露)
→ 张 燕 笔名鹊儿。来宾市作家协会理事,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曾发表于区内外各级刊物,鲁迅文学院第四届西南区青年作家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