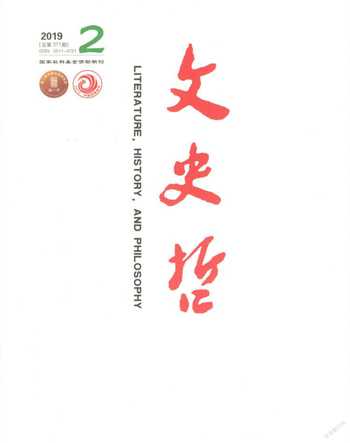庄子“齐物”观念的政治意蕴
摘 要:庄子的“齐物”非仅指涉着以生命为本怀而绽开的精神境界,更蕴涵着以政治为关切而衍生的治道推衍。“齐物”的政治性在“齐是非”的旧义与“齐文野”的新义中均有体现。“齐物”既意味着庄子对儒家政治哲学“入于非人”的细微批判,也呈示着某种“齐之以道”的政治建构:通过对“成心”之必然、多元与开放义的揭覆,庄子主张摆脱“是非之争”的樊乱以及“师心自用”的知识、价值或权力专断,以避免“意有所至而爱有所无”的情感落差与“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惨淡结局;通过对“道通为一”、“相尊”、“相蕴”等存在视域的孤明先发,庄子认为政治生活应充分尊重并涵容“多元主体”,从而倡扬以挺立主体的独立性、激发主体的创造性、维护主体的多元性为鹄的的“天籁”式政治模式。
关键词:庄子;齐物;是非;道;治道。
《齐物论》无疑是《庄子》中最富哲学内涵的篇章,其语言之微妙、思致之邃密,适足以展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敞开样态,从而激发并涵容着后人对它的多维诠释。对于篇题三字应作何解,哲学史上即有两种主流意见:“齐物-论”以及“齐-物论”。鉴于先秦典籍中屡有关涉“齐物”之说[ 例如,《庄子·秋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天下》:“齐万物以为首”;《周易·说卦》:“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孟子·滕文公上》:“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子·上德》:“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齐同”。“万物一齐”、“齐万物”、“万物之洁齐”、“物之不齐”、“万物齐同”等说法均意味着“齐物”是先秦时代的流行观念。],早期注家时将《齐物论》简称为《齐物》[ 例如,《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句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崔譔之言曰:“《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页)],并常用“齐物”来概说庄子的思想[ 《齐物论》“五者园而几向方矣”句郭象注:“故齐物而偏尚之累去矣”(郭庆藩:《庄子集释》,第88页);《齐物论》“我欲伐宗、脍、胥敖”句成玄英疏:“欲明齐物之一理,故寄问答于二圣”(郭庆藩:《庄子集释》,第89页)。郭象、成玄英都以“齐物”为庄子哲学的核心观念。],我們不认为源出宋代的“齐-物论”[ 林希逸说:“物论者,人物之论也,犹言众论也。齐者,一也,欲合众论而为一也。”(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页)]这种读法与庄子的本义更为接近,或者说更能全面揭示庄子思想的可能意蕴。因此,本文关注的是庄子的“齐物”观念,并以之为庄子哲学的核心要旨。对于“齐物”,陈少明先生以“齐是非”、“齐万物”与“齐物我”三层意旨阐释之[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认为在认识论、本体论、生存论的相应论域中,三者均指向“庄学最为关心的个人幸福(自得其乐)或精神境界问题”[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第174页。],且以揭示了“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的“齐物我”为“庄子哲学的最终结论”[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第66页。]。此外,陈先生虽然意识到了隐含在“齐物”背后的“政治焦虑”及“政治抗议”,但并不认为《齐物论》的主要价值是“提供直接的政治意见”[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第47页。]。陈先生的相关研究无疑是精到而周洽的,本文则欲详其所略,旗帜鲜明地从“政治”维度切入对庄子“齐物”观念的诠解,不仅凸显庄子的“政治抗议”,而且建构庄子的“政治意见”,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这一哲学纲领的理论空间。
一、“经国莫如《齐物论》”
在对庄子哲学的研究中,因为我们更惯于或乐于强调庄子的生命关切、精神境界、美学情调或神秘体验,也便不能充分理解他对“方内”世界的烛微照察。余敦康先生认为,在“挺立了知识分子的孤傲狷介独立不倚的人格理想”的同时,庄子也有着“貌似冷峻而实则热忱的救世情怀,站在宇宙意识的高度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谋求自由而和谐的社会发展前景的政治理想”[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9页。]。那么,庄子的“救世情怀”何在?其“政治理想”何解?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事君”、“事亲”的传统价值之外开出了“自事其心”之独异存在方式[ 参见王玉彬:《庄子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1页。]的庄子会返而“入游其樊”,对那个他不欲以“庄语”道之的“沉浊”世界进行正面而积极的筹划?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回答这个问题:“齐物”在何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
论者多会承认,“齐物”之核心义即为“齐是非”。显然,“是非”涉及到真理的标准、知识的结构、语言的运用等问题,可以被很方便地归入知识论语境。庄子对此有着丰富的论说,并构成了《齐物论》的主体内容。然而,先秦“是非之争”的理论目的多非通过理性思辨而求索真理,而是体现着诸子在“时之弊”、“世之衰”的政治背景中对救世之方的积极求索。我们不认为庄子业已“超凡脱俗”,完全脱离或超离了这种现实背景与思想关切。对于庄子研究而言,如果“使其哲思仅守成于‘生命哲学’的格局,则将令庄子断离于战国时期以‘拯济时弊’为基本关怀的思想脉络,仿佛其与整个时代思潮完全无关一般。”[ 吴肇嘉:《庄子应世思想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第10页。]这显然不符合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的思想背景与深沉恻怛的存在关怀。换言之,庄子“齐是非”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解决“儒墨之争”的思想问题,但鉴于“儒墨之争”的目的是“务为治”,庄子对儒墨之“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理论批判必然蕴涵着对儒墨之治道(尤其是儒家)的评判。而对于“是非”与“治道”的密切关系,在《庄子》中有着非常清楚的表达: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为来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大宗师》)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而未始入于非人。(《应帝王》)
在儒家的政治图景中,“是非”必须得到明确的说述,才能佐证仁义价值的真确性;“非人”即“以人为非”,蕴涵着“以己为是”的价值确信以及“强人以从己”的内在诉求。可见,“是非”问题堪称尧与舜(有虞氏)所奉行的政治运作方式的核心,显然是关乎“治道”的。而庄子之所以欲从根本上消解“是非之争”的正当性,是由于樊然淆乱的“是非之争”是世道丧乱的根本缘由,或者说,流行于世的“明言是非”的治理方式是天下沉浊的直接原因。显然,无论是从思想背景还是理论指向来看,作为“齐是非”的“齐物”与“政治”有着内在关联,其“最终指向”依然是诸子究心的“治道”问题。
在《庄子》的诠释史中,着意于将庄学解读为“涉俗盖世之谈”、“游外冥内之道”的郭象既已对《齐物论》的很多文本进行了政治化的解读。然而,鉴于郭象哲学的起点和归宿深具“调和儒道”、“摄道归儒”的特点,在其注文体系之中,庄子对尧、舜、孔子等儒家圣人的批判注定会被消弭于无形,这恰恰歪曲了庄子政治哲学的独特品质,窒碍了庄子政治思想的潜能与活力。在中国哲学史上,真正欲将庄子独具一格的“齐物”之政治理趣发扬光大的哲人,则非章太炎莫属。在章太炎看来,庄子乃“方内之圣哲”[ 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6页。],《齐物论》为“内外之鸿宝”[ 章太炎:《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7页。]。基于这种认识,章太炎创制了“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梁启超评价说:“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6—87页。]。实际上,章太炎为“齐物”思想开辟了两块“新国土”:一是以“唯识学”解“齐物”之理,二是以“齐文野”阐“齐物”之义;前者是学理性的,后者是政治性的。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学理性解读过于炫目而深涩,其政治性解读的开创性价值也便隐藏在这种光耀之后的暗影里了。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着意于凸显“齐物”观念的“方内”特征和“外王”指向,以佐证“经国莫如《齐物论》”[ 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5页。]的断语,其立论主要围绕着这段材料: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齐物论》)
章太炎认为此章“辞旨渊博,含藏众宜”而又“精入单微,还以致用”[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101、64页。],堪称《齐物论》之“环中”。据此,他发明了一种崭新的“齐物”义理——“齐文野”。所谓“文”,即尧所代表的德化文教;所谓“野”,即宗、脍、胥敖所代表的“蓬艾之间”。由此,尧对三国的攻伐实际上意味着“文明/进步”对“野蛮/落后”的粗暴侵凌。在章太炎看来,正所谓“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第100页。],尊重弱者的政治实际与生活方式才是更“文明”的做法。帝尧的“不释然”体现出了他的自我反思,意味着“以文压野”的行为委实并不“仁义”。如欲避免假借“使彼野人,获与文化”的“高义”而行侵略兼并之实,就应当承认风纪万殊、政教各异、文野异尚而以“齐文野”为“齐物”之究极[ 章太炎说:“夫应物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第101页。]。正如论者所说,对于章太炎而言,“齐物可说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之最后定论。它坚持每一个体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不必受任何首出群伦的标准所笼制,世界文化亦不必求其大同,而人类文化最可贵处也正是在每个文化之间各有独特性,最重要的不是去寻求统一,而是对相互间的差异抱同情的理解。”[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由上所论,庄子“齐物”观念的政治性可在两个层面得到证成:其一,“齐是非”的基本义内蕴的政治性是毋容置疑的;其二,“齐文野”的创新义也在引导我们重视“故昔者尧问于舜”章的政治寓意。由此,我们便可推而行之,纲举目张地展开对“齐万物”、“齐物我”等“齐物”之义,以及《齐物论》中“丧我”、“天籁”、“成心”、“相尊”、“相蕴”等重要概念的政治性解读。
二、“入于非人”的政治批判
在庄子的思想脉络中,上引“故昔者尧问于舜”章意味着庄子对以尧为代表的儒家治道的严厉批判[ 历代注家对于此章文义与寓意的解读颇为驳杂,参见王玉彬:《庄子〈齐物论〉“十日并出”章辨正》,《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尧对宗、脍、胥敖等小国的攻伐实即意味着儒家标榜的“德教”的异化,在尧的强力推行之下,这种理念比“十日并出”更显光耀,会导致“万物皆照”也即生灵涂炭、万国夷灭的灾难性后果。郑开先生认为,庄子“针对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抱有某种强烈质疑与彻底批判的反思精神”,其锋芒所向,主要就是“当时徜徉于世的、深植于传统之中的礼治方式和德政(仁政)理念”。[ 郑开:《〈庄子〉浑沌话语: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29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4页。]那么,儒家的德政与礼治到底有什么弊端?庄子的质疑与批判是如何开展的?“齐物”又在何种程度上呈示着庄子对儒家治道的批判?
尽管尧对攻打宗、脍、胥敖感到“不释然”,但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看,这种行为却有着某种道义支撑:“文明”是可欲的,“野蛮”是可耻的;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推己及人”是仁爱的正大体现,哪怕这种“正义”的实现依靠的是“不义”的攻伐。显然,这种政治逻辑的隐含理路主要便是“是非”问题:文明为“是”,野蛮为“非”,对“野蛮”的攻伐实即所谓“杀无道以就有道”(《论语·颜渊》)。
庄子认为,我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无不建立在某种“立场/成心”之上,“立场/成心”是衍生“是非”的根源。那么,“文明/野蛮”的分判是否也是出自“成心”?庄子正是通过对“成心/立场”的深入辨析来回应儒家的“仁义之端、是非之涂”的。围绕对“因是”一词的分析,李巍先生对庄子哲学的“立场”问题有如下精到理解:首先,立场的限定不可摆脱(“因是”的必然义);其次,立场的选择不是唯一(“因是”的多元义);第三,立场的封界亦非绝对(“因是”的开放义)。[ 李巍:《立场问题与齐物主旨——被忽视的庄子“因是”说》,《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以此审视“尧攻丛脍胥敖”这段材料,我们会看到:其一,因为存在物在时间、空间、知识、智慧等层面的有限性,以及存在立场的相对性,“此”之所“是”在“彼”看来未必为“是”,尧舜所代表的文明也不例外。其二,存在物“固”有其“然”与“可”之维,即便是“野蛮”的宗、脍、胥敖,在其存在范围内也有其天然之“是”也即合理性。其三,存在者的在世状态无不有限而相对,缺乏“使正之”的终极标准,所以天下并无所谓“同是”或“公是”,“文”或“野”均無法构成人人可欲的共同价值。
可见,尧对三国的攻伐不仅在手段上是不义的,在理路上也大堪商榷,其行为可谓“齐其不齐”或“强不齐以为齐”,不仅未能自知并自省“立场”的天然限度(立场的“必然性”),更没有正视并尊重“蓬艾之间”的存在合理性(立场的“多元性”)。尧对三国的讨伐实即“非人”(以人为非),这种洋溢着傲慢与偏见的施政方式无法通达更理想的政治。庄子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齐物论》)儒家的“明辨是非”根本无从“明辨”,是非之见愈彰明,大道就愈隐闇、世道愈樊乱。因此,庄子说“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齐物论》),既然“十日并出”那样的光耀只能生成混乱和犹疑,圣人应限制并消解之,才能超越“立场/成心”的必然限定而尊重他者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
在强行推行仁义之道的过程中,因为对其灾难式后果不无预知,尧难免会产生“不释然”的戒惧之感。也就是说,尽管尧的目的是推行仁道于天下,但对于宗、脍、胥敖三国的君民来说,他们或许根本无法“心悦诚服”地接受之。这就产生了一种悖反:仁道之爱可谓尧之本怀,灭顶之灾则为三国之实际。对此良好意愿与悲惨结果之间的悖离,庄子有寓言曰:“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蚉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人间世》)正如“爱马者”,“爱人者”也应意识到“仁常而不成”(《齐物论》),力免将温润的仁爱“常理化”,方可有所“成就”或“成全”。“常理化”便意味着价值或思想的“固着化”,或者说原教旨主义化、意识形态化。《齐物论》深叹“君乎,牧乎,固哉”,便寄托着庄子以“齐物”之理“活化”尧舜治道的意图。在庄子看来,尧舜治道的本质即为“藏仁以要人”,通过对仁道的怀藏而要结或笼络人心。在这里,“藏仁”是手段,“要人”是目的,而“仁”之工具性的凸显也便意味着仁爱的异化、价值的弥散,可谓将仁道“常理化”或“固着化”的必然后果。正所谓“大仁不仁”,真正的仁者并不“自以为是”而会尊重对方,并不“怀藏仁义”而视之为本然价值。
那么,庄子何以反对“仁”之“常”或“藏”而提倡“不仁”之“大仁”?王博先生说:“仁爱是有‘我’的,而且也是以‘我’为前提的。不仁则意味着对万物的一视同仁以及‘我’的放弃,而这就是齐物。”[ 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7—118页。]可见,有“我”与否是其中的关键。“藏仁要人”者,有“我”之境也;“大仁不仁”者,无“我”之境也。尧舜治道的根本缺陷便在于“有我”: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蚉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
“日中始”的名号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炙热的“十日并出”,他为肩吾提供的正是“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这种闪耀着“光之暴力”的统治方式。在这句话中,“己”与“人”的对立是很明确的——“己”是法制政令的创作者,“人”是法制政令的承受者,“人”必须听信并遵从“己”的号令,才能在世间合理存活。在庄子的视域之下,哪怕是“圣人”,“己”也并非完美无缺,而是“有限性”的存在。正因如此,尧舜等儒家圣人在《庄子》中从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在《逍遥游》篇,庄子笔下的尧已然产生了“吾自视缺然”的珍贵觉悟,遗憾的是,其“让天下于许由”的动机依然是试图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来治天下,这种“缺然”的觉悟尚不彻底。庄子认为,如果意识不到人类在智慧、知识、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天然限度,我们就易于一厢情愿地以己为是而强人从己、推己及人。[ 无独有偶,《尹文子·大道下》云:“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倡导以“圣法之治”替代“圣人之治”,亦对“圣人”的有己性、私意化、成心化等弊端颇为戒惕。]如此,圣人所面对的作为民众的“他者”实质上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面目不清的“童蒙”。庄子反问道,飞鸟、鼹鼠尚且本能地知道它们应该如何生存,难道人连鸟兽都不如吗?
总而言之,庄子的“齐是非”既揭示了“己之所是不必为是”,也说明了“他人之非不必为非”。通过“己之所是不必为是”,君王应该自觉限制自己的知识欲与权力欲;通过“他人之非不必为非”,君王应该尊重并包容他者。对于君王来说,“齐物我”无疑是极为必要的:只有意识到了“我”的限度,以及“物-我”之间的同与异,才能避免“我”对他者的侵犯或伤害:无论是《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还是《齐物论》所言“吾丧我”,都道明了对“我”的超越诉求。“无己”、“丧我”意味着对“我”的否定或限制是通达“齐物我”的最初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永远只是以“我”的立场去观察万物、思考万事;“无己”、“丧我”之后,“至人”或“吾”则能默会到“物”的本然状态与自在价值;惟当如此,舜才能避免“未始出于非人”的是非之见,尧才能对宗、脍、胥敖的异样存在感到“释然”,走向“自我中心的搁置与换位,对他者的倾听与敞开”[ 赖锡三:《道家型知识分子——〈庄子〉的权力批判与文化更新》,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第285页。]。
陈少明先生认为,现代庄学未能充分回应与“齐是非”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以抽象信念为出发点的原教旨主张”是否合理?其二,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有无“公认的标准”?[ 陈少明:《启蒙视野中的庄子》,《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通过上述讨论来看,庄子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庄子“齐是非”的目的,正在于破除“原教旨主义”的迷妄以及“普遍真理”的狂妄。在“齐物”的政治批判进路中,庄子反对“入于非人”的价值傲慢与权力专断,而倡导“出于非人”的集虚与宽容。
三、“齐之以道”的政治建构
通过上述对“齐物”与政治之关系的描述,可知庄子对政治的批判并非仅为感性的情绪宣泄,更是出乎理性的冷静剖析。就像“庖丁解牛”那样,庄子精准地触探到了儒家式权力结构、政治图景中的罅隙与骨结,并对之进行了细致入微、游刃有余的剖解。那么,在政治解构之后,庄子是否有更进一步的理论关怀,或者说“建构”一种理想政治的努力?王安石说庄子的目的是“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24页。];徐复观先生说庄子对政治的态度并非一味“否定”,而是“在积极方面,要成就每一个人的个性;在消极方面,否定一切干涉性的措施”[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第373页。]。如果说我们在上文中主要论述了庄子对“天下之弊”或“干涉性措施”的否定,接下来,我们将展开对庄子之政治建构的论述,其核心问题便是:“齐物”在何种意义上意味着可将天下“归之于正”并积极地“成就每一个人的个性”?
在庄子那里,除了“言”之维度的理性反思,“齐物”观念更需要“道”之本体的证成。儒墨之是非为何“樊然淆乱”?尧伐三国为何“不释然”?“以己出经式义度”为何不出于“私”?正所谓“道隐于小成”,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成心对大道的遮蔽。如欲从根本上解决之,就必须依恃对“道”的诠解与体认。庄子云: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
若从“道”的视角去观照万物,小大之别、美丑之异均被消融;所有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存在物无不在道境中自由敞开自身:“物物独立于道中,物物共生于道中”[ 叶海烟:《庄子的生命哲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21页。],无所谓成与毁、是与非、大与小、美与丑、常与怪,彼此之间和谐共蕴、通达一体。可见,这里的“道”并非创生并规范一切的宇宙实体,而仅意味着“虚而待物”的开放境域。在此境域中,万物的存在是“相异”的,是“相关”的,又是“相含”的[ 吴光明在描述庄子的“自缠”论理时,认为“自缠”的要素“要相反,更要相关,又要相含”(氏著:《庄子》,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64页),本文化用了这种说法。],而唯独不应是“相非”的。
孔子曾以“齐之以礼”来反对“齐之以刑”(《论语·为政》),鉴于庄子“齐物”的理据在“道”,由之推演出的治道便可称为“齐之以道”。在此意义上,“齐物”又不无“齐民”之意味[ 对于“齐物”的“齐民”意涵,《文子·自然》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达:“故圣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为其所能,周其所适,施其所宜,如此即万物一齐,无由相过。”依照文义,这里的“万物一齐”即“牧民”的结果,也即使民众“各便其性”的状态。]。“齐之以道”与“齐之以礼”的区别在于:“礼”指涉着对贵贱贤愚的人为区分,“道”则意味着对小大美丑的天然肯认;“礼”源自“圣人”之制作而有立场之限定,“道”蕴示“万物”之自然而无容私之困扰。庄子的“齐之以道”并非“齐其不齐”,而是“不齐而齐”,透显着对个体之独立性的肯认,对个体之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不齐”之“差异”的彻底维护。这样,庄子哲学衍生出的是对“多元主体”的真正接纳,而倡扬以“相尊”、“相蕴”为基础的“平等”观念。庄子说:
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齐物论》)
在“道”的“脗然自合”之中,一切由“礼”而衍生出的“纷乱”都被悬搁[ “滑湣”即“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老子》第三十八章所谓“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即便是礼制体系中“皂隶”这样的低贱卑下者,也有其不容忽视之尊贵在,也有其不容蔑视之尊严在,吁求的是“相尊”;与此同时,在“道”的“通达为一”之中,一切由“礼”产生的“是非判断”也会被消弭殆尽,“万物尽然”意即对万物之存在独立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肯认,含藏的是“相蕴”。简单言之,“相尊”意味着对他者之独立性的尊重,“相蕴”意味着对主体之多元性的肯认。这样,圣人威权、礼教传统在政治建构中便不再居于核心地位,一种崭新的充满创造性与想象力的政治境域便有可能通过主体之“自己”、“自取”而萌生并蕴成。
庄子相信,以此相互尊蕴的精神对话并倾听、行动并创造,人们才能摆脱一元价值的束缚,消解绝对权利的戕害,社会生活或公共空间才能避免僵化或固化为沉浊的“樊笼”,而蜕为如“天池”般温暖而惬意的意义世界。可以说,“齐物”表征着一种崭新的政治哲学的路向,这种政治哲学以挺立主体的独立性为起点,以激发主体的创造性为追求,以维护主体的多元性为鹄的。这样的“齐物”关怀,将具有反思、对话、行动等创造能力的“主体”[ 这里的“主体”显然不是“主—客”(“彼—此”)二元对立中的“主体”,也不是儒家的“道德主体”。按照毕来德的说法,庄子的“主体”是“在与虚空和万物的来回往复的关系中生成变自我更新与赋予意义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定义我们与自我、他人及事物的关系,并引发更自由的、更恰当的行动”(参见毕来德:《庄子四讲》,第131-132页)。赖锡三认为,庄子的“主体”并非同一性、实体性的封闭固我,而是通达于气化流行、物化交融的不断变化流动,并朝向丰盈差异化的无我之我,即多元流变、不断延异的日新主体(赖锡三:《道家型知识分子——〈庄子〉的权力批判与文化更新》,第466页)。本文认同毕来德与赖锡三两位先生对庄子之“主体”的界定。]视为政治的价值源泉,显然溢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视整体、向往一统的樊囿。
可惜的是,尽管已经萌生了上述“大有迳庭”的政治意识,以及“与天为徒”的独立理念[ 《庄子·人间世》云:“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这种闪耀着平等独立之光的生命意识正是庄子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或归宿之所在,朱熹即明确称之为“不可行于世者”。],受制于时代思想的客观氛围,庄子并未对王权的正当性问题提出过任何明确质疑。在庄子那里,自由而独立的多元主体对理想政治的自发构建,依然不可避免地与圣王的思与行关系密切。只不过,圣王的思与行亦应以“相尊”、“相蕴”为价值基底: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
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圣人应该“立乎不测,游于无有”或“游心于淡,合气于漠”,既不限定自己的立场,也不拘束自己的心神,才能去除“名”的负累(有莫举名)、“私”的困扰(无容私),从而“放宽一切标准而平等扩大之”[ 钱穆:《庄老通辨》,北京:九州出版社,第129页。],最终抵达“使物自喜”的理想政治状态。
吴肇嘉先生说:“庄子理想中的圣人之治,以根据的内在性为起点,而以作用的普遍性为终点。根据内在,故不会自我异化;作用普遍,故不致有所不及。”[ 吴肇嘉:《庄子应世思想研究》,第120页。]庄子的“齐物”观念即链接“内在之根据”(游心于淡)与“普遍之作用”(顺物自然)的“枢轴”:“齐物”既是“独与”的超越认知,也是“相与”的政治理解;既能挺立“真我”的生命观照,也能通达“大我”的政治关怀。作为一种政治结果或理想的政治状态,这里的“顺物自然”、“使物自喜”与《齐物论》开篇南郭子綦所述的“天籁”遥相呼应: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齐物论》)
理想的政治正如“天籁”,“圣人的政治活动,使得个人的逍遥变成了个人自己的问题,而不再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问题”[ 陈赟:《逍遥境界的政治向度——〈庄子·逍遥游〉“知效一官”章的政治学解读》,《学海》2009年第2期。]——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真正的“使其自己”、“咸其自取”,既不用承担社会、政治的外在压力,也不用“引领而望”,期待“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人来解救或建构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多元主体”还可与“天籁”式的政治境域发生“通达往复”的关系,最终成就的不仅是个体的发抒,也导向“吹万”这种和谐而生动的社会共同体。
有趣的是,通过“风”的比喻,我们再次看到了庄子与孔子或儒家之间的某种对话。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与“小人”之间是教化与从化的关系,在圣人天地之德的风化中,“草”只是随风摇摆,屈从地朝向同一方向,被动地展现统一姿态。与之相比,庄子的“天籁”之所以能成就“小和/大和”的和谐情状,除了“泠风/飘风”的吹拂,实际上更依赖“万窍”自身——它们呈现的是“鼻、口、耳、枅、圈、臼、洼、污”等异状,发出的是“激、謞、叱、吸、叫、譹、宎、咬”等众音。“使其自己”、“咸其自取”表明,“万窍”之“自”在“小和/大和”之境得到了天然的畅发,可谓各各呈现了自身,也各各实现了自身。因此,在政治所指涉的公共空间中,圣王如果固执于自己的主体性,民众的主体性就会被压抑或消解;圣王如果“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民众的主体性就能得到释放与成就。在庄子看来,正如万窍之畅发可以蕴成畅达美妙的“天籁”,民众主体性的释放则能通达最为良善的政治秩序。
总而言之,“齐物”并不预设任何道德价值或伦理观念的优位性或真理性,因此能够超越“彼是相非”的“是非/文野”之见以及“师心自用”的知识、价值或权力专断;“齐之以道”并不主张“仁者爱人”的情感表达或“推己及人”的主观志愿,从而可以免除“爱有所无”的情感落差或“十日并出”的惨淡结局。面对“齐之以礼”的政治进路在动机、价值、理想、效果等层面所可能导致的弊端或危殆,“齐之以道”试图对之进行曲折灵活、细致入微的疏瀹,以从根源处杜绝价值观念的一元化与成心化,避免权力意识的容私性与专断性。在政治模式的建构方面,“齐物”的政治视界则体现出开放、流动、多元的特征,这些语汇意味着:在秩序与生命之间,庄子并不主张以“某种”秩序来规范或宰化生命,因为,“生命”的独立性与多元性并非任何现成或约定的秩序所能匡缚;“生命”是“秩序”的创造者,而非“秩序”的服从者。对于“秩序”,我们宜乎采取“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齐物论》)的“两行”或“随成”态度,才能走出对“秩序”的依赖性利用,摆脱对“秩序”的规约化迷恋,而在自取、自在、自喜、自适的“逍遥”体验之中将“秩序”的至高价值——尊重并成全“生命”——开显出来。
四、结语
在《庄子》内七篇中,《人间世》的政治批判意味最明显,《应帝王》的政治建构特征最清晰。虽然《人间世》与《应帝王》明确体现出了庄子的人间关怀与外王向度,若仅就这两篇材料而叙述庄子的“内圣外王”,在理路上并不饱满。这是因为,《人间世》的政治批判多为“表象”,《应帝王》的政治建构流于“形式”。我们更应追问的是:庄子之政治批判的内在理路是什么?庄子之政治建构的理论根柢是什么?答案即隐藏在《齐物论》中。
庄子“齐物”观念的“政治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既呈现了政治批判的内在逻辑,又开显出政治建构的本源理据。通过对此内在逻辑与本源理据的抉发,庄子政治思想的模糊面目会变得清晰,其贫乏形象也渐趋充实,从而有助于矫正并补足我们对“齐物”以及“庄子哲学”的惯常或固化理解。对于庄子哲学研究而言,“精神境界”或“生存美学”的经典范式可谓精妙绝伦,但绝非完美无缺,因为,这种范式无法整全呈现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的饱满理型,从而遮蔽了庄子哲学的应世性格与人文精神,也就难以据之以回应时代挑战并创发时代新义。实际上,从“生命”进路理解“齐物”观念或庄子哲学不惟不应排斥,反而内在吁求着对它的政治解读——“政治”本身就是隶属于生命“之内”而非“之外”的重大问题。而历代那些业已注意到庄子之政治关怀的学者,比如郭象、王安石等,无不着意于将庄子的政治思想导入儒家途辙,不惟弱化了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更遮蔽了他的独特的政治建构理路。
在当今学界,很多学者业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展开了坚实的研究:赖锡三先生致力于阐述庄子的权力批判与文化省察而建构“道家型知識分子”,积极主动地反思当今时代“诸如寓言、权力、他者、伦理、生态等等跨文化的普遍难题”,以“将《庄子》放入当代的生活世界,开出道家对今日‘人间世’的治疗药方与更新活力。”[ 赖锡三:《道家型知识分子——〈庄子〉的权力批判与文化更新》,第ii页。]以对《逍遥游》、《应帝王》的讨论为主,陈赟先生倾心于在先秦政教思想的宏观背景中揭覆庄子政治哲学的精义[ 陈赟的此类文章主要有:《逍遥境界的政治向度——〈庄子·逍遥游〉“知效一官”章的文本学解读》,《学海》2009年第2期;《“尧让天下于许由”:政治根本原理的寓言表述——〈庄子·逍遥游〉的内在主题》,《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混沌主题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庄子·应帝王〉与儒家帝王政治之批判》,《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非人之人”与庄子的政治批判——以〈应帝王〉首章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以期复原并凸显其“内圣外王”的哲思本怀。本文对庄子“齐物”观念的政治意蕴的粗略阐发,也是对赖锡三、陈赟先生的研究理路的某种呼应,以期通过哲学视域的必要调整,将庄子哲学的理论复杂性与思想创造性周遍地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