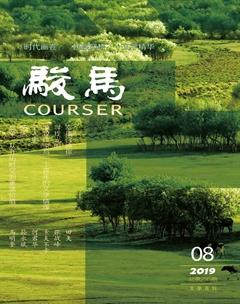意象:从开拓时空到重建价值
马明奎
冯秋子《寸断柔肠》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是:意象作为艺术符号实现了开拓时空和重建价值的功能——就前者言,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意象体系的营构;就后者言,叙述也不再是意象实体的连接,而是一个价值生成的过程。在冯秋子这里,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同一从而完成了艺术本体的建构。
一、感觉化
把一个过程性叙述铺写成立体境界,营构了一个融历史、社会、心理及感觉为一体的意象世界,确切地讲是完成一种艺术本体的建构,是冯秋子《寸断柔肠》推进散文艺术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换句话说,过去散文理念中的叙述,记叙描写议论和抒情各司其职、自成景象,它们针对相对单一的叙述对象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艺术任务从而进入表情达意。就像一块拼板,基本线路和格局是记叙,细部用描写,间有抒情、议论甚至说明,文章形成集成电路板一样的纷繁复杂景象。
冯秋子重新回到意境,回到感觉(意象),回到心理逻辑。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夜晚会偶然响起一种古老的声音,由远到近,如沙尘暴冲散了狼群。但是人马厮杀、兵器碰撞的日月殒灭的时候,那些凄厉的声音就已经成为古战场的童话了。(冯秋子:《寸断柔肠》,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3页。)
这段语言描写一种声音,她用了三个意象:沙尘暴冲散狼群,人马厮杀、兵器碰撞、日月殒灭的古战场,童话。
这三个意象是三种独特的感觉,但它强调那种声音的恐怖凶险、古野荒凉和空幻不测,强调历史感和神秘感。这三个感觉又不是胡乱横陈和杂相拼凑在一起的,而是依循一个秩序:从听觉到视觉再到感觉。这不仅拓开了一个从空间到时间、从现实到历史、从境界到神意的诗性境界,尤其是衍生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和心理的价值空间。这是一种存在,一种灵魂俯贴着大地,耳朵和鼻子乃至整个生命感觉无微不至地体察、呼吸着宇宙万物的一动一静的,逼真而富有生命感的诗意存在。事实的世界从时间和感觉上被延长、拓展、加载了,灵魂就从这种存在中彰顯出来。
这三个意象既不可拆离也没有客观逻辑。但是拆掉一个意象,整个感觉空间就坍塌了;但是如果硬性地从客观社会历史的文化意蕴或题材的物质材料性上对其实施组装,则不仅是乱无头绪的,也是光怪陆离的。这段叙述的主体形象是“一种古老的声音”,是遮盖了“我”的整个童年、黑夜里经常出没的鬼魂,是与沙漠的童话和草原的黑夜深刻同一的存在本身。如果不是诉诸感觉和心理,而是客观坐实地描写,那就从科学的意义上走失神意而成为一堆心理碎片。
冯秋子把整个客观生活材料感觉化了。不仅传神尽意,更鲜活、更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而且回归感觉,营造氛围,营构意象体系,其营构之式就是心理逻辑,就是作为感觉的意象其意脉的自然迁衍和形态蜕变。一旦如是,意象建构就从客观性和事实性衍入诗意和价值,衍入人之于世的那种呼吸感应、相关相契的境界,艺术建构也就自然提升为一种价值重建。
二、意象化
冯秋子的叙述能力是极强的;如果不是负有艺术审美的承担,仅止于表达或概括,她也肯定是一个意向深潜、表达简约的高手——
歌是歌,人是人。人们再也顾不上唱那些麻烦的歌,也顾不上恋爱呀、死亡呀一类折磨人的事情。唱旧歌的人,随同旧歌一起被埋藏。有人解决现世,解决生存,跟着他,就是跟着革命。前世和来世压迫得我们太苦了,实在是没有缘由的事情。(《寸断柔肠》,第6页。)
这是那个特殊年月里中国人文化心理普遍浑沌的抽象概括:斩断生命与历史、与文化的关联,截断物质性现实生存与灵魂和精神的价值性关系,急功近利,简单冲动,人的存在成为失却神意的、走向孤寂并将最终消失于漠漠宇宙的白矮星。冯秋子在表达这一意向时会其意而撮其神,直言其事,历练简约到无以复加;但她还在做进一步的工作,那就是使严整凝练的春秋笔法发生错置,把已经错乱的客观事实纳入感觉空间,形成某种价值间离,造成时空超越和意义拓展的效果,于浓郁的心理氛围中将意象体系回复为意境。
我问地下到底有多少鬼,有多少是冤鬼?
他说爸爸杀的都是该杀的人。
我说冤鬼魂灵不死。
他说爸爸的战友死了多少多少永垂不朽。
我说我害怕,永垂不朽是不是就是魂灵不死?
他说他十二岁离开家出去当了一个小兵。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小离开呢?
他说老家离这儿两三千里。(《寸断柔肠》,第8—9页。)
这是两条由意象系列构成的(每一个语句就是一个意象)不同的心理线索的错接。一条是孩子的“我”的心理:纯真、善良,对世界充满奇思异想,更有着对于残酷现实的恐惧和警觉。“我”所追问的是灵魂、地狱和这个世界的苦难,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思考;另一条是成熟的社会主体、作为过来人的“爸爸”的心理:有着清晰坚定的政治观点和价值理念,又确定不移地认证着历史事实。“爸爸”所关切的是曾经的苦难和斗争,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观点。这两个意象系列、两条情感逻辑和两种生命境界交织着却错接着,本质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的互相彰显和互相开拓:前者鲜明地映照出后者的残缺和冷硬。这里,发生了价值基点的挪移:从“爸爸”的政治历史观点向着“我”的人性和存在观点的挪移。这两个意象系列既勾勒了“爸爸”和“我”两代人不同的人生轨迹,又将各自的存在状态意象化为呼之欲出、令人有切心之痛的价值幻境。本质地讲,这是一个价值幻化的过程。
意象化并且价值化是冯秋子艺术建构的根本方式。
一般地讲,除开上述错乱春秋笔法、离间价值空间之外,她还在两个方法上实现着这一方式。一是依循着情感逻辑构织那些独特而生气灌注的、储满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的细节,将地域文化特色的普泛客观描写变成一些细节从而意象化、价值化;一是于事件叙述的逶迤流走间拈取细节,信手掘凿、拓展心理空间从而映现价值趣向,于价值生成之际回归意象化。前者是从意象化到价值化,后者则是从价值化到意象化。作者的艺术触觉始终飘泊于意象与价值的流变过程中,一如她自己所说:“我始终在路上。”
冯秋子对于塞外边荒的地域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蒙古民族)是非常熟悉的,但她不写特别离奇的故事,也不专事曲折情节的营构,相反她把这样的叙述事件浓缩了,粗糙化了,甚至把过细过多的材料性打磨掉,留下一些耐人寻味的、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坚硬细节。她的艺术之烛始终灼痛着人的心灵和情感而不是客观事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写三个细节:弥满了草原之夜的古老声息(鬼的歌);姥姥的歌及年轻女人们的歌(人的歌);祈祷。三个细节演绎了“我们”生存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生存的地方作为一种存在并不是某个确定地域,而是人心版上的三处深刻印痕。这样,题材整体地意象化也抽象化了;由于滤掉那些滋赘冗繁的现象性描述,全部生活得以价值化处置,结果是存在从生存意义和历史事件基础上的价值飞升。
《额嬷》是典型的篇子。写一位蒙古族老人钦格勒,其切入点是她的“生”,那种九死一生、不屈不挠的生,所谓“生不草”。这应该是一些事件,一场生殖运动和一种生命冲动。但是冯秋子把它细节化了,强劲地突出那种爱的意向,那种无怨无悔、不消不歇、不求不解的对于丈夫的爱。然后是“养”,养育自己的和别人的孩子,于生存的艰辛中领承最高者的爱——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着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個宁静。突然,从她胸腔里流出悠远跌荡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寸断柔肠》,第38页。)
最后是额嬷的儿子巴耶尔的死。一个母亲怎么可以杀死自己的儿子呢?那是因为:她心里有最高的爱,有大于母子之情的价值存在;由于额嬷的“杀”,巴耶尔的罪孽得到清洗,灵魂从俗世的暗昧中得以澄明。爱,是最终也要实现的。生、养、杀——那么义无返顾的爱,那么艰辛卓绝的养,又是那么坚定明确地杀;最基本的生命繁衍和生殖运动构成的现实人生就细节化为一些蒙上历史风烟的日子,意象化为从爱中领承爱、由于领承爱而超越爱、最终因爱而成圣的价值人生。通篇看来犹如一块凝结了血泪因而殷红暗紫、珠光宝气的胭脂宝石,通体透亮的意境里氤氲着三缕暗紫的血色,整体上象征了那个古老民族苦难而庄严的存在。
三、价值化:细节-心理-价值
冯秋子写感觉不是诉诸心理学或修辞学术语,而是时时处处尊重感觉,注重细节,在心理与感觉的神意流动之间嵌入细节从而形成巨大的意象空间,营构一种“思性”存在从而实现艺术本体的建构。这里又有三法:一是地域土语的运用,一是嵌入地域生活细节,一是把细节拉回到当下的心理现实。
土语的运用肯定不是大众化或通俗性的努力,更不是那种故意把话说得结结巴巴的语言堕落。而是一种历史感和事实性、一种文化和生命的逼真性追求。家乡人读她的作品是会掉泪的,少半是由于这些土语。比如“生不草”,“袄补丁”,“日怪”,“拉下大疙蛋”,“呆眉怵眼”,“灰塌塌”,“没甚起色”,“干不龇冽”,“臭扒牛”,“干牛粪片片”,“燎泡”,“荨麻”,“甜苣”,“沙蓬”,“浮皮潦草”,“麻烦个甚”,“圪转”,“圪混”,“一年来天气”,“黑瞎瞎的”,“雀儿”,等等,这些土语汇成一个历史堆积层,一种文化存在。它蕴含的是塞外边地那种苦寒而深远的人生况味,那种走遍世界也再找不到的,艰辛而诙谐、厚道而明澈的深挚人性,是那片土地特有的实在和亲切。作为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作为一种材料和质素,它们本身就生成着意境。
其次是细节。冯秋子的细节非常生活化又非常意象化,它是一种超现实性联想和幻觉,一种心理搭建方式。这些细节往往形成叙述平面上的一个个凿洞而深嵌着对于历史和生活的独特领悟。
看着红扑扑奔突的日头,和晃晃悠悠的神山,我常常觉得,这个日头跟神山,很像自己家墙角架上的笼屉,和那把踩上去就要散架的烧火板凳。每天出门前,我踩着板凳,踮着脚丫,从笼屉里面够出少半块窝头。无限美好的早晨就从这块莜面白面玉米面捏成的“三面”窝头开始。(《寸断柔肠》,第45页。)
表面看是用孩子从笼屉里够窝头这一细节比喻人与日头和神山的活动关系。但是这个细节的嵌入使早晨上学这一铺紫陈红的叙述平面凿入了非常具体鲜活的生活内容,凿入尤其令人欣悦而感伤的生存况味。“日头和神山——笼屉和板凳——窝头和早晨”这一构式不再是一般过程性叙述,而是一个意象蜕变的立体流动过程,在氤氲而成的意境里,价值和意义随之改变。“笼屉和板凳”不正是横亘于物质现实生存与神意灵魂存在之间不可逾越的价值阻塞吗?然而它又是一条必由之路,是价值存在的入口处:不经过如此艰难苦恨,“红扑扑奔突的日头”就失去她光明临照的现象世界,“晃晃悠悠的神山”也就宝光锐减,神意顿失,黯然神伤。
第三是在一个细节上凝滞,衍入情感和联想,再引回当下的心理现实中来。这种不断帘出的技法不仅是一种心理辐射或时空反弹,而且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价值追寻,一种历史意象的感觉化和当前化,一种当下意象的历史化和心理化。
我说:“你看见我的时候想什么?”
他说:“你跟着我干什么。”
父亲离家以后,我常常端详那张刚解放不久他跟妈妈结婚照的相片,母亲身穿列宁服,稍微侧过头,望着前上方;父亲身穿军装,正对前方。非常奇怪,我变换到哪个角度,父亲都跟着我移动,就像黑夜里月亮跟着小孩往前走、往后退,他的目光总能望见我……那时候我不懂得这是他当时盯住照相机镜头的缘故,一门心思在想:不能想坏事也不能干坏事,父亲能看见我。(《寸断柔肠》,第183页。)
当下的场景是“我”与父亲谈论过去,然后是父母结婚照片的细节。作者在这个细节上凝滞笔触,然后渐渐衍入心理,又衍入现在时当下心理。“那时候”是个引领词,由于这一引领,后面的心理内容就变成既是历史事实又是现实心理这样一个双重价值塑造。它再一次把父母的结婚照片所凝结的那种时代的神圣感和存在的庄严感加以强调,写出这种庄严神圣对于当时乃至现在的“我”的看管和监护;但是,野蛮和荒诞正是从这种神圣和庄严里生发的:父亲被游斗,一个可怜的孩子无力解救这种苦难,“能做的仅止是看见伤害,并为之疼痛,还有就是铭记它”。这不就是那个时代的庄严神圣里深刻的价值荒诞吗?
四、从意象到意境的回复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冯秋子从感觉化到价值化的这样一个审美心理过程,意象是其中介——亦即依循心理和情感的逻辑撷取细节从而建立意象体系,实现价值和审美。其最重要的方式是错置意象系列、形成细节群落、铺陈土语堆积层加上开拓心理时空。意象体系的建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之间、物质现实性生存与灵魂神意性存在之间的价值追寻过程,其终极旨趣是艺术本体化的实现。
冯秋子的散文使我不禁想到这样一个对比:当那些龌里龌龊的所谓作家们像饺子一样投入滚沸的市场海洋时,他们把神圣艺术普世化、庸俗化甚至垃圾化,到了身体作家之流就彻底呈示了依循俗世法则、从神性价值体系逃亡的无能和软弱来。冯秋子不是这样:她依旧走着把庸俗和日常神圣化、价值化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坚贞和不屈,一种存在诗意化和人性价值化的哲学努力。这是我们这个喧嚣骚乱的世界里一点神性和光明的依恃。它肯定是艰难的,但绝对是理性的。
我们同时注意到冯秋子艺术本体建构的某种旨趣:意境的回复。她遵循着感觉化—意象化—价值化这条路走来,末了只能是意境的回复。而意象化是关键。这里的意义在于:她使我们又一次想到东西方以及古典与现代艺术之间打通或连接的可能。冯秋子意象建构的前半截主要是在撷取细节、组织意象从而开拓时空,后半截是通过感觉化、心理化从而重建价值。这是一个从客观向主观、从世界到心理乃至由意象到意境的艺术努力——不是从客观生活,不是从哲学观念,也不是从艺术典范,而是心理和感觉与意象及其体系此二者的同一进而完成艺术本体的建构——这就是意境的回复。事实证明,意境不是单一的客观生活情景在艺术显影剂里的不断显影,而是——人性光辉照耀下的生命复苏和灵魂彰显,是意象底膜在情感和心理版样上的价值投影。意境完全有可能在现代艺术和文化中修复,并且成为人性济渡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