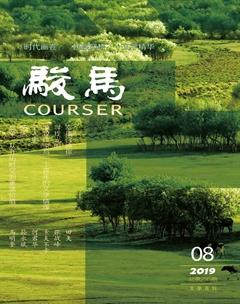寻找光明
张战峰
最近,金刚总是失眠,而且还咳嗽,前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半夜睡着了却头疼。天还没完全放亮,他只好躺在床上发呆,两条粗壮的胳膊吊在脑后,一条条青筋如蚯蚓般爬在皮肉上,他狠狠地伸了个懒腰,一双大脚蹬出被子,黝黑的身体赤条条露出来,呈现着肌肉刚劲的棱角,一股雄性荷尔蒙瞬间被荡起。他实在睡不着了,干脆到宿舍门口抽支烟。
金刚是在小煤矿上干活,睡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人挨人睡着,冬天挤一挤还暖和,但夏天不通风,又热又臭,各种的臭味,汗臭味、臭脚味、狐臭味,闻久了也就习惯了,嗅觉失灵是很正常的事。最不能让金刚习惯的是,半夜总有人在他刚睡着的时候,从他头顶上迈过去再走到门口,然后听到一股急促的水声持久地冲进地里,吵得他愈加失眠。更讨厌的是当这个人再次经过他头顶的时,会有一滴液体滴漏在他脸上,他真的很想骂一句。
金刚以前是在水泥厂打工,每天就是坐在大机器旁,手提袋子装水泥,等水泥“扑通”一声掉下来,然后将水泥袋扔到传送带上去,工作又累又脏,就算戴了两层口罩,也挡不住漫天飘荡的水泥。一天下来,别说脸上、耳朵里落了厚厚一层水泥,连吐口痰都是泥浆。金刚担心长期干下去,水泥会像砌墙一样把肺都糊住,最关键的还是工资太低,金刚觉得不值得。
三年前,一个老乡非要拉他到煤矿来干,说挖煤挣得多,而且有额外补助,一年能挣五、六万。金刚没见过五、六万到底有多少钱,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跟着来了。到了矿上,他才知道是个私人老板开的窑,环境还不如水泥厂好呢。招工的人对金刚说有这个保险、那个补助的,说得天花乱坠,但口说无凭,连个带字的纸都没见过就上岗了。一个小青年给他们随便讲了讲安全常识、操作流程、逃生方法,而且讲得太快。金刚也记不住,他想好了,就跟在班长后面,跟着领导混肯定没错。
真正到了下井时,队长怕他们几个新来的不敢下,就气势张扬地说,咱这个工作很光荣、很伟大,咱挖出来的东西不叫煤,叫“乌金”。啥是“乌金”,那就是黑色的金子,是国家发展工业化的粮食,啥是工业化咱也不说清楚,反正发电需要煤,炼钢需要煤,制造水泥也需要煤。总之,你就想着,下去一次就能挖一车金子上来,你盖房子就多了一车砖,娶老婆就多了一叠彩礼钱。队长激动地说着,吐沫星子乱飞,一会拍胸脯,一会攥拳头。金刚听得也很澎湃,他听明白了,挖金子比装水泥有用,他开始盘算,挖几车“乌金”就能把债还完,再挖几车“乌金”能把新房盖起来。
“咣当”一声,金刚和工友们被关进了铁笼子,他突然感觉自己像养肥的猪被拉去了屠宰场,随着“咔嗒”一声带来的失重感,铁笼子越下越深,眼前越来越黑,笼子里没有人说话,只剩下头顶的灯光和急促的呼吸声。
巷道里,巨大的鼓风机轰轰隆隆作响,噪声震耳欲聋,风像海浪一样被抽进坑道里。在工作面上,带着长长钻头的钻机“哒哒”地响了起来,钻头钻进煤层里面,煤一块一块掉下来,煤尘四处弥散着,工友们在工作面上若隐若现。
钻机在金刚手里像一头小野牛,一会就跑偏了,很快他就感觉手心麻痒,端也端不住。班长贴近金刚的耳朵说,钻机跟女人一样,抓得太紧使不上劲,得让它有点松动,把好方向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按照班长的方法操作,钻机果然听话了。工作面上的煤尘越来越大,金刚虽然戴了防尘口罩,还是被呛得直咳嗽,咳得越厉害吸的煤尘越多,他总觉得透不过气来。而班长对煤尘不仅没感觉,反而脱得精光,只剩下大裤衩,熊一样的前胸后背,随着钻机的抖动,浑身都在爆发力量,汗水在他脸上、身上淌出一道道辙,滴到地上渗进煤里。
这一天,大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才从井下上来。金刚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重见天日呀!可天却是灰蒙蒙的,工友们浑身上下都是黑的,衣服上、安全帽上、头发上、眉毛上、鼻孔里,全都布满了黑麻麻、细粉粉的煤尘,只有牙还是白的,金刚已经认不出谁是谁了。
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把白天当成黑夜过的日子,日复一日地钻到黑洞洞的地下,一边挖煤,一边想着自己的新房子和女人。他们在黑色里工作,在黑色里生活,连周围的房子、道路、汽车,什么都逃不出黑色的笼罩。他们常常会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和冒着黑烟的工厂说,挖煤的人才是光明使者,那里的光明是他们用命换来的。说完这话,他们好像从黑暗中挣脱出来了,感觉将来的生活一定很美好,說不定他们也能成为城里人。
金刚不敢想城里的生活,他知道自己没文化,除了种地啥也不会,城里的活他是干不了的。他听说现在工厂里的活都是由机器和电脑做,人只要站在一边用电脑就行了,可他连个短信都不会发,用电脑的活想都不敢想,他身体好,一身肌肉,还是做点力气活容易些。
金刚从井里出来,没有马上洗澡换衣服,他想先歇歇,就蹲在澡堂门口抽烟,一口烟吸得有点深还没吐出来,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干脆不抽了,他把半截烟丢在地上,用脚尖拧灭了烟,背着手去洗澡了。澡堂不大,里外间,外间换衣服,里间泡澡、沐浴。金刚一进澡堂,一股掺着肥皂味和汗臭味的气浪冲到脸上。班长刚洗完澡,光着身子坐在长条椅上抽烟,头发没擦干,一滴又一滴水前脚赶后脚地汇聚在一起,顺着头发往下滚,沿着脸颊一直滴到班长青白的大腿根,又流进了两腿之间的丛林里。班长狠狠地咳了几声又继续抽烟,一直抽到火红的烟头快烧到手指,才将烟头弹出弧线,落入地上的一滩水中。
金刚与班长一黑一白,好像来自两个世界。在这个澡堂里,没人会在意你是黑的还是白的,是光着屁股的还是兜着裤衩的,人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活着从井下回来,活着才是王道。金刚走到柜子前一边脱工衣,一边问班长晚上干什么,班长把两条腿抬起,盘坐在长条椅上,伸了伸腰,打着哈欠说,不知道该干球点啥,喝酒去!
走出矿场不远处,有一条不足二里的街市,每当灯火阑珊时,这里就变得十分热闹。这里以前没有街和市,因为开了矿所以才有了街市,完全是挖矿的人带动了这里的商业,同时这里的商业发展也满足了矿工的业余生活需要。这附近有好几个煤矿,每个矿都有一个老板,每个老板都有自己的靠山,他们各立山头,井水不犯河水,而矿工们并没有门派,他们在这里只想找到消除空虚的解药。
金刚和他的兄弟们是这条街上的常客,他们经常会去一个叫“夜来香”的小饭馆喝酒。小饭馆的老板娘三十来岁,嘴上涂了很浓的红色,像刚咬死过一只活鸡,穿着低胸衫和超短裙,胸前像挂着两只装了水的气球,摆来摆去,裙子把屁股裹得紧绷绷的,好像一颗大西瓜。所有路过的矿工都会眼馋地望一阵,胆子大的还偷偷摸一下,老板娘总是嗲声嗲氣地说,讨厌!
金刚和兄弟们像回自己家一样进了小酒馆,老板娘的热情很快把这群煤黑子烧着了,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老板娘快要挤爆的上半身,有人假装低头捡东西,眼睛却射向老板娘裙底。班长用空杯子敲了敲桌子说,想吃啥先点上,喝上酒再慢慢看!扭头对老板娘说,就照往常的那几样来吧。老板娘应了一声就去准备了。
矿上的男人是用命换钱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埋在井下了,这一点他们比谁看得都清楚,及时行乐是对自己最大的犒劳,酒和女人是最普及的行乐方式。喝醉就忘记了生死,睡过女人的人生才圆满,这是他们的座右铭。与酒相比,他们更喜欢女人,闲谈的时候聊女人,寂寞的时候找女人,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玩归玩,他们最在乎的还是家里的女人,那才是他们叶落归根的地方。他们自己可以在外面乱搞,但谁要是敢动他家里的女人,他们便可以拿命去要说法,这就是他们的法则。
金刚跟着矿上的兄弟,去过几次美发店,但并不是去美发,因为这些美发店的主业并非美发,而是提供特殊服务。小姐也被分为小猫咪、大白猪、野狐狸等类型,不同品味的男人,会选不同类型的小姐,不同类型的小姐价位也不同。金刚只去过两次,不是花不起30块钱,而是在紧要时总想到会不会得艾滋病的问题,所以搞不了几下就败下来了,干脆就不去了。
金刚喜欢到春妹那里。春妹在街尽头开着一个裁缝店,年纪二十来岁,身材丰腴,长发下垂,一天到晚低着头做活,好多路过的男人都会停下来偷偷看。听说她男人以前也在矿上挖煤,在一次瓦斯爆炸中被埋在了井里。春妹在老家也没什么亲戚,凭着一手好针线活在街市上开了裁缝店,帮矿工们缝补工衣,或者帮小姐们改一改廉价的衣服,虽然挣不了几个钱,但混口饭也绰绰有余。
去年夏天,金刚的工裤撕裂了,他没找到针线,就用细铁丝穿起来了,但干活的时候总会扎到腿,所以他走进了裁缝店。当春妹抬起头时,他吓了一跳,春妹的左眼发灰而浑浊,无神地望着金刚,显然那是一只看不到东西的眼,金刚很快就故作镇定地说要补裤子。春妹拿起来看了看,就放在一边,让金刚明天来拿。金刚说,你随便给我缝一缝就行,我一会来取。等金刚吃完饭来取的时候,春妹已经打烊了。第二天金刚来取的时候,春妹把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裤叠得方方正正,递到金刚手上,工裤上还散发着洗衣粉的清香。金刚每天从井下上来,累得跟狗一样,衣服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汗味或臭味都已经习惯了。在这里他第一次享受到女人帮他洗衣服的待遇,激动地站在那里傻笑了很久,他掏出十块钱给春妹,春妹却说这么一点小活咋能要钱呢。
一来二去,金刚和春妹成了熟人。有一天晚上,春妹在街上拦住了金刚,说厨房的水龙头坏了,问金刚会不会修,金刚一拍胸脯说,“包在哥身上。”其实,金刚根本没修过水龙头,虽然水龙头勉强修好了,结果不仅把自己喷得浑身湿透,还把春妹喷成了“落汤鸡”。春妹找了件她男人的衣服递给金刚说,大哥要是不嫌弃就先换上,别感冒了。金刚接过衣服说,你先去换吧。
春妹进了里屋,门却没关上,金刚偷偷地瞟过去,看到春妹白嫩的身体,长发及腰,心里像烧起了火,下身就顶了起来。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腿,走进了里屋,一把抱住了还没系上扣子的春妹,而春妹却平静地接受了,这天夜里金刚没有回去睡大通铺。后来,金刚隔三差五就会主动来帮春妹干点什么活,春妹就给金刚做几个菜,倒一小壶酒。喝完酒金刚就会抱着春妹办点重要的事,而每次办事的时候他都会想到采煤时用的钻机。
快到季度末了,生产任务还没完成,矿上给各班组下达了量化任务,班长一边换衣服一边骂,这帮龟孙子就知道下任务,老子也不是机器,上吊也要喘口气呀!下井后,大家低头干着自己的活,谁也不出声,连女人都没人聊了,只有手中的钻机在哒哒地叫唤。
突然金刚的身后落下一大块煤,紧接着稀稀拉拉地往下落煤,速度越来越快,金刚还没意识将要发生什么,班长大喊一声,快跑,冒顶了!金刚没听到,仍然端着钻机想着春妹。班长跑过去拽着金刚就往外跑,最终还是慢了一步,班长的腿被压住了,金刚憋足了劲儿把班长拽出来,可落下来的煤已经堵住了通道,金刚想到了死,可他不想这么早死。他和班长徒手扒煤,扒到皮开肉绽、指甲脱落,终于刨出一个洞,班长让金刚先走!金刚说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班长使劲儿压住金刚的头,把他的半个身子推了出去,金刚身子出去了,手还拽着班长的手。幸运的是,金刚和班长都被救出来了,不幸的是有五六个弟兄留在井下再也出不来了。虽然活下来了,但班长的半条腿没了,矿上赔了一笔钱,就送班长回了老家。
快过中秋了,矿上给大伙发了二百块钱补助,兄弟们都有点想家了,又吆喝着去喝酒,说好喝完酒再去快活快活,金刚找了个理由溜走了,他去了春妹那里。到了春妹的门口,金刚轻轻敲门没人应,使劲敲门没人应,金刚就蹲下来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实在等不回来,他才唉声叹气地回到大通铺上。
第二天,春妹主动来找金刚。她说,大哥,俺要走了,来跟你说一声,谢谢你一直看得起俺,愿意帮俺这个苦命的女人。金刚怎么留也留不住,后来他请春妹吃了一顿饭,酒后他们回到老地方,进行了一次特别深入而持久的战斗。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完事后春妹对金刚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她五岁时被拐卖,转了好几家,才卖给了以前的男人,但那时候她还小啥也不记得了,忘记了爹妈的模样,更不知道家在哪,只记得是在跟哥哥玩捉迷藏时被拐走的。她以前的男人比他大十岁,对她很好,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她也就死心踏地跟他过日子了,没想到他那么早就死了。金刚问她,无亲无故地回哪里呀?你跟俺过吧!春妹摇摇头没说话,一直流泪。金刚想帮春妹擦擦眼泪,春妹一把拉过他的手狠狠地咬出两排牙印,然后说,俺知道大哥是好人,但大哥有老婆孩子呀,终是长久不了的。他给春妹留了两千块钱,春妹拒绝了。
春妹走了,金刚心里空荡荡的,再加上最近咳嗽得厉害,胸口闷而且喘不上气来,身体也总是乏力,他有点想家了,想起了老婆和孩子。
金刚的老婆叫引娣。他和引娣是通过媒人认识的,见过一面都有好感,再见面时,引娣送金刚一双亲手做的布鞋,金刚送引娣一个带镜子的粉盒,这事就算定下来了。金刚长得并不帅,黝黑粗壮,一看就是庄稼人,但金刚粗中有细,很会体贴人,又喜欢笑,笑起来脸上还有个酒窝。两人交往了三个月,引娣就过门了。结婚两三年,引娣才怀上孩子,村里人都说她是不下蛋的鸡,为此引娣不知哭了多少回。可自从生了儿子春宝,金刚爹娘对引娣的态度极速转变,夸赞引娣会生养,给金家生了大胖小子,延续了金家的香火,是功臣。金刚更是乐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俺当爹了!”金刚对引娣说,俺这辈子就给你和儿子当牛做马,保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小春宝3岁那年得了肺炎,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虽然最后平安出院了,但落下了每到冬天就气喘咳嗽的毛病。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家人刚从医院回来没几天,金刚他爹上房顶晒谷子,脚下一滑从梯子上滚下来,摔断了腰椎,摔破了肺,在医院抢救了三天,还是没救过来,半年后金刚娘一觉睡去再没醒来。金刚是家中独子,爹娘没了,家里空了,本来就不富裕,为了给儿子和爹看病,给爹娘操办白事,欠了很多钱,小日子顿时变得乱糟糟。为了挣钱还债,金刚这才跑出来挖煤。
金刚把电话打到了村长家,请村长叫引娣来接个电话,不一会功夫村长回话说,引娣不在。金刚问,她干啥去了。村长说,哎呀,这谁能知道哩,反正最近总是去镇上,春宝也送到他二姨家了。金刚感觉村长话里有话,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隔日,引娣打电话告诉金刚,她昨天去镇上赶集了,半道上自行车坏了,推着回来的,所以就晚了。金刚听了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安全就好,俺担心黑灯瞎火的别遇上打劫的。引娣嫌他唠叨,就说,行了,别一天到晚瞎琢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想不想知道?
想,当然想!引娣让金刚猜猜,金刚说脑子笨,猜不出来。引娣小声说,俺身上两个月没来红了,大概又怀上了,可能就是你端午回来那几天的事。金刚说咋可能,才五六天就种上了?真是俺的?电话那边停顿了几秒说,金刚,你个王八,你啥意思,不是你的,是谁的?
本来金刚有很多疑虑想要问个清楚,可被引娣这么一问,反倒是没话说了。是啊,不是自己的还能是谁的!于是赶紧补了一句,开玩笑呢,你怎么不懂幽默呢!
放屁!这是幽默吗?你这是骂俺呢!引娣带着哭腔說。
引娣这么一哭,金刚慌了神,感觉有点内疚,引娣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既当娘又当爹,忙了家里忙地里,他觉得不该怀疑引娣,赶紧给引娣赔罪,引娣看金刚认错态度好,也就没再追究。
金刚撂下电话就拉一帮兄弟去街上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兄弟拍着金刚肩膀,竖起大拇指夸金刚,你小子金枪不倒呀,回家才几天就种上了,你女人的地够肥的。金刚被大家忽悠着,心里美滋滋的,他回味着与引娣翻云覆雨的每个片段,给大伙讲女人与钻机的关系,开始高谈阔论地分享床上的经验。
这时,一个兄弟突然站起来,虽然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但喝了几杯酒话多起来,喝到连眼都睁不开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话。他说,别高兴得太早,说不定是谁的种呢!操,老子拿命挣钱养家,那个贱人却给老子戴绿帽子,还生了野种,谁都能看出来不是老子的种,老子还没打她,她就承认了。话还没说完,嚎啕大哭,整个人滑落在满地的空酒瓶上,还不停地说,非宰了这对狗男女不可。
金刚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整夜在床上翻来滚去。老大三年多才种上,这次咋这么容易就种上了,真的这么巧吗?村长为啥说她总去镇上?金刚越想越不痛快。
第二天下井后,金刚一直心不在焉,此时的钻机已经不是女人,而是一挺机关枪。钻机抖动带来的已经不是快感,而是心神不宁的烦躁,他想快点结束这黑漆漆的煎熬,他要问个明白,这种子到底是谁种的。
终于收工了,金刚连澡都没洗,红嘴白牙满脸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村长家。村长隔了不一会回来说,家里没人。金刚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妈的,你要是给老子扣绿帽子,老子不把你们劈开,就他妈不是站着尿尿的男人。说完这通话,金刚摘下安全帽,蹲在地上抽烟,手抖得连火机都打不着,打了好几次,才点着了烟,他吸进去又吐出来,一股清烟在他面前铺展开。他仿佛看到引娣正脱得精光,光滑的脖颈,粉红的耳垂,高耸的双峰,翘起的肥臀,可是抱着引娣的不是金刚,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金刚手一抖,烟头已经烧到了手指,他一边用脚尖使劲将烟头熄灭,一边骂道,妈的,奸夫淫妇,老子不会咽下这口气的。
他刚要起身,手里的电话响了。喂,金刚,你打电话找俺?俺刚才在厨房给春宝洗澡呢,没听到村长叫俺。有些话到了嘴边,金刚又咽了回去。他了解引娣,引娣虽然性格热情、大大咧咧,但绝不会背叛自己,这一点金刚还是有信心的。
腊月里下了一场细细密密的大雪,盖住了整座山和整个村子,白茫茫的世界让人分不清天地,远处冒着青烟的小院,却像暗夜里的海上灯塔,指引着回家的路。村里的路被踩出一片泥泞,一直延伸到村外更远的地方。寒冷又将这泥泞冻出各种模型,车轮印、牛蹄印都陈列在冰天雪地里,无声地述说着被季节囚禁的想念。金刚沿着这条再熟悉不过的村路,踏着“咯吱咯吱”的雪声,三步并两步地往回赶。他终于看到自家的屋顶,他猜想引娣正给他做一碗热乎的鸡蛋面,“上马饺子下马面”,这是老辈留下的传统,想着冒着气的荷包蛋,心里就热乎乎的,脚步不由地再次加快。
引娣在厨房忙乎着和面、擀面、扯面条,她把面条扯得又细又长,像一条细麻绳,喃喃自语:拴住你,拴牢你,看你还走不走!儿子春宝坐在小板凳上,边看引娣扯面边问,娘,俺爹啥时候回来,他给俺买手枪了吗,要是没买可咋办呢?引娣把扯好的面放在瓷盆里,用一条半干不湿的毛巾盖好,看了看絮叨的春宝说,放心吧,你爹最疼你了,肯定给你买了手枪,要是没买,娘不让他进门。
娘俩正说着话,院门咚地一声被推开,引娣迟疑了一下才喊,你爹!
春宝转身就跑出去了,还没看到人,就喊,爹!爹!
哎,儿子!金刚应着声奔向春宝。
突然,春宝定在路中间,两手伸直,两腿张开,脖子挺得直直,摆成一个大字,大声对金刚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
引娣已经从厨房里出来,春宝就狭路阻截在金刚和引娣之间。金刚看着引娣傻笑,我回来了!引娣望穿秋水,终于盼回了金刚,潸潸然泪似珠,滴滴哒哒融化了满院的雪。
春宝看到爹没有交买路钱的意思,急得边跺脚边说,你要是没给我买枪,娘就不让你进屋!
春宝的样子逗得金刚和引娣哈哈大笑,金刚连忙说,买了,买了,回屋就拿给你。春宝纹丝不动,还是坚持要看到枪才让金刚进屋,金刚只好在院子里就打开背包,拿出一挺会发光、能出声的机关枪。春宝立刻冲过来夺在手里,一夫当关的路,一挺机关枪就打通了。
引娣和金刚进了屋,引娣拍拍金刚肩上尘说,瘦了,瘦了!两眼溢出了泪花。金刚一把搂住了引娣,在脸上亲个不停,他刚把手伸进引娣的棉袄里,就听春宝举着枪“哒哒哒”地冲进来,对着金刚就是一通扫射,像战士一样大声喊,你是坏人,谁欺负俺娘,俺就打死他!
金刚被突然出现的儿子吓了一跳,慌乱地赶紧和引娣分开,金刚抱住春宝不好意思地说,爹可不是坏人,爹跟你娘玩呢!然后用胡茬拱春宝的脸,春宝大喊,好扎,好扎!金刚打开背包,拿出好多零食,好吃的東西远比亲爹有吸引力,春宝捧着零食就跑了。
春宝刚出去,金刚就迫不及待地解开腰带,准备脱裤子。引娣赶紧小声说,孩子在,别急,晚上好好侍候你。金刚坏笑而不语,继续将裤子褪下,露出鲜红的大裤衩。引娣的脸烧得通红,心跳得嘣嘣响,手却不由地开始解衣扣了,刚解了两道扣子,就现出深深的沟壑。
金刚哈哈一笑,嗖地从裤裆里掏出一叠钱递给引娣。引娣惊讶得眼睛都直了,她把带着金刚体味的钱放到鼻子前,闭上眼闻了又闻,她睁开眼时,金刚从裤裆里又掏出一叠钱。
引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多少有点惊讶。
好闻吗?
好闻!引娣笑得合不拢嘴。
是钱好闻,还是俺的味道好闻?金刚故意撩逗引娣。
都好闻!引娣含笑似醉地说,头也不抬地一张一张地数,然后吐了口吐沫到手指上,再数一遍,这才压到箱子底下。
第二天早上,出了太阳,天蓝得像被水洗过,引娣早早起床出门扫雪,雪亮得刺眼,晃得引娣睁不开眼。引娣推开院门,正遇上村长路过,她提高嗓门说,村长,这么早去哪呀!村长转头对引娣说,听说你男人回来了,还没起呢,看来是夜里侍候好了吧!引娣没说话,团起一个雪疙瘩,朝着村长抛过去,落在了村长身后。村长哈哈大笑,哟哟哟,侍候了一黑夜,就累成这个样,连个雪疙瘩都扔不动了,金刚攒了一年的劲儿都用上了吧!看把你舒服的,脸上都开花了!等金刚起来了,叫他中午到俺家喝酒去!
不去,俺家的碗还没捂热呢!
嘿嘿,是身子没捂热,还是碗没捂热呀!村长一边说着,一边走远了。
快晌午的时候,金刚才起床,他刚要起身,突然重重地咳了起来,而且越咳越烈,整间屋子都在震动。
咋了,咋了,咋咳成这样?快披上,别着凉!引娣连忙跑进来,一边把被子扯到金刚的背上,一边帮他捶背。金刚两只手用力一撑,坐起来说,没事,可能路上受凉了。
村长是金刚的本家堂叔,又是一村之长,金刚决定去村长家走串走串,去之前他买了两瓶酒、两条烟。村长那可是真热情,一听金刚来了,趿拉着鞋就迎出来,三句没聊完,爷俩就摆上酒咂吧起来了,喝着喝着酒劲儿上了头,金刚跟村长说矿上如何如何好、挣钱多。村长竖起大拇指说,好!能挣上钱最好,别就像村西头的栓柱,钱没挣上,腿还折了,老婆又跟别人跑了。金刚很惊讶,妈的,矿上干活的人最怕后院起火!不过,俺家引娣不会跑,这个俺一百个放心。
村长低头收眉,端起酒杯碰了一下金刚手里的杯说,再新鲜的麦子见不上阳光也会发霉的,男人女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都有七情六欲,你这话可别说得太早,你在外面就没点啥事?金刚难掩尴尬地笑了一下说,俺是啥人,你还不了解吗?
没有就好,来,走一个!村长没再深问下去。
回家的路上,金刚碰见了老光棍刘富贵。金刚兄弟,回来了,回来就好呀,男人回来女人就不会乱跑了。虽然刘富贵说得很小声,但金刚听得却很真切。
自从金刚回村以后,他总觉得怪怪的,人们说话阴阳怪气的,似乎想暗示什么。他走到哪都好像有个人跟在后面,可他猛地一回头,身后又空空的,连个猫狗都没看到,但是当他再往前走的时候,又隐约听到一声半声踩雪的脚步声,回头一看,还是没人,他心想大白天的闹鬼呢?
金刚越来越感觉不对劲,越想越来气,他觉得人们的话里一定有话,是不好明讲出来的话,是想传达什么意思呢?难道引娣真的……金刚的心咯噔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这一提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开始拼命地咳,咳得气都透不过来,蹲在院门口咳了很久都止不住。
引娣领着春宝跑出来,他爹,你咋了?快进屋呀!金刚甩开引娣的手,脸阴阴地进了屋,引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挺着大肚子只好跟在后面。屋里烧得很暖和,金刚一屁股坐在床上。
他爹,你这是咋的了?金刚没有答腔,躺在床上看着房顶,突然又拼命咳起来。他爹,咳得这么厉害,明天去镇上看看吧。不看,死了算了!引娣听出金刚的话里有刺。她冲到金刚眼前,指着他说,每天好吃好喝供着你,咋还侍候出毛病了,说话间,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
一晚上两口子都没有说话,引娣安顿春宝睡下,就坐在床边默默地流着泪。金刚躺在床上假装睡觉,但一会就咳得坐起身。引娣忍不住过去帮他捶背,金刚反而咳得更厉害了,引娣只好轻轻地摩挲,引娣给金刚放了一个枕头,让他靠在床头,这才顺过气来。
金刚在矿上就经常咳嗽,但从来没像现在咳得这样厉害,其实他也担心自己出了什么毛病,他甚至想到了矿上那些小姐,怀疑那些小姐把艾滋病传给了他,想到这里他头皮发麻,手脚冰凉,不停地出虚汗。
第二天一早,引娣生拉硬拽要让金刚去医院。两人借了辆摩托车,引娣坐在后面,圆鼓鼓的肚子顶在金刚的背上,金刚感觉到那个小家伙踢了他一脚。他们摇摇晃晃、颠颠簸簸地从村路上穿过,像荡在海面上的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被海浪打翻。到了上坡路的时候,金刚推着摩托,引娣在后面扶着,积雪很厚,尽管有太阳,但还没有消融,他们沿着山路一直向上。到了县医院,拍片子,做检查,跑前跑后,一上午过去了,医生拿着片子说,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尽早去市里的大医院看吧。金刚听出了医生的意思,赶紧追问,很严重吗,俺就是咳嗽气短,没有啥地方不舒服,给俺开点药、输输液就行了,以前也是这么治的,管用呢。
医生说,没那么简单,不瞒你们,我判断是肺上的病,像是尘肺病,你们还是早点去大医院检查吧,那里条件好、专家多,兴许能帮上你们。
回家的路上,金刚一句话也不说,一路灌风一路咳,一直咳到半山腰,摩托车被震得都快散架了。到了半腰再下到坡底就到家了,可金刚累得喘不上气来,直冒虚汗,他停下摩托车,要在大青石上坐一会,引娣用厚厚的大手套把大青石上的雪扫去,扶金刚慢慢坐下。引娣说,咱俩搞对象时,你经常带我到这里来坐,你说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你要带俺走出去,俺听了可高兴了,心想不管以后再苦再难都要跟着你,跟你一辈子,像膏药一样粘着你。他爹,你可一定要好好活着,俺和孩子就全靠你了,你要是有个好歹,俺也不想活了。金刚没有说话,目光呆滞,两眼噙泪,一把抱住引娣。
金刚病了,全村人都知道了,没过多久,众人发现村里好几个在矿上打工的人都得了咳嗽病,可金刚咳得最厉害。金刚越来越暴躁了,难受起来他随时都会发脾气,引娣端了一碗鸡蛋面给他吃,他摇摇头。引娣说,吃点吧,不吃连点力气都没有。金刚不知哪里短路了,冲着引娣就骂,吃,吃,吃,吃球死老子,你好再找野男人,是不是!
引娣端着碗站在原地,手一抖面汤洒在了地上,眼泪汹涌而出。金刚看引娣哭了,他不再说话,又开始咳。引娣转身去了厨房,泪哗哗地流,却不出声,哭着哭着就长长地吸一口气,再继续哭。哭了一阵,肚里的孩子不停地动,她不敢哭了,站起来擦了一把脸,镜子中的自己,没有了当年的样子,白嫩的脸已经晒黑没了水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转眼开春了,雪融了,天气也暖和了。引娣把春宝托付给她二姐,挺着大肚子,扶着咳嗽不止的金刚,一步三晃地进城了。这次进城,他们想去大医院看看这咳嗽咋个治法。排了一天的队,才挂到专家的号,专家说金刚是典型的尘肺病,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不过还需要做很多检查项目,一天根本弄不完。当天回不去,晚上金刚和引娣只能在医院过夜了。万万没想到,半夜里引娣突然破了羊水,就直接进了产房。引娣一边生一边喊,金刚你个王八蛋!俺恨你!毕竟生过一胎,没疼多久孩子就生下来了,医生告诉金刚是女孩,金刚只是“嗯”了一声。医生把孩子抱给引娣看,说这孩子长得多好看,脸上还有个小酒窝哩。引娣努力睁开眼看了看,使出全身的劲大声喊,他爹,有酒窝哩,是你的!说完这句话,她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引娣一边哭一边说,老天爷呀,你真是开眼了,俺心里堵着一块大石头呀,快憋死了!
隔日,专家拿着胸片对金刚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你的肺就像一块煤又黑又硬,已经是尘肺病三期了,这个病治愈率很低,如果手术换肺需要40万,洗肺的作用也没有多大效果,只能吃药维持。听了专家的话,金刚感到天崩地裂,他觉得为了挣钱把肺弄残了,自己最多再活两三年,挣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人啊,活着才有意义,活一天就赚一天。他对引娣说,俺错了,俺不该怀疑你,你是个好女人。引娣听了这话,眼泪汪汪地说,他爹你别怕,不管再难再苦,俺都会陪着你,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你把病治好,俺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把两个娃拉扯成人。金刚只是咳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夕阳下,金刚和引娣走出医院准备吃点东西,他们走进医院旁边的一条小巷,这里到处都是药店、小食店、小超市。突然,金刚站在原地不动,他揉揉眼睛又认真地看了看,前面一扇玻璃门里坐着两个熟悉的人,一个是拄着拐杖的班长,一个是眼睛斜视的春妹。金刚激动地走过去,和班长抱在一起,金刚告诉班长自己得了尘肺病,班长低下头没有说话。春妹尴尬地看了看引娣和引娣怀里的孩子说,俺大哥也得了尘肺病。
春妹说,她离开矿准备回老家,结果公安局说有人找她,见面才知道是班长,原来班长就是春妹的亲哥哥。爹妈去世前嘱托班长,一定要找到妹妹,这辈子找不到,下辈子也要找到。世界就是那么小,每天都见面,却不知道是亲兄妹,直到警察抓到了人贩子,他们才艰难地相逢。春妹为了给班长治病,在医院旁边租了个小店,春妹做裁缝的手工活,班长在门口卖点烟和零食。
从城里看病回来后,金刚整天待在家里,搭把手帮引娣看着孩子。引娣一个人汗珠摔八瓣地在地里干活养家,春宝有时候跟在后面打下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日落西山,一堆女人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刚走进村口就像散了伙的鸟,各自往家飞。一会儿功夫,村里炊烟袅袅,隔着院门就能闻到各家烧秸秆的焦味和蒸饭的香味。
金刚家住村西头,红砖砌的院墙围着三间正房。尽管要侍候生病的金刚,但夏天的时候引娣仍然抽空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蔬菜,一眼望过去绿中带红、红中透紫。一条红砖路通向正房,路两边搭着架子,靠近院门的架子上结着南瓜,靠近正房的架子上结着葡萄,红色泛紫的玫瑰香和青翠透亮的白玛瑙,正是成熟的季节,像一串串水晶玉雕,饱满欲滴。引娣一进门先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咕咚咕咚灌进肚里,用袖子抹抹嘴,然后舀一瓢水倒进脸盆,搓洗一下粘着黄泥巴的手,再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在盆里搓洗几下,拧干毛巾擦一把脸,这才开始做饭。
金刚吃不下饭,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气来。引娣怕金刚坐太久生疮,隔几天就给他洗洗澡,脱下衣服,金刚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当年的雄性风采,两排凸显的肋骨,肉皮松垮得可以拉起来。金刚痛苦地说,活得还不如一条狗,他想到了死,可喝农药时被引娣发现,抢下瓶子扔到茅厕坑里了;他又把手弄湿去摸电源,结果停了一天的电。他哭着说,想死都死不成,活着就是个死人,活死人呀!一到夜里他就胸闷气短,咳得睡不着,只能整夜整夜地坐着睡,不然猝不及防的咳嗽会把他憋死。引娣想了个办法,从房梁上甩了两条绳子下来,再吊上一块木板,在木板上放了枕头,金刚就趴在木板上睡觉,真的还挺有效果,金刚觉得舒服多了。
金刚咳得越痛苦,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他拉住引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婆……我想……等我死……了以后。引娣赶紧捂住他的嘴说,呸,呸,呸,不敢瞎说,你的命长着哩!俺还没跟你过好日子呢!金刚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俺知道……你跟了俺……吃苦了!可是……俺没多少……日子了,答应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和娃们住上……小洋楼……等不上了,俺……对不起你们呀!只好下辈子再给你……当牛马了!可是……俺没活够呀!金刚还没说完,引娣已经哭成泪人。
正月刚过,雪地里还埋着炮仗的红色残体,门前挂的老玉米上还盖着雪,搭在院里的衣服坠着细细的冰柱。又熬过了一年,情景如同回放的电影。
夜里北风呼呼,急而刺骨,吹得树枝、电线杆都摇摇晃晃,几只羊缩在圈里挤得紧紧的。雪纷纷扬扬飞旋而至,亲吻着饥渴的大地,玻璃窗透着昏黄的灯光,随后大幕落下,漆黑的夜里只有茫茫的雪还泛着银光。第二天早上,全村人都出来送金刚,市人民医院的急救车就停在泥泞的村路上,两名穿着白大卦的人抬着一个单架,单架上从头到尾盖了一块白布,引娣牵着两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追出来,哭声响彻整个山谷。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春妹坐在病床上,醫生拆下她眼睛上的纱布,她真真切切地看清了这个世界。班长拿起一张报纸,一边哭一边读:一个叫金刚的尘肺病人,去世后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了需要光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