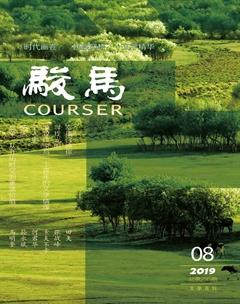个人史
何君华
第一本书
很多年后跟我的小学语文老师陈海英取得联系,竟然是源于一则网络求助信息。
人世间有许多相遇毫無预兆,而这一次相逢却是如此让人措手不及:陈老师的女儿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治疗费用需要几十万元,对于一名曾经的乡村教师来说,这无疑是天文数字,迫不得已,他只好上网求助。
2000年,只有二十岁的陈海英大学毕业来到湖北黄冈的蕲春县何铺小学教六年级语文,我从此荣幸地成了他的学生。他是我们简陋的乡村小学第一个有大学文凭的老师,也是第一个上课时操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许多书,有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曹禺的《雷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还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当时怎么也记不住这个前苏联作家的名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甚至还有《金瓶梅词话》。在他那里,我读到了人生中第一批文学书。尽管这些书我多数读不懂,内容也多已忘却,但晚上十点在宿舍走廊昏暗的灯光下读书的欣喜与满足至今记忆犹新。
我感觉我的小学时光极其短暂,而我的六年级生涯却极其漫长,甚至比整个小学时光都要漫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却的确如此。我感觉跟着陈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而那些事情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比如,他让我以老师的身份去给五年级的学生讲课,尽管我讲得一塌糊涂,还闹出过把学生们回答正确的问题判为错误的笑话,但他依然热情洋溢地鼓励了我。他带领我们去登山、郊游,甚至野炊,带领我们在操场上打球,给我们展示他自己的画作。我记得当中甚至有全裸的女体。我们为此惊骇,也从此打开眼界,看见了许多课本以外的事物。在黄冈这样一个应试教育根深蒂固并因此扬名全国的地方,他带领我们做一切与考试无关的事情,做一切在别人眼里“出格”的事情,并因此招致我们班主任的不满,甚至遭到校长的批评。
时至今日,我的少时同窗黄福青仍然记得陈老师拿着我的作文在班上朗读的情景。他说我的作文已经超过了初三的水平。如今我当然已不记得那些拙劣的作文写了些什么,它们当然足够稚嫩,但陈老师鼓励了我,甚至说要把我的作文拿去发表,我为此兴奋无比,每次写作文都格外认真。
多年后我不止一次跟身边的朋友说过,如果没有陈老师,我很可能不会写作。这句话当然是事实。人世间有许多行当可供选择,我为何没有成为一个植物学家、建筑师或是医生、警察,偏偏成了一个作家?我想大抵是因为陈老师。
很多年里我都羞于承认自己是“作家”,因为自知写的东西还远远当不起一个作家的分量。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或以真心或以假意称呼我为“作家”时,我再不以作家自称就显得矫情了。尽管这些年我仍然没有写出什么值得骄傲的作品,但我却越来越敢于以一个作家的面目招摇过市而不感到羞愧了,除了在陈老师面前。
在陈老师面前,我仍然羞愧难当。由于自己无可救药的懒惰和意志力的不坚定,一直没能静下心来写出有足够分量的作品,每每自感愧对陈老师的教诲。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联系陈老师的原因。我实在没有勇气拿那点小小的成绩去面见他,以致这么多年我从未以任何形式主动联系过他。
乾坤朗朗,星汉迢迢,多少人在阳光下作恶万端而问心无愧,又有多少人在夜色里受尽苦难仍然内心澄明。多年前,陈老师为我们打开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教给我们正直和善良。多年后,当面对陌生人的善意,陈老师请他们一一留下姓名,以期来日如数奉还。
陈老师名叫陈海英,但他总是把名字写成“陈海鹰”,大海上翱翔的鹰,那是一种本能的不屈的力量。
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上苍的安排用意何在,明明豁朗的天空为何偏偏被披挂上浓重的阴霾?但或许上苍也给出了答案,因为那些被阴霾击中的地方已经有人举起火把,那些光亮会尽力到达尽可能远的地方。
等信
今天微信时代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等信”的煎熬,尽管我所说的“我们那个年代”距离今天也仅仅是十个年头而已。
美国有一句著名的俚语叫TextPurgato? ry,意思是“等待回信的炼狱般的煎熬”。Purgatory是一个宗教词汇,指人死后所经历的净化灵魂、除去罪恶的洗涤过程,也就是“炼狱”。把等信比喻成炼狱,说明等信该是怎样一种煎熬。
我也曾经历过这种煎熬。那是2009年的10月,我照着从学校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抄来的地址,给《青春》杂志寄去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花衣裳》。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煎熬——等信,等来自《青春》的信。
2007年9月,我考入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然后开始写小说。
我天天跑去学校门口的邮政信箱看,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我的信。于是我又迫不及待地给《青春》寄去我的第二个短篇小说《玩具》。然后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等信,就像1957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1957年,被哥伦比亚《观察家报》派驻欧洲的年轻记者马尔克斯一天天地跑到旅馆楼下的门房问有没有他的信,得到的回复往往只有两个字:没有。不久前,由于哥伦比亚国内政局动荡,《观察家报》被查封,租住在巴黎索邦大学附近小旅馆的马尔克斯断了口粮,非但支付不起房租,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饥饿难耐的马尔克斯只好一遍遍地给友人们写信寻求接济,然而回复者寥寥。
尽管如此,马尔克斯并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因为还有一件事像火光一样指引着他前行,那就是文学。彼时的他无论如何困顿,也从未停止去写一部叫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中篇小说。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本来写的是他外祖父的故事,一个落魄的老上校每天去邮局看有没有他的信和救济金,不幸的是,这个悲伤的故事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在说三十岁的马尔克斯自己。
幸运的是,与老上校终其一生也没能等到来信不同,马尔克斯总算熬过来了,尽管那是很多年后的事。整整十年后,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出版,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倔强的哥伦比亚人。
我也终于迎来了我的幸运。那是一通以南京区号025开头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告诉我,我的短篇小说《玩具》将在《青春》发表,但需要修改,并给了我十分具体的修改建议。我至今记得打电话的人的名字,她叫裴秋秋。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一个南京区号025开头的电话,我以为还是裴秋秋,但并不是(原谅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青春》的另一位编辑,她告诉我,我的短篇小说《花衣裳》也将在《青春》发表。
她并不知道,《青春》此前已经留用了我的一篇小说。她更加不知道,她和她的同事裴秋秋不约而同地两次将我从绝望的炼狱中拯救了出来。
我激动地连夜按裴秋秋的建议改好了小说。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手机独自走到宿舍楼下,兴奋地给裴秋秋打去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将小说改好,请她“指点”。
跟许多孤独的写作者一样,我一直都是隐匿地、怯生生地躲在角落里写小说,从来不敢在人前张扬这样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我实在不敢在宿舍里当着舍友们的面拨出这通关于文学的电话。
直到彼时,我仍然不敢相信,我写的小说当真可以发表。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隐秘地喜爱着文学啊。中学时每一个月的月底,我总是怯生生地跑去书店问新一期的《中学生阅读》或是《中国校园文学》来了没有。如果来了,就一定要省下当天的晚饭钱买下来,然后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看,仿佛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难为情的事。
及至上了大学,我开始偷偷地写起小说来。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作(毕业多年后,我回母校做一个文学交流活动,偶然得知当时学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管理员王妍老师竟然关注到了我的写作,因为我总去那里将我手写的小说稿录成电子版,她在巡视时偶然发现了我,从此记住了我的名字。如果不是她后来调到文学院,我们得以在这次活动上重逢,我可能终身都不知道当时竟真的有人知晓我写作的“隐秘”),现在,我的小说就要白纸黑字在杂志上发表,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梦里一样。
我又开始等信了,天天往学校门口的邮政信箱跑,盼望着刊登我小说的《青春》杂志早日寄到。
我等到了,并且真的是两次,《青春》2009年第12期和2010年第1期连续两期发表了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小说。
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令人激动的事。
余华说:“一个天天写的人,不怕成不了作家。”从此,一个不可救药的孤独写作者头也不回地踏上了文学的“不归路”。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高行健说:“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我想,作为南方人的我,到内蒙古定居生活,并在这里写作,便是我的命运。
2007年高考,因为两分之差,我的第一志愿落榜,被调剂到坐落于内蒙古通辽市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彼时我尚不知通辽市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沿着呼和浩特市周边找了许久,就在我快要放弃寻找时,无意间在另一个省会城市沈阳西北二百公里处找到了它。我实在想不到内蒙古的幅员面积竟是如此之辽阔(它甚至比我的家乡湖北省的面积要大六倍之多),已经学过三年高中地理的我对内蒙古的误解如此之深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我竟然很快便适应并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寒冷,沙尘肆虐,有着跟南方故乡完全不一样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但我几乎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更重要的是,四年大学生活之后,我竟然没有离开通辽,而是继续留在这片我此前从未想过要涉足的地方。尽管我从未将高考失利看作命运无情的捉弄,但我当然也并不明白造物主如此安排用意何在。我只是以我向来逆来顺受的性格平和地接受了这荒唐的安排。及至后来我在这里写下我人生中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才终于理解了命运如此安排的因由——原来它是想让我到内蒙来继续完成写作的夙愿呀。
写作,几乎是我从小就树立的梦想。
人世间有千奇百怪的兴趣爱好,而我偏偏钟情于一个个小巧的方块文字。明明是再普通不过的汉字,谁都会写谁都会用,可是在作家笔下却能开出花来,经过他们的生花妙笔一番排列组合,一个个毫无干系的文字就会变成一篇令人沉迷的小说故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作家简直是这世间最神奇的魔术家。我甚至会因此羡慕我的同龄人们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稚嫩文字,不止一次梦见自己的文字也变成铅字发表在上面。后来我的作文当真发表了,而那本发表我“处女作”的杂志我一直保存了多年,直到它终于遗落在时间的缝隙里。
到内蒙念大学之后,我关于写作的梦想很快就被重新激活了。因为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我便发现自己住进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透过这个房间的门窗,我看见了迥异于南方故乡的奇异风景。从我们的学生宿舍向北望去,你会看见一座公园,这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公园,但它的名字叫西拉木伦,你根本不明白它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所散发出的异域般的神秘气质,迫使你不得不像婴孩般好奇地走近它。在内蒙古,这样类似的词汇举不胜举:科尔沁、哲里木、达尔罕、额尔古纳、花吐古拉、乌珠穆沁、白音胡硕……我为此找来《蒙古秘史》,找来《成吉思汗箴言》,“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捧在手心里阅读,于是一幕幕更加瑰丽的风景便在我的眼前次第展开,我的小眼睛睁得大而圆,也因此看得更高更远。
草原文化一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写作的灵感,于是一篇篇“草原小说”在一个来自南方的小说学徒笔下诞生:《头羊》《呼日勒的自行车》《希仁花》《少年与海》《礼拜二午睡时刻》……有人看了这些“草原小说”,甚至疑心我是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内蒙人,甚至问我是不是蒙古族,我只好笑而不语。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也愿意用心体悟草原上的事物,或许你也会写出属于你的“草原小说”来。
异域总是令人心生向往,远方总是让人无限着迷。博尔赫斯写出了迷幻的中国故事《小径分叉的花园》,卡夫卡寫出了令人震惊的《中国长城建造时》,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甚至可以算作一部彻头彻尾的“草原小说”,因为它讲述的正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描述他在草原帝国旅行的见闻和故事。而我远比当年的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们要幸运得多,他们一生从未踏足中国的土地,更不用说内蒙古大草原,他们的“中国故事”、“草原小说”完全是凭空杜撰,而我好歹就居住在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推开门窗便是活生生的壮丽图景。
尽管今日的草原不得不承受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种种令人绝望的痛苦,但它仍然是美的,依然值得我们用手中的笔去书写。尽管一如我借我笔下一名虚构人物、一位草原画家那日苏所说的,草原的美是我这支拙劣的笔所不能书写万分之一的,但写下去是有意义的。起码之于我自己,之于十几年前那个沉迷于方块字的小男孩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便是命运,这是命中注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