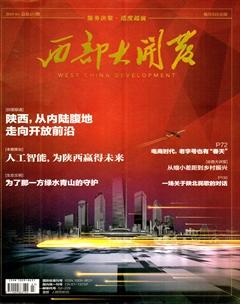朔北的风
蒋仪洁

我家住在陕北黄土高坡,小时候最害怕刮风,大风携裹着黄沙遮天蔽日,我们称之为黄风。
每年风从坡上刮过,带走了沉降的种子与刚发芽的小草,只留下光秃秃的山梁,想打一筐猪草也要翻山越岭到好多地方找寻。最难熬的是逆风行走于家校之间,拖着瘦弱饥饿疲惫的身子只好走走停停,有时风急了瞬间会有窒息的感觉,待到回家时就变成会眨眼的泥塑,那时真是谈风色变。
到了冬天,风沙拼命的往里灌,土窑洞的窗户纸是经不住风沙侵袭,破了只好用旧床单和破塑料应急遮挡。那时树木稀少,缺少取暖的柴火,家里特别的寒冷,感觉针尖的洞有钻牛的风。
如遇大旱,一年一场风,从冬刮到春。大风起时,天昏地暗,像一堵通天彻地平移的沙墙,大风过后,野田禾苗半枯焦,农民半年的希望化为泡影。
陕北人民就祖祖辈辈生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面对风沙肆虐束手无策,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只好祈求上苍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相传清光绪年间陕北靖边县知县王沛蕖《七笔勾》“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川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所描写的就是陕北真实生态状况。古时的榆林城也因风沙南迁三次。九十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到陕北考察后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人生存的地方。
历史上陕北靖边其实水草丰美,牛羊塞道。公元五世纪,赫连勃勃投奔后秦受命安北将军镇守朔方,后起兵逐水草而建大夏国都统万城,慨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若斯之美”。后因戰乱和人为破坏,那段车辚辚马萧萧、狼烟四起、刀光剑影的历史永远销匿沉寂在沙海中,只有断壁残垣矗立在那里铭记篆刻着历史兴替生态变迁。
七十年代,陕北生态加速恶化,大风推动沙丘一路南下,吞噬农田、侵蚀庄园,沙进人退愈演愈烈,生存空间逐步挤压,人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勇敢转身向沙漠进军,从此拉开了人与黄沙共舞的大幕,涌现出牛玉琴、石光银、女子民兵治沙连等治沙英雄。他们采用扦插、套袋和草方格治沙技术年复一年终于驯服了那片沙漠,演绎了一个个战天斗地、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治沙故事。这种无私无畏的治沙精神也成为一代代陕北人民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九十年代,党中央发出“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动员令,陕北人民苦于生存现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投身到家乡生态建设中、天保工程、封山禁牧、舍施养羊、飞播造林等多措并举,草、乔、灌生态系统加速修复,退耕还林经济和生态效益日益显现,昔日山花无锦绣、水恶虎狼吼的陕北,如今呈现“东风夜放花千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旖旎景象。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犹如一缕春风吹遍千山万水,吹进千家万户。“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科学论断渐入人心,陕北人民认真践行“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今流动沙丘全部固定,沙进人退的局面发生了根本逆转,村庄田园不再遭受风沙威胁, “微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秀美山川正在形成,靖边也成为不向黄河输送泥沙的美丽县区。
朔北的风带着苦难、带着梦魇千百年来从黄土高坡吹过,吹皱了额头,吹昏了双眼,如今北风南调,生态文明之风徐徐吹来,吹开了心田,吹绿了旷野,陕北人民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固化“五大理念”,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我们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态梦一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