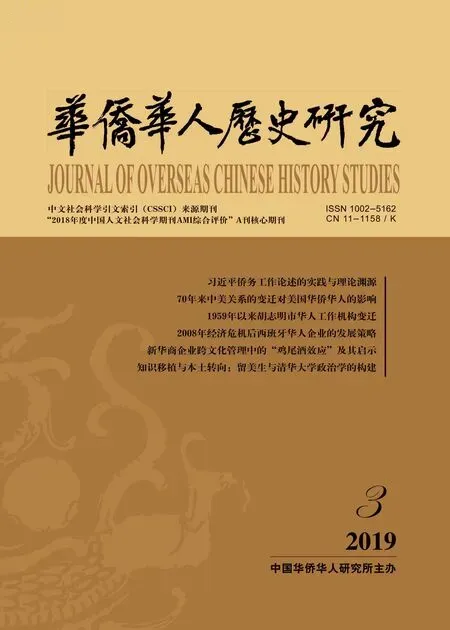7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迁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
陈奕平 尹昭伊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一、国家间关系与外来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初步的分析框架
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从战略视角治理海外侨民的做法引起学界的重视,①有关研究参见以下文献:A. Gamlen,“The Emigration State and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Political Geography, 27(8), 2008, pp. 840-856; J. Itzigsohn, “Immigration and the Boundaries of Citizenship: the Institutions of Immigrants’ Political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3(4),2000, pp. 1126-1154; P.Levitt& R.de.la Dehes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tate: Variations and Expla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6(4),2003, pp. 587-611; E. Østergaard-Nielsen(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nding Countrie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P.Nyiri, “Expatriating Is Patriotic? the Discourse on ‘New Migra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Recent Migrants from the PRC”, in B. S. A. Yeoh, & K. Willis(Eds.), State/Nation/Transnation,London: Routledge,2004, pp.120-143;陈奕平:《侨民战略视野下我国侨务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侨民战略”(Diaspora Strategy)的概念。[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近30年来华侨华人研究学界的重点,包括华侨华人的种族、文化乃至政治认同,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以及华侨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与中国外交等领域的作用等方面。[2]其中,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分析了100多年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华侨华人与中国合作的基础、特点和趋势;[3]任贵祥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利用中央档案馆中尚未开放的档案,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党和国家的侨务思想及侨务政策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大力支持;[4]吴前进的《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勾勒出华人与中国及其居住国的互动关系;[5]麦礼谦的《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赵小建的《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等著作都以翔实的史料和案例记载和分析了美国华人在中美关系对抗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推进居住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6]孔秉德和尹晓煌主编的论文集《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剖析了美籍华人作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对中美关系发展所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7]
总体而言,学界从侨汇、知识转移、人文交流、政治影响等领域对移民与祖籍国关系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但是“解释国家为什么和如何管理离散族裔仍然具有挑战性,部分原因在于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阶段有多种影响因素”,包括“一些外部因素如住在国的社会性质、离散族裔在住在国的合法地位、住在国与祖籍国的关系、国际或地区组织的作用、调和祖籍国与离散族裔关系的特定国际规范等”。[8]其中,居住国和祖籍国关系的变动对移民的影响在学界受到的关注明显不够。
本文拟通过梳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三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关系的波动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对苏冷战,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中美关系进入意识形态的对抗期;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出于共同抗苏的地缘战略考虑,中美关系逐渐缓和并实现正常化,可以说进入地缘政治合作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对华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战略,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更强调战略竞争,中美关系进入经济相互依赖和安全防范的竞合期。[9]可以说,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冷战对抗到关系正常化和“准联盟”,从接触和经济相互依赖到战略性竞争的演变。当前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推行对华全面施压的霸权政策所致。
国家间关系的变动势必影响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据统计,美国华人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15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43万人;1990年达到164万人;截至2017年,以508.17万人居美国亚裔人口之首。[10]长期以来,华侨华人对美国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美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也不时遭受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华人间谍论”的影响。
从中美关系与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美国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友好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但也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波动乃至交恶的受害者。一方面,从华侨华人的桥梁作用角度看,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好,融入美国社会程度高,既可以参与公共外交,也可以更好地影响美国舆论,促进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友好发展,依赖程度加深,经济、科教等领域互动频繁,美国对华实施“接触”政策,舆论环境良好,有利于美国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反之,中美关系波动,断绝往来或者限制交往,或者两国相互猜忌,美国反华舆论甚嚣尘上,自然不利于美国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
中美关系变动对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三个维度(见图一)。从政治维度看,中美政治互信带来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美国华侨华人的自由发展;反之,中美政治上互不信任,相互猜忌,出现类似麦卡锡主义的反华狂潮,美国华人被怀疑不忠诚,甚至被妖魔化为“黄祸”“间谍”,自然严重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经贸方面,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作为桥梁和纽带的华侨华人能够积极交流与合作,自身也可以分享合作的成果;反之,如果出现贸易摩擦,与中国经济密切的华商或华人企业难免受到冲击。在人文交流方面,中美关系友好,人文交流会得到鼓励,华人科学家和人文精英有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反之,中美关系出现波动,华人科学家和人文精英往往被怀疑不忠诚,遭受调查甚至被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坐牢,这自然严重影响华侨华人参与人文交流。
二、冷战时期中美对抗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1949—1969)
冷战使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支持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美国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与社会主义阵营壁垒相对,随着两极格局确立,美国国内对华立场逐渐倒向对华强硬派,再加上朝鲜战争,自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时期。1950年2月,麦卡锡在演讲中宣称,他知道有205名共产党员为美国国务院工作,[11]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共人士利用“恐共症”掀起红色恐慌,大肆渲染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宣称华侨华人充当“颠覆”美国的“第五纵队”。成千上万的华人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华人社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遭受无妄之灾。
(一)中美对抗对美国华侨华人政治领域的影响
1.被迫中止与祖籍国的联系
随着中西方冷战的升级,华人社会在政治上的发展也相当曲折。在此之前,美国华侨华人大多自认为是中国人而非美国人,基于对祖籍国的忠诚,大多数华侨抱着“落叶归根”的心态想要回归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美关系敌对,支持新中国就会被扣上“叛国”的罪名,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侨华人害怕遭受政治迫害不得不放弃回归的念头。在朝鲜战争之前,许多美国华侨华人都参与中国的政治集会,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多数华侨华人(尤其是在美出生的华人)开始回避中国政治问题,[12]与祖籍国的政治联系被迫中止。
2.华人社会内部分化
在冷战时期,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争夺华人社区,动员当地华侨华人支持台湾当局,类似的政治宣传激化华人内部政治矛盾,导致华人社会内部分化,这种特殊的冲突折磨着华人社区。[13]虽然一部分华人对国共之争没有兴趣,但在这种氛围下,只能被迫参与活动表达自己的忠诚,部分华人的政治表达自由被内部势力斗争影响,对现存状况感到失望。
3.华侨华人遭受政治审查
在麦卡锡主义浪潮下,对于美国政府和公众来说,华侨华人即使获得永久居留甚至入籍美国,也是外国人。中美对抗时期,在调查共产党颠覆活动的幌子下,不仅新移民入境受阻,连那些已经获得了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的华人也成了美国政府的调查目标。[14]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军队在朝鲜前线对垒,美国政府在后方加紧监视一些进步华人,反共政客经常以调查共产党活动为借口,多次传召知名左翼华人。这些左翼华人被舆论攻击,声誉被损害,谋生的事业也被摧毁。“恐共症”不仅扼杀了激进分子的言论,也扼杀了华人社区中的不满意见,国民党也仗着有美国政府撑腰,借机打击那些在华人社区中反对他们的华人。[15]政治审查不仅是对美国华人的攻击和限制,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传播了不实舆论,使部分社会大众对华人社区产生认知偏差。
(二)中美对抗对美国华侨华人经济领域的影响
1.华人企业生存环境艰难
在反共气焰逐渐上升的美国社会里,华人企业陷于微妙的处境。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卡锡内部安全法案》,授权拘留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人,几乎一夜之间,一些华人的客户开始取消订单,企业出现亏损。朝鲜战争时期,在洛杉矶的一家餐馆,一名酒保无意中听到顾客嘟囔着:“我们快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中国人经营的”。[16]中美对立时期,种族主义者排华故态复萌,不少华侨华人担忧自己被打上“敌国侨民”的标签,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日裔被关入集中营的悲剧,一些商人为了要给社会一个好形象,不得不采取行动,纷纷发表效忠美国的宣言。[17]
那些在族裔集中地区开办企业的华人首当其冲,所创办的企业、商铺、杂货成为偏激分子攻击的对象。大多数美国人光顾中餐馆的热情降低,有些人则完全避开中餐馆,在2.5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中餐馆已不复存在,而在较大的城市,中餐馆的数量也有所减少。[18]不少中餐馆因中美对抗生意一落千丈。
2.华侨华人向侨乡汇款中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进入全面对抗时期,美方全面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来自海外华人的汇款有助于中国进行朝鲜战争,谴责华侨华人的侨汇都是非法资金,试图阻止华人以人道主义为由援助中国,对华实施国际贸易禁运。[19]美国认为华人对中国至关重要,美国财政部估计直至1951年底,共有大约400万到500万美元的汇款邮至中国,[20]大量的侨汇为中国提供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本。美国政府怀疑华人如果变成中国的“第五纵队”,就会凭借其经济力量支持共产主义发展,对美国安全和外交利益产生威胁。[21]禁止侨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想用侨汇资助家乡的华侨华人。
(三)中美对抗对美国华侨华人人文交流的影响
1.华人学者遭受审查
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舆论导致华人知识分子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以钱学森为例,这位二战前留美的空气动力学家于麦卡锡时期被卷入所谓间谍争端案中。1949年,钱学森申请了美国国籍,然而在美国国内反共的政治环境下,他没有得到基本安全保障,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很快就从信任变成了怀疑,指控他是共产党员并充当中国间谍,[22]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依据《麦卡锡内部安全法案》对他进行监视、跟踪和审讯。[23]在中国政府的积极争取下,经美中日内瓦会议的协商,钱学森和其他数百名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才得以返回中国。
2.文娱活动方面遭到限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文化渗透,将矛头指向唐人街,监视唐人街的科教文娱活动,华人社区中许多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被迫取消。只有华侨民主青年团,即“民青”及绿源书店还在勉强维持,但在政府和反华群体的不断骚扰下,也不得不先后解散。[24]同时,华社自由言论遭到限制,一些华人报刊例如《太平洋周报》《中西日报》等接连停刊。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对立,以《美洲华侨日报》为代表的华文媒体,因公正报道中国国内新闻而遭到国民党及美国政府的攻击。美国财政部称该报因刊登向广东侨乡汇款的广告而违反《与敌国通商法》,借机打压《美洲华侨日报》。1963年开始,报社决定将报纸改为每星期出版两期,直至1977年才恢复原有出版规模。[25]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华侨华人的影响(1969—1989)
20世纪70年代初,基于抑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中美关系逐渐解冻。1971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双方紧闭长达二十多年的国门,使中美关系回暖。1978年底中美两国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关系逐渐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推动与压力下,美国国会通过《移民与国籍法修订案》,之后亚裔移民数量激增,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善。这两件事深刻影响了美国华侨华人,许多人转变以往“落叶归根”的念头,想在美国“落地生根”,华侨华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的步伐,在美国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一次讲话中对美国华人评价甚高,他认为“正是华人生活上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使他们对工作有信念,富有自谦和自我牺牲的纪律性,这些品德也给美国社会添砖加瓦。”[26]体现了中美建交时期,美国华侨华人逐渐得到居住国的认可。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华侨华人的政治影响
1.华侨华人参政热情升高
双边外交关系的恢复,为华侨华人群体表达自己政治立场提供了保障。此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给美国华侨华人群体注入新的血液,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种来源的新移民占美国华侨华人总人口比例已达75%,显示了华人移民涌入美国的趋势。[27]新老移民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华侨华人逐渐意识到参政对华社的重要性。为打破族裔固化标签、维护自身权益、重塑华人形象,美国华人开始在政治中崭露头角,如1984年美籍华人吴仙标当选美国特拉华州副州长,并取得卓越的政绩,华人参政热情不断提高。
2.华人社团在政治领域取得新突破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华人社团建立的一些政治性组织,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政策,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华侨华人对美中关系有了新的期待与展望,开始关注与影响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1971年3月,美国国务院取消美国公民来华旅游限制的禁令,为后续华人社团促进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为例,该社团成立于1974年,是一个致力推进中美民间外交的非营利组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通过组织演讲、赞助活动等方式为美国人民深入、真实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平台。[28]这表明华人社团不仅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维护族裔的政治利益,同时也开始活跃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舞台。在签署《上海公报》的过程中,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华裔民主党协进会、中美邦交协进会等华人社团积极发声和行动,[29]华人社团的政治取向有了新的突破和定位。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华侨华人经济领域的影响
1.华商来华投资逐渐增多
中美关系转机,在美国华侨华人社会内部激起千层浪,美国对华封锁禁区打开后,许多美籍华人立刻申请到中国。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一些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华人很快被中国迅速扩大的市场所吸引,纷纷到中国投资项目,华人资本又再次涌向中国。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间,他们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动和促进有目共睹,中国兴建大批合资企业,一些侨乡最先出现个体私营经济和小型集体经济,利用侨胞资金、信息和市场做大做强,为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30]
2.华人就业机会增加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双边经贸往来大幅度增加,许多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华侨华人凭借自身语言、资源、信息等优势,在中美经贸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华人利用自己的人脉为中美经贸往来牵线搭桥,还有一部分华侨华人进入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就职,或是作为美方代理进驻中国。[31]其次,唐人街的各个行业也从苦力劳动为主转向多元化发展。美国商务部依据1987年调查资料统计,华人经营事业共89717家,经营情况较佳,在亚裔及少数族裔中占领先地位,尤其是食品、纺织品加工业、电子电器制品等。[32]这得益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美国实施新的移民法,其二是中美建交后新移民数量增加,新移民携带资金前往美国创业的现象逐渐普遍。
故障特征值是故障诊断的核心内容,它提取的好与坏将直接对故障诊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产生影响。故障特征值的提取过程就是将电路中的波形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即信号的处理过程。时域分析法与频域分析法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信号处理方法[13]。时域分析法原理简单,但是操作和实现困难,所以在这里采用实用性更高的频域分析法。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把时域里的波形变化到频域中来,利用其频谱特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华侨华人人文交流领域的影响
美籍华人学者在麦卡锡主义时期的遭遇令人唏嘘,两国正常交往后,他们的处境大大改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给华人学者提供一个发挥自身特殊身份的空间,鉴于他们对中美两国各方面的了解,华人科学家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两国科技合作的桥梁。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的大门终于打开了。[33]《上海公报》中科学交流占有突出比重,中国和美国都把科学交流看成是隔绝多年后通向相互理解的一条中性的、非意识形态的路线。[34]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都多次到中国访学,创办教育交流项目,培养了许多优秀科研人才。以杨振宁为例,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知名华人科学家,在美国政府取消对华访问限制后,他便返华为新中国科学发展出谋献策。
宏观上看,在中美对抗时期,美国政府一直对华人政治活动抱有戒心,不断在政治忠诚方面做文章。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由于政府对华舆论放缓,一直“默默无闻”的美国华人学者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开始去中国进行访学,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坚实的、富有成效的努力。
四、后冷战时期中美竞合关系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1989—2019)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美国对华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的新时期。中美竞合关系下,政治接触和经济相互依赖为美国华侨华人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但当前美国决策层戴着冷战有色眼镜看待发展的中国,不断对华施压,甚至炒作中美“注定一战”,[35]美国挑起的紧张局势势必影响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中国威胁论”对美国华侨华人的政治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便借口所谓的人权、知识产权、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不断通过立法、外交等手段向中国施压,并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美国华侨华人也因此受到波及。根据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2001年全国公众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公众认为“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忠诚”,同时调查发现,近40%的公众认为“亚裔美国人在政府和高科技领域‘过于’有影响力,并且这些人对祖籍国更加忠诚”。[36]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疑心和防范心理只增不减,相继出台了各式各样评估中国实力的战略报告,以冷战思维妖魔化中国,旨在塑造“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这些新冷战思维和舆论充斥着美国朝野,打破了华人社区的平静。一些华侨华人清醒地发现,“中美关系一有风吹草动,美方还是会把他们当外国人”。[37]
美国媒体和学者甚至对中国侨务政策[38]和海外统战工作[39]进行炒作和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2018年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公开宣称,在美国“几乎所有领域”中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教授、科研人员、学生”都可被视为“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他们有可能秘密地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40]百人会认为这种言论非常令人不安,认为这是标签化某一族群而煽动针对该族群恐惧心理的行为。[41]这种渲染华裔学者“威胁论”、“间谍论”的做法使华人社会警惕,致使华侨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活动大量减少。
美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侨务政策和海外统战工作进行的炒作和攻击,实质是“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重弹。其实,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长对美国的所谓“威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有一种论调针对的就是华侨华人,把他们污蔑为“黄祸”和“第五纵队”。其实,即使是作为移民接受大国的美国也鼓励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鼓励移民为祖籍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奥巴马政府甚至把居住在美国的国际移民纳入其对外战略总体布局之中,提出“国际侨民接触战略”,建立“国际侨民接触联盟”,支持居住在美国的他国侨民在美创业,开展公共外交、志愿服务、创新联系、慈善捐助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外交的开展,达到争夺国际影响力的目的。[42]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有关“侨务干涉论”“中国间谍威胁论”等换汤不换药的“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愈发喧嚣之际,美国华侨华人的处境备受关注,不少人担心此类言论会使华人社区污名化。
(二)中美贸易摩擦波及美国华侨华人企业的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之际,美国政府捕风捉影地炒作“华人间谍”事件,对美国华人是极为不公正的,也势必挫伤华人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心血和才华的热忱。[44]美国百人会主席吴华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贸易摩擦还具有其他象征性,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美国内部分化与焦虑,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让美国感到其地位受到威胁,同时迅速增长的华裔以及其他种族人群也让美国白人社会担忧,中美贸易关系持续恶化,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波及华裔群体。[45]特朗普政府对中美贸易的强硬观点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威胁,这会推动反华情绪的升级,致使美国华侨华人受到两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冲击。
(三)中美战略竞争波及美国华侨华人的科技和人文交流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防部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文件,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美方的意图明显有针对性,从中兴到华为,美方剑指“中国制造2025”。此外,有言论指出,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监视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华人学者,并采取起诉和开除等行动。为针对千人计划华人学者,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018年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的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允许国防部终止向参与中国、伊朗、朝鲜或俄罗斯的人才招募项目的个人提供资金的拨款和其他奖励。[46]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首要潜在敌人”,这些都会使美国华侨华人的忠诚度遭到质疑。近20年来,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华裔美国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案件早已被证实是无稽之谈。
2017年百人会在白皮书《起诉中国间谍:经济间谍法的实证分析》中指出:“根据《经济间谍法》进行诉讼的136起案件样本显示,从1997年到2008年,华人被告方占案件的17%,但在2009年至2015年间,该比例增加了三倍,达到52%;华人和其他亚裔被告被判的平均刑期分别是25个月和22个月,是欧洲裔被告被判刑期的两倍;21%的华人和22%的其他亚裔被告从未被证明犯有间谍罪或其他罪行,这一比例是欧洲裔被告的两倍;而在被判有罪的华人和其他亚裔案件中,多数是对虚假陈述、隐瞒证据这样的小过错认罪,而换取撤销所有的重要指控。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华裔近年来正在被不断猜忌和怀疑。”白皮书撰写者安德鲁·金指出,“这是否是美国司法部把更多资源用于识别和起诉与中国有关的间谍活动?是否反映司法部资源的合理优先次序,或者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种族定性案件,并开始新的‘红色恐慌’。”[47]
1999年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因涉嫌窃取、泄露机密被美国政府逮捕,在“李文和案”发生后,《考克斯报告》又被炮制出来。这份由美国众议员考克斯领导、以调查中国盗窃美国国防秘密的报告发布后,在中美两国都引起轩然大波。两件案例均视中国为“威胁”,通过舆论影射华裔学者为间谍,给美国华侨华人蒙上阴影,其背后反映了华侨华人深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2000年,李文和在被监禁278天后获释,主审联邦大法官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er)向他道歉,法官承认法庭被美国政府误导,李文和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专访时指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绝不会被控间谍罪,更不会被恐吓要处决。”[48]
无独有偶。近年来水利专家陈霞芬案、物理学家郗小星案等冤案频发。2019年春季,美国国立卫生院的代表向美国医疗中心发出警告,借所谓“外国有系统地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在美国各地开展了对华裔教职员工的大规模调查,其中包括搜查华裔学者的电子邮件、电话通信、视频监控,一些华裔学者职位(包括终身职位)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终止。[49]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次记者会上用“相由心生”来回应“间谍案”,说道:“世界上到底是谁在对其他国家实施大范围监听、监控、窃密、渗透,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持并施加影响力,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50]针对华裔的负面评论和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出公告,认为这类评论会对华裔造成伤害和信任危机,而加利福尼亚的黑暗排华历史早已警示大众,基于原籍国的怀疑,可能导致非常可怕的不公正。[51]
美国的种族偏见总是在特定的时期和场合,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特殊时期,美国华侨华人总会因为中国背景而被质疑其对美国的国家忠诚。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一次采访时说道:“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属的身份标识以及自己怀有归属感的身份群体获得外界社会的认可,尤其是那些由于历史沿革而被边缘化的群体。”[52]此观点也是对当前美国华侨华人处境的描绘。美国政府从行动上限制家庭移民、高科技人才,从舆论上散布各种有关“中国威胁”的信息,这些举动都抹黑了华侨华人形象,造成美国民众对华人群体的认知偏差,对华人社会形成无形的压力。
五、结语
美国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友好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也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波动乃至交恶的受害者。70年来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冷战到缓和,从接触加遏制到战略竞争的阶段性变动,国家间关系的波动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维度对美国华侨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进入对立时期,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共人士掀起“红色恐慌”,排华舆论盛行,阻碍华人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正常发展,甚至连华裔进步学者也遭受无妄之灾。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上台后开始改善两国关系,美国社会对华舆论逐渐缓和,华人群体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后冷战时期起,中美关系时好时坏,近期美国政府的一些举措,如监视千人计划的华裔科学家、渲染“侨务干涉论”、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等行为,都严重影响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华人群体在美国的地位和待遇与中美关系变动直接相关,不同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华舆论均有所不同,不管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有多坚定,一旦中美关系变迁,美国华侨华人总是受到波及。如今,在美国全面对华施压,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华侨华人难免受到冲击。当然也需要他们站出来,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是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移民是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共享资源”(shared resources),他们和祖籍国的关系不仅仅在于往来和互动,更关键的是互动的目的和结果,即互动是否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合作与共赢。事实上,中国侨务工作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有利于”政策,即“有利于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发展我国同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53]“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发展我国同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排第一和第二位,说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海外移民的生存和发展,重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以促进合作和共赢。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华侨华人对美国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当前,华侨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人数最多的族群,各行各业都可以看见华人的身影。美国华侨华人作为非官方角色,是连接中美关系的桥梁,他们在积极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也有助于打破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不实舆论,使美国大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注释]
[1] Mark Boyle, Rob Kitchin and Delphine Ancien, “The NIRSA Diaspora Strategy Wheel & Ten 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2009, http://diasporamatters.com/wp-content/uploads/2011/05/Diaspora-Toolkit-Booklet-5.pdf; 其他有关侨民战略的论述见:Delphine Ancien, Mark Boyle and Rob Kitchin,“Exploring Diaspora Strategi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NUI Maynooth, Workshop Report, June 2009;Aikins K, Sands A, White N,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Diaspora Strategies:The Global Irish Making a Difference Together”, The Ireland Fund, 2009; Mark Boyle, Rob Kitchin, Delphine Ancien, “The NIRSA Diaspora Strategy Wheel and Ten 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 Working Paper, 2009; Delphine Ancien, Mark Boyle and Rob Kitchin, “The Scottish Diaspora and Diaspora Strategy: Insights and Lessons from Ireland”, Scottish Government, 2009.
[2] 刘泽彭、陈奕平等:《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3]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任贵祥主编:《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5] 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6]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赵小建:《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8] [美]亚历山大·德拉诺、[新西兰]艾伦·加姆伦著,罗发龙译,陈奕平校:《祖籍国与离散族裔的关系:比较与理论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
[9] 参见陈奕平:《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继承的遗产及走势展望》,《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陈奕平、王琛:《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
[10] 有关数据参见以下文献: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Asian-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 Heritage Month:May 2018”, MAY 01,2018,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facts-for-features/2018/asian-american.html, 2018 年8月25日浏览;庄国土:《从移民到选民: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11] Mary Wood, “McCarthy Era Offers Cautionary Tale for Post-9/11 American, Stone says”, University of Virginia,April 15,2004, https://www.law.virginia.edu/news/2004_spr/mccarthy.htm, 2018年8月25日浏览。
[12] Charlotte Brooks, Between Mao and McCarthy: Chinese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Cold War Yea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2.
[13][15]陈依范著,韩有毅等译:《美国华人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290、262页。
[14] 赵小建:《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16] Ellen D Wu, The Color of Succes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1.
[17][24]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345、349页。
[18] Rose Hum Lee ,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63.
[19] 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outledge Press, 2013, p.35.
[20] Yousun Lu, “Programs of Communist China for Overseas Chinese”,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56, pp. 71-72.
[21] 张焕萍:《再论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战(1949—1964)》,《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22][34]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44、246页。
[23] 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5页。
[25] 王土谷:《美洲华侨日报的创建和发展》,《新闻研究资料》1991年第3期,第169~171页。
[26] 李小兵、孙漪、李晓晓:《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27][29]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2、188页。
[28] 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bout USCPFA”, http://www.uscpfa.org/about.html, 2018年8月25日浏览。
[30] 严瑜:《侨这四十年,与国共奋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14日。
[31] 徐德清:《旅美学人——中美友好合作的桥梁》,徐德清、洪朝辉主编:《世纪之交的反思:中国旅美学人谈中美关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8年,第248页。
[32] 陈怀东:《美国华人经济现状与展望》,台北:世华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65页。
[33] 基辛格:《白宫岁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705页。
[35]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6] Jane Leung Larson, “Still the ‘other’? Are Chinese and Asian Americans Still Seen as Perpetual Foreigners by the General Public?”, April 2009, https://committee100.typepad.com/committee_of_100_newslett/2009/04/still-theother-are-chinese-and-asian-americans-still-seen-as-perpetual-foreigners-by-the-general-pu.html, 2018 年 8月29日浏览。
[37] 阮次山:《中美关系下的华人处境》,《国际观察》2001年7月号,第7~19页。
[38] Harry Krejsa and Anthony Cho,“Is Beijing Adopting an Ethno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7-10-23/beijing-adopting-ethnonationalist-foreign-policy, 2018 年 8月25日浏览。
[39] 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ugust 24, 2018, p.3, https://www.uscc.gov/Research/china%E2%80%99s-overseas-united-front-work-background-and-implications-united-states, 2018 年 8 月 25日浏览。
[40] 刘栋:“美国‘华人间谍’威胁论调查”,澎湃新闻网,2018年3月2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36830, 2018年8月29日浏览。
[41] Committee of 100, “Committee of 100 Denounces Broad Brush Stereotyping and Targeting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Academics”, April 05,2018,https://www.committee100.org/press_release/committee-of-100-denounces-broadbrush-stereotyping-and-targeting-of-chinese-students-and-academics/, 2018年8月29日浏览。
[42] 陈奕平:《美国“国际侨民接触”战略及其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43] 吴乐珺:《加征关税将加重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负担》,《人民日报》2018年8月24日。
[44] 李庆四:《美炒作华人间谍是双输之举》,《北京日报》2015年5月28日。
[45] 吴华杨:“种族、身份与价值观:中美贸易战中的文化冲突”,2018年7月16日,http://www.ccg.org.cn/Effect/View.aspx?Id=9393,2018年8月29日浏览。
[46] Mitch Ambrose, “New US Visa Screening Measures Target Chinese Citizens Studying ‘Sensitive’ Subjects”,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13 June,2018, https://www.aip.org/fyi/2018/new-us-visa-screening-measurestarget-chinese-citizens-studying-%E2%80%98sensitive%E2%80%99-subjects, 2018年8月23日浏览。
[47] Andrew C. Kim,“Prosecuting Chinese Sp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Committee of 100,May 2017, pp.8-10, https://committee100.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2017-Kim-White-Paperonline.pdf, 2018年8月29日浏览。
[48] 任毓骏:《李文和新书面世》,《人民日报》2002年1月17日。
[49]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CCS sent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leaders of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requesting the profiling of ethnic Chinese scientists to cease”, June 4,2019,https://www.apajustice.org/community-responses.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2019年6月5日浏览。
[50] 闫子敏:《外交部回应美澳“中国间谍威胁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2日。
[5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Reaffirming our support for Berkeley’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ebruary 21,2019, https://news.berkeley.edu/2019/02/21/reaffirming-our-support-for-berkeleys-international-community/?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9年6月5日浏览。
[52] 李佳佳:“对话弗朗西斯·福山:美国中期选举、身份政治及中美关系”,搜狐网,2018年12月2日,http://www.sohu.com/a/279410591_570253, 2018年12月5日浏览。
[53] 万钢:《努力实现侨务工作的科学发展》,《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