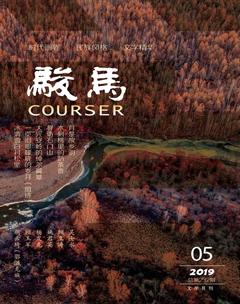隐情
钟寿军
他病了,几乎每年的秋季都要患一次重感冒。别看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每次生病,无需打针输液,吃点药,躺几天就会挺过来。这次却是个意外,已经一个星期了,病不但没有好转,还日益加重。
她听说了,急火火地赶来,推开门,看到病榻上的他,双眼深陷,红润的腮也塌下去了,面色灰暗。她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搂住他瘦削的肩膀嘤嘤啜泣:老哥哎,才几天不见,你就病成这个样子,怎么不去医院看看呀!
听她这么一哭,来探视的人心里都酸酸的。在村里他可是公认的好人,他曾当过小学教师,写得一手好字,谁家的娃娃淘气挨了爹娘的打骂,赌气不吃饭了,他轻言细语地劝几句,娃娃就乖乖地端碗吃饭了。谁家过春节、结婚找他写对联,他立马写好给送去。村里人都很尊敬他。就是这么个好人被疾病折磨成这样,看了怎能不让人心疼?更何况她是他的弟媳,有亲情牵着,流些眼泪是情理中的事。他抬起双眼望望她,强作笑颜:“不要紧,估计过几天就会好的,去年把你们大家伙儿吓了一跳,后来不是也挺过来了吗?”言毕,一阵剧烈的咳嗽,那声音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她的心上。
自从跟老实巴交的丈夫从河南老家搬迁过来,大伯子就成了他们家的主心骨,盖房子、儿子娶媳妇样样都得他操心,她心里很感激他。每到入冬前,手巧的她都要给他织件毛背心,他的气管不好,最怕着凉了。每次杀年猪,她都要把他连同他儿子一家喊来香香地吃顿猪肉,可有好几次,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每次她都没有叫上大伯嫂,为这事嫂子没少怄气,拿话给她听:“一家人就多我自己吗?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能吃你多少肉?顶多吃你一小碗,难道会把你吃穷了吗?”她自知理亏,笑嘻嘻地端碗肉去算是赔罪,但下一次还是没有招呼嫂子吃肉。
正当人们期待他康复的奇迹再次出现的时候,却传来噩耗。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他一下子背过气去,再也没有醒来。一向注意仪表的她,也顾不上洗脸梳头,跌跌撞撞地赶来。院门口,灵棚已经搭起来了,里面那口红木棺里躺着亲亲的他。棺木的正前方摆着他的大幅黑白照片,年轻俊朗的他头顶着白菊花正对着前来吊唁的人微笑呢。香烟一缕缕飘起来,萦绕在他的脸上迟迟不散。她扑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花白的头重重地磕在棺木上,“老哥呀,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话没说完就昏过去了。人们立即把她抬进屋,放在炕上,又是掐人中,又是呼喊她,一阵紧张的忙碌,她总算醒过来了,紧闭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失神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天花板,眼泪一滴接一滴地落下来。
“莫非中邪了?”
“不能,是悲伤过度。”
有人在议论。雨裹着厚重的悲伤还在下着,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再好好地陪一陪他。一天一夜过去了,当黎明再次来临的时候,她依然躺在床上,水米不进,眼睛一直睁着。
已经6点了,该起灵了,屋里的人大都去院门口观望,要送他走完最后一程。重重的棺木被抬起来放到车上。
“起灵——”,随着一声命令,他的儿子“砰”地一声摔碎了那只盛过纸灰的瓦盆,灵车在“隆隆”声中缓缓启动了,披麻戴孝的黑衣人都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她突然手脚聚拢,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起来。
“快找人看看吧,她的魂被掳走了。”有人找来了医生,给她注射了镇静药和强心剂,她醒过来了,这回却是双眼紧闭。
“怎么会这样呢?大伯子死了为他悲痛,流些眼泪是正常的,可她悲痛到这种地步,让人怎么也理解不了。”
她是听得到这些窃窃私语的,却置若罔闻,她只知道,从此在这个世界里再也看不到他了。想起这些,已经干枯的眼里又盈满泪水,泪光中,如烟的往事波纹般一幕幕荡来——
年轻的时候,她曾有过一段美满的婚姻,女儿出生那年,丈夫在一次下矿采煤时遇难。一个羸弱的女人带着孩子过活,日子很是艰难。有好心人给她寻婆家,就把回乡探亲的他介绍给她。他老母说:老大长相俊,还识文断字,不愁娶媳妇,还是说给闷葫芦一样的老二吧。媒人知道她心气高,提议由老大代弟相亲。他坚决不肯,可看到老母愁白的头发,弟弟可怜巴巴的眼神,他答应了。
在一户农家,他见到了俊俏白净的她,素花衣服衬着那张桃花一样的脸,更加娇媚可爱。这么美的姑娘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看到她一汪盈盈的秋水,他心里很慌乱,忙把视线挪开,投到窗外新蕾初绽的桃树枝上,一对小鸟正热烈地对着情歌。
看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领口露出一圈洁白的衬衣,英武的眉宇间闪烁着一双炯炯的眼睛,那风度、那气派是村里任何男子都无法相比的,她像喝了桂花酒一样,心儿都醉了,爽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
一周后,她嫁到了他们家。吃过酒席,晚上入洞房,羞答答的她左顾右盼,终于等来如意郎君。门开了,羞怯地抬起头,她一下子驚呆了,面前站着的这个人不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他,却是又黑又丑、又憨又痴的老二。木已成舟,一切不可逆转,蒙上被子,她哭了一夜。那一夜,隔壁的他也没有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