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须加码
文/本刊记者 陈相龙
医学伦理是贯穿于医学研究与临床全过程的无形准绳,当其面临风险时须提高警惕。
医学伦理事件轮番登上“新闻头条”,将医疗行业推向舆论风口。2018年11月,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声称他已促成全世界首例基因编辑防艾滋病的婴儿诞生。仅仅隔了数月,2019年2月,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陈小平教授利用疟原虫治疗晚期癌症患者引发广泛关注。
“医学伦理是无形的准绳。医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科研伦理问题不容忽视。”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段丽萍教授指出,医学技术本无罪,但失控的技术可能带来灾难。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安身之本。无治理则无伦理,让科技趋利避害,还要寄希望于科学家的道德自觉。
伦理审查是道“关口”
大多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的诞生,需要通过基础科学论证,才能开始进一步产品化。在此过程中,需要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并在通过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和试验,而伦理委员会负责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审查。
“伦理审查的目的就是通过伦理观念的制约,把好医学和临床研究的‘道德关’。”北京天坛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党委书记宋茂民向本刊记者介绍,有三类内容需要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查:一是新药、新医疗器械、新耗材和新设备等新产品上市前的临床试验;二是临床科学研究;三是各医疗机构临床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例如某个专科领域的第一例手术。
事实上,伦理审查是为了保护前述三种情况所涉及的受试者的尊重、权利和安全。所以,伦理审查是一个严肃、讲科学的过程。
宋茂民表示,“以药物审查为例。在全世界范围内,一款新药从研发到进入临床用于治疗疾病,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并且,药物在进入临床之前必须进行伦理审查”。
企业的新药研发在完成实验室阶段的研究之后,若要上市进入临床,企业(申办方)需要向国家药监局提交实验室研究的有关数据及资料,接受临床试验(人体试验)前的审核。宋茂民指出,“这道关口非常严格,药监局有评审专家进行评审和评价。如果药品通过审核,得到国家给的临床试验许可,就可以去找具有临床试验资质的医院(多是三级甲等医院)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医师负责牵头代表申办方制定临床试验方案,申办方向该医院伦理委员会提出审查申请,获得通过后才能开展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一般分为四期。
第一期开始前,就需要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内容是药品的实验耐受性试验和药代动力学试验。目的是初步了解试验药物对人体的安全性情况和人体对试验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消除情况。第二期开始后,医院伦理委员会继续审核,内容是药品治疗作用初步评价阶段。目的是评价药物对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第三期开始后,伦理委员还要进行审核,内容是治疗作用确证阶段,其目的是进一步扩大患者的样本案例,验证药物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为药物注册申请的审查提供依据。之后,便可以上市生产。第四期临床试验为新药上市后的应用研究阶段,其目的是观察患者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
综上所述,伦理委员会的认可对药物市场化进程的节奏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新药如此,其他内容亦如此。面对如此多在医疗研究和临床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审查的“事情”,现阶段伦理委员会究竟是如何审判,从而保证方案“符合道德”的呢?
“在目前的国际规范里,对伦理委员会审查及讨论表决有着程序规定。”宋茂民介绍,首先,由主委主持对临床试验方案进行审查的提问和讨论,但主持发言不能有倾向性,要保持中立。提问和讨论两个阶段都是先由两位主审先提问或表态,然后其他人自由发言,之后主委才能发言。最后主审先归纳总结,其他人补充,主委总结委员们的意见,给出综合建议,秘书记录。最后全场与会委员进行表决,决定是否通过研究方案。
伦理委员会审“案”结论可能产生四个结果:一是通过方案;二是提出方案修改意见,修改后通过;三是提出方案修改意见,修改后重新上会再审;四是不通过方案。
四个结果客观且公开,相对规范地保障了伦理审查的后续操作。宋茂民表示,“有的试验方案对某些患者可能具有利益诱惑嫌疑,伦理审查要为这部分患者把住关,避免患者因被诱惑而参加试验,以保护弱势群体。”
“关口”摸索道路崎岖
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人口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对伦理的认识差异以及审查水平参差不齐是我国伦理委员会审查的一个显著特点。宋茂民指出,“伦理受到地域、民族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审查水平也有差别。”
国务院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原卫生部制定的《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是目前我国活体器官移植基本性法律文件。两部法规文件明确规定:活体器官捐赠者必须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接受人限于配偶(仅限于结婚三年以上或者婚后已育子女)、直系亲属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如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
宋茂民讲述了一个他熟知的事情,在数年前,广州市发生一则关于伦理审查捐肾的新闻。一个需要肾源的患者找了有亲情关系的人给他捐肾,但是广州某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没有认可通过捐赠者与受者之间的“亲情关系”。随后,这个案例在海南省某医院的伦理委员会通过了伦理审查,肾移植手术得以实施。因此,伦理审查没有绝对性,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有关系。
不仅如此,经过数年的经验摸索,我国的医院在伦理审查问题上还存在审查流程不规范等问题。
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卫生法学教授王岳介绍,“现阶段,诸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对人员的相关资质没有严格的要求,有些人还对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的概念有误读。并且,很多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现阶段没有民主氛围,还是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来审核方案,欠缺一些更加科学的进程。万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这些少数人的观点可能并不是错的。”
“我国在医学伦理问题方面起步确实比较晚,但这并不是审查水平差的最主要原因。关键问题还是许多医院对伦理审查不够重视。”宋茂民指出。
天坛医院伦理委员会在20世纪90时代末成立,2010年前后开始更加规范,并且还取得相关资质的国际认证。截至目前,在受试者保护体系建设方面,在全国各类医疗机构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医院具有比较完整的受试者保护和伦理审查体系,很多医院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伦理委员会今后的发展方向,王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伦理委员会应该是争鸣的地方,要有一个非常充分讨论的机制,要有‘黑的白的’各种不同观点。通过一系列辩论,最后委员们进行相互说服,而不能简单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匆匆结束。”
王岳还提出,“相关部门对省一级的伦理委员会应进行权威认证。伦理委员会的委员也一定要有相关资质的认证,从而进一步提高委员们的业务能力。委员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问题。”“伦理审查没有高低之分,培训伦理委员会委员的素质和审查水平是个永恒的课题。”宋茂民这样强调。
伦理委员会固然需要继续进一步发展,而患者的权益在伦理审查中如何保障呢?据了解,在涉及患者的伦理委员会方案里,患者签的知情同意书直接影响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与否。
对于“知情同意”的定义,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国豫表示,一个完整的知情同意过程至少包括三个要素:行动主体、行动客体(即知情同意主体)、行动的目的。数据的可信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是知情、告知的前提。而对于医生和研究人员来说,面对海量的数据,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哪些告知哪些不可以告知?选择的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都是决策的依据和 标准。
尽管如此,我国的医患在知情同意问题的推进上依旧存在诸多困境。
首先,我国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其次,受试者的选择能力与对风险的可接受能力较弱,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然后,患者对疾病的态度和对风险的可接受性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文化差异性)。这些都是考验患者理性能力和是否决定签下同意书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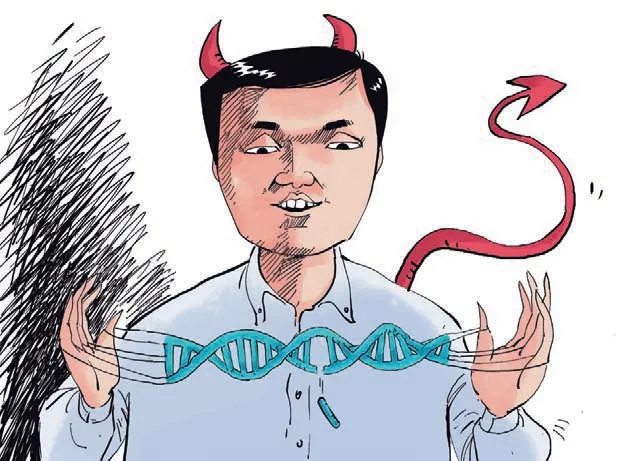
遵守科研道德是科技工作者的基本行为准则,恪守科研伦理是科学家的重要社会责任。
“医患之间一定需要建立信任感。”王国豫提出,如何在履行告知和解释义务时,做到不伤害且对患者有利,这是研究人员和医生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
伦理风险亟待关注
“对于疾病,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疾病与死亡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但是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战胜了。我们应该去重新审视医学的使命。”王岳认为,医学的使命并不是消灭全部的疾病,而是尽量去提供更多帮助患者的方法,从而解决患者的问题。但是面对疾病,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治病”,就是一定要把病症消灭掉。
在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著的《善恶的彼岸》146小节中有这样一句话,“When you look long into an abyss,the abyss looks into you ”意思是“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会注视你。”这句话非常契合我国医学伦理行业的现状。
目前,国内伦理审查机制尚不完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却在持续提升。过去,科研似乎更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进行。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科研项目的覆盖面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担起重要科研任务。医学科研越来越深入基因,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伦理审查机制也陷入困境。
王国豫指出,“现在,患者已成为医学研究的参与者,医学伦理学因此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今的医学诊疗在概念和模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疾病与健康、治疗与试验、患者与参与者、医疗与消费的概念正在变得模糊。
“我国医学高速发展的五六十年来,对于一些癌症依旧束手无策。”王岳表示,药物只是延续生命的工具,并不能完全治愈癌症。一旦从根本上治疗就要涉及基因编辑技术。
事实上,人类进化的过程也是基因不断编辑的过程,但是编辑基因的不是人,而是自然这把剪刀,自然选择在基因突变中基因筛选和编辑的作用,决定了进化的方向。
王国豫介绍,过去的医学干预主要还是停留在表观遗传学的层面,但是生殖细胞上的基因编辑将有可能传给后代。
在基因医学领域上,有数个实例已在进行。“地中海型贫血基因编辑技术”将患者的患病基因改成正常基因,从而造福一众罕见病患者;而“基因编辑婴儿”却修改了人类的正常基因,让婴儿天生就可能拥有某种免疫缺陷,用人体来做这种目前无法估量后果的实验,是不人道、违背医学伦理的体现。
“整个基因的多样性就像是一池湖水,别有用意的基因编辑,会打破湖水的自然性。”王岳指出,很多企业愿意和科学研究院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一旦有了商业机会,在巨大的商业利益之下,某些科学家就会脱离专家共同体,成为具有科学知识的商人,然后利用知识去“为所欲为”。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科学家可以无视“国自然”等官方鼓励金,因为他们不缺项目基金,甚至通过商业融资,他们可以轻松融资到数亿元。
科学家的伦理审查和专家共同体的约束对于此类科学家已经不起作用。因此,对专家行为的规制不能只靠伦理,还需要依靠刑事立法。“刑事立法是约束和制约这些行为的有力机制,因此刑事立法的确迫在眉睫。”王岳这样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