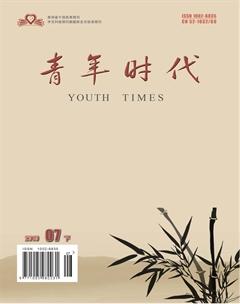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魏怡丹
摘 要:郭沫若作为留日文学团中的重要成员,在留日期间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其中日本女性的形象极富典型性。本文将从正面的妻子形象、纯情的少女形象和丑陋的妻子形象3方面对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进而探索作者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郭沫若;留日小说;女性形象
一、引言
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悠远的文化交流,中国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中日最初的交流始于汉代。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远,因此,从古至今,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才这般频繁,到了现当代更是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管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这些五四文学的先驱者,还是前期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几乎都曾留学日本。正因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有不少作家都写过与日本有关的作品,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位。郭沫若在日本见识到了各种类型的女性,遇见了后来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后改名郭安娜),并以她们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其中的女性角色既是日本社会女性形象的缩影,也是作者内心情感的隐晦体现。
二、正面的妻子形象
在日本典型的男权社会中,妻子的地位一向是低微的。在影视画面和相关文字资料中都常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丈夫回家时,妻子都会跪在门口或者鞠上一躬说一声“您辛苦了”表示迎接。这样的社会地位也间接塑造了日本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吃苦耐劳的形象,而郭沫若的妻子郭安娜也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性。
1916年,郭沫若与郭安娜邂逅相遇,两人通过通信确定恋爱关系,不久后同居。郭沫若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别离》《Venus》等最早的一批白话诗都是献给安娜的。两人同居后,生活拮据,尝尝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但安娜依然尽心尽力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照顾家人。在郭沫若的小说中,以安娜为原型的妻子形象就是一个吃苦耐劳、坚强独立、沐浴在圣洁光芒中的人。
《歧路》中展现了一个极为坚韧的妻子形象。“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人,7年前和他自由结婚了,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她本来期冀着他回来后能靠医学在社会上立足,使他们一家摆脱贫苦的生活,可他“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重新投入了文学的怀抱。但是在当时中国,文学是无用之物,又加上失去了每月的官费补助,他们的生活日渐窘迫。最后他的女人终竟苦于生活的压迫,到头不得不带着3个孩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而且她还宽慰丈夫:“福冈还有些友人,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闲游的,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一个妇女独自抚养3个孩子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尽管到了这般地步,她仍说:“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别的生活你别要顾虑。”妻子对丈夫心怀无尽的体贴和包容,使得一个近乎完美的妻子形象鲜明跃然于纸上。
《万引》里,松野在图书馆偷了一本“chatterton”,偷完他就担心妻子知道后会大发脾气,因为“她是再不肯做亏人的事的人。平常不怕就是家贫,她是从不肯拖欠,想方设计把每日每月的生活总要弥缝下去。她现在和他同过着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甚么怨言,把她全部的青春为他抛弃了,正因为爱他,尊敬他的人格”,所以妻子知道真相后痛心疾首地责怪了松野几句,不愿在孩子面前损毁形象的松野恼羞成怒,反而朝妻子发了一通脾气。有错在先的松野生着闷气,却不愿放下面子先行认错,反倒是“他夫人最后走到他面前来,反转先向他赔了一礼,说她刚才说的话过分了,望他不要介意”,还把手上的戒指取下来让松野当掉换钱去补上书的钱。既明辨是非坚守道德底线,又善解人意包容丈夫,这种伟大的妻子品格最终使松野自我忏悔,恶念和罪行也得到了妻子圣洁之光的救赎。
三、纯情的少女形象
不同于崇高圣洁的妻子形象,郭沫若小说中的另一类主角是纯情、稚嫩的少女形象。如果说郭沫若在描绘妻子形象时是心怀崇敬和赞美的话,那么在勾勒少女形象时则是心懷悸动和欲望的。
这一类的少女,有一些怀有超越她们年龄的深情。《牧羊哀话》中的牧羊女郎本是名门小姐,却因青梅竹马英儿死于非命,甘愿留下替他守护羊群。两人关系极好,时常一起牧羊,一次两人半夜还未回寺,大家四处找寻后才“远见得一群羊儿睡在海岸上。英儿靠着一个岩壁,佩荑小姐靠着英儿的箭头,他俩早都睡熟了”。英儿母亲也说:“小姐常对我说,自从英儿死后,大小羊儿,总是不肯十分进食。几年之内,早已死了一半多了。羊儿每死一匹,小姐总要伤心一场,还要在英儿的墓旁,替它作座羊冢。我想我那英儿,他在九泉之下,定不会十分寂寞的呢。”两人深厚的情谊没有因为阴阳相隔而消散,佩荑小姐将守候和思念寄托在羊群身上,融深情于日夜守候之中。
而在《落叶》中,菊子姑娘的爱则炽烈又直白,她为中国留学生洪师武写的41封信,流露的全是深情和爱意。菊子几乎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真切地称呼洪师武为“我亲爱的哥哥”或“我挚爱的哥哥”,表达自己对洪师武真诚的感情以及深深的思念与牵挂。“知道我的心的,能够做我的全依赖者的只有我哥哥一人”,菊子将洪师武视作精神信仰,来往的书信是她灰暗生活的精神支柱。在最后一封信的结尾,菊子姑娘带着近乎绝望的语气写道:“哥哥,我祈祷你永远过着平安的生活,永远得着救度,永远不要再失掉了你的信心。”无数声恳切的“哥哥”让人潸然泪下,绵长的41封信,记录了菊子姑娘从满怀希望、陷入矛盾,到最后完全绝望的心理过程,言语之真挚,情感之炙热,都透过冰冷的文字传递到读者的内心,读之仿佛能看到一颗赤裸裸、滚烫烫的心在纸上跳跃着。虽然作者未曾对菊子姑娘做具体的形象描绘,可从她字字含泪、句句含情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无疑是个如白云一般纯洁、善良,又怀揣着如海浪般翻涌爱意的少女。
美好的少女同样也吸引着郭沫若,在《喀尔美萝姑娘》中这种痴迷和欲望尤为显著。“我”见到喀尔美萝姑娘的第一眼就沦陷了,“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至那之后“我”便抓住一切机会接近喀尔美萝姑娘,瑞华给“我”的钱也尽数献给了她,只为创造两人相遇的机会。“我的性格已为她隳颓,我的灵肉已为她糜烂,我的事业已为她抛掷,我的家庭已为她离散了”,“我”还因为思念过度梦见与喀尔美萝姑娘亲吻,以至于梦醒后发现身边人是瑞华时失落至极,感慨“我怎么不死在梦里呢”。
喀尔美萝姑娘是生机的、灵动的、娇美的,与端庄贤良的妻子相比,她充满了诱惑和无尽的想象。“她一见了我便把眼睑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样的浓密,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富有生命力”,从对喀尔美萝姑娘的描绘中就可以看出,她带给“我”的是青春的气息,如同在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投放了一颗炸弹。长久的陪伴使“我”对妻子的爱逐渐转变成了质朴的亲情,妻子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我”也安于接受这样的馈赠,心绪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趋于麻木。可遇到喀尔美萝姑娘后,“我”沉睡的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着魔一般心甘情愿为她做任何事,这才是接近人类原始爱欲的充满欲望和激情的男女之爱。
四、丑陋的妻子形象
这类女性在郭沫若的小说中并不多见,因为郭沫若多是带着一种褒奖和赞美的眼光去塑造女性形象的,但日本女性也并不全都是真善美的化身。
《鼠灾》的篇幅不长,却把方平甫妻子自私自利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她为掩饰自己的失误,态度油滑地说道:“不是二三十块的东西!不晓得你要怎样地怒我。”阴阳怪气的语调愈加凸显了她的心机和心虚:她将自己的衣服放在好箱子里,将丈夫的衣服放在烂纸箱里,导致老鼠咬破了平甫那件极其珍贵的冬服。但平时,“每逢他女人的东西搅坏了,或者放遗失了的时候,他(女人)是定要冒火,闹得一房间的空气如象炭坑里的火气一般的。今天他的冬服咬坏了,他(女人)却那样平静”,郭沫若不先直接描写方同甫妻子火爆的脾气,而是以娇嗔的话语作铺垫,再通过方同甫的心理活动侧面体现妻子平日的蛮横无理,从而形成鲜明的形象反差,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方平甫这位日本妻子自私自利、乖张圆滑的形象。
《鼠灾》中的妻子虽然令人厌恶,但实际不过是被贫苦市井生活磨坏了性格的家庭妇女,但《曼陀罗华》中哈君的日本妻子却是从心底里坏透了,她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凶狠歹毒,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诺儿也毫无疼爱之情,是个心灵极其丑陋的世俗妇女。她爱慕虚荣,“姿首并不美,却总爱涂脂抹粉”“前年来的时候是二十岁,去年还是二十,今年也还是二十”。是她的疏忽导致儿子小小年纪就生病死亡,但她对这件事情不但不感到伤心自责,反而打扮得非常华丽去看孩子解剖,“一阵阵的粉香、椿油香、香水香空气中浮泛”,相比起孩子的去世,她更在乎自己的形象,她甚至还跟将孩子的死亡当成一个求取金钱的借口。从中可以尽览哈君这位日本妻子唯金钱是图、丧失人性的丑恶面孔。
作者摹写这类形象丑陋、性格自私的日本女性形象,不仅出于对客观现实的观察,也源于自我心境的流露。通过描写受这类丑陋女性打压、控制的男性处境,展示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悲惨境遇,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留学生在他乡苦恼、无奈、抑郁的心情。郭沫若笔下的这类丑恶形象不仅是对现实中某些现象不满的表现,也是作家对苦闷、压抑与无奈情绪的一种发泄與释放。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即鲜活又具有典型性,从对日本女性的描绘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作者的内心情感。在陌生的国度里,女性既是家庭生活的贤内助,又是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托,所以对于这一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外界进一步了解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动向,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