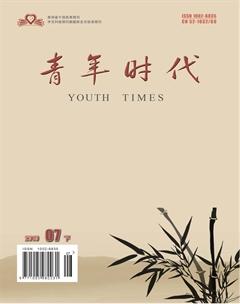论关仁山小说《麦河》的生态叙事
龚新越
摘 要: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麦河》基于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借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反映了工业化给传统农村带来的生态危机,蕴含着重建文明观念、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从自然环境和农民精神两方面着手,分析关仁山在《麦河》中的生态思考,探讨土地政策与生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多元平衡问题对于当下的文明反思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关仁山;《麦河》;生态叙事
一、引言
2002年,我国颁布《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政策成为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重大转型。关仁山敏锐地观察到了新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政策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小说《麦河》将当代环境问题与政策相结合,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土地问题做了纵深式的追述,从而引发作家对于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方面的思考。本文从自然环境和农民精神两方面着手,分析关仁山在《麦河》中的生态思考,试着探讨土地政策与生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多元平衡问题。
二、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质疑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习总书记也痛定思痛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仁山的《麦河》在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书写中,把自然环境作为个体进行烛照,对河北平原的优美景色进行诗意描绘,又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了工业化、城市化给土地造成的生态压力。
《麦河》中用大量笔墨书写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被工业化侵占后,麦河地区的风景画发生扭曲。土地因为现代农业的侵入,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造成了大面积土地板结。麦河坍塌、天坑的出现更是触目惊心。白立国不禁提出了深层问题:大自然究竟咋啦?是大自然害了人,还是人破坏了大自然?诚然,如果人们无节制地侵犯自然、改变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小说中提出一个命题:要让土地变成聚宝盆。这是曹双羊离开土地时留下的誓言,然而事实是“乡村一步步变成一个庞大的没有厂房的大工厂了”,其结果是青山没了、绿水没了,农民依然贫困,前途渺茫。从这个过程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工业化进程=远离土地的进程=糟蹋土地的进程=生态破坏的进程。工业化进程确实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其代价也是巨大而惨痛的。
其实,关仁山并没有因为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系统紊乱而对人与自然关系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而是在《麦河》中对未来乡村发展寄托了美好的愿景,他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苍鹰虎子抒发出来。小说中用一整个章节“遥望未来”借虎子之眼预言了30年后鹦鹉村的生态景观。30年后的鹦鹉村已经城镇化,它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农业规模”,“麦河还是那个麦河。土地还是那片土地。……这条河就更加灿烂了。”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纯净、有序、自然,仿佛白立国童年记忆中的麦河。白立国把他对土地全部的深情都融入未来乡村的想象中,这是近乎乌托邦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想象的世界或者说是预言的世界,是不拒斥工业文明和城市化进程的,是现代工业生产在自然生态环境下运营得井然有序之景,这无疑是寄托了关仁山对于乡村自然生态和工业发展达到平衡的美学理想。
三、农民精神的生态危机
关仁山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不仅涉及自然环境中的土地问题,还包括农民的精神问题。《麦河》中的关仁山设置了根植于土地、固守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守望者,向往财富、大胆冒险的新一代农民改革者,以及背叛乡村、寄居城市的新一代农民逃离者,从3类人物的心理变迁和命运沉可以浮窥见农民精神所遭受的生态危机。
第一类是根植于土地、固守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守望者,是包括瞎子白立国在内的农村中的大部分群体。土地流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要求土地入股,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拿出来集体致富。这无疑是对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农民的一个巨大挑战。白立国面对热热闹闹的现代农业发出了“不种粮食,种菜、花、蘑菇,要是有个灾年农民吃什么?”的质疑;曹双羊的母亲曹大娘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轮回式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而不知所措;郭富九对农村走向机械化、集体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失地的农民”刘凤桐和转香因为村里要把土地变成马场而想要自杀;甚至连死去的枣杠子灵魂都吐露出了“没有地种多难受啊”的感慨……。其中,失去土地的叹息、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失落、无根感的苍茫跃然纸上。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上。”[1]农民的精神生态中丧失了土地,他们便踏踏实实踏上了虚无。事实上,固守土地的老一代农民并不意味着落后和愚昧。作者对于这类农民并不是持批判的態度,而是对于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无从生存的局促感,现代农业圈套中的迷失感给予关注,这表现了关仁山在创作中“聚焦底层人物命运,关注弱者复杂的命运”的“悲悯情怀”[2]。
第二类是向往财富、大胆冒险的新一代农民改革者,以曹双羊为代表,他们在攫取财富的过程中变得贪婪、凶残,渐渐迷失自己,而不得不走向灵魂救赎之路。他们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变得越发贪婪疯狂,“满脑子都是赚钱之道,整天沉浸在物质狂欢里,灵魂已经没有家园了”,他以“经历开发,造福百姓”这类冠冕堂皇的字眼进行欺骗、恐吓、厮杀,甚至不惜将农民的土地作为抵押换取资本积累。“人的‘意志能量不再‘向上仰望,而是‘向下、向着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壑‘猛扑过去。”[3]小说中的曹双羊等人渐渐沦为欲望的工具、金钱的奴隶,但当曹双羊遭受精神煎熬与折磨时,麦河又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着曾经伤害过它的人们。事实上,在现实中受到种种羁绊,转身回归故土,投入自然的怀抱以完成精神救赎是人类共同的道路选择。
第三类是背叛乡村、寄居城市的新一代农民逃离者,以麦圈儿为代表。她在城市里的堕落一方面受到城市生活的引诱和生活的逼迫,一方面源于自己的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好吃懒做。作家对于她的救赎只能以自杀的方式完成。这里既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好逸恶劳价值观念的否定,又可以看出他对底层女性的人道主义关怀。
可以说,作家对于曹双羊、桃等人的精神救赎、精神生态的保护出于他们没有完全被经济浪潮席卷,还保留了人性善的一面的肯定;而对于麦圈儿的悲剧结局,则是对人沦为欲望的奴隶的彻底否定;至于传统农民如何在变革与坚守中获得精神家园的丰富,关仁山只是在小说最后以“小麦图腾”这样缥缈的观念进行图解,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四、多元平衡问题的反思
面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阎连科以“炸裂”,賈平凹以“浮躁”,张炜以“愤怒”书写现代文明侵入农村之迅速与之带来的病态。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农村拒绝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始终处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下就是农民应有的出路吗?城市在的钢筋水泥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城市人体验着炫目的灯光和快感时,农民为了自然生态保护而拒绝发展,年复一年过着贫穷而枯燥的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是公平的吗?这种矫枉过正是对无数想要摆脱贫穷获得资本和人生的广阔疆域的高加林们、涂自强们、曹双羊们的忽视,所以没有人可以以资本伤害土地为由拒绝农村发展。“生态文学对工业和科技的批判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工业和科技本身,而是要突显人类现存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致命缺陷,促使人类思考和探寻发展工业和科技的正确道路,以及如何开创一种全新的绿色工业和绿色科技。”[4]关键问题在于,开发利用土地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懂得透过历史的教训反思当下的经济建设,只有做到“竭泽而渔”才能持续发展。这也是《麦河》中反复要依托麦田这样的自然风景来守住农民的精神家园的意义所在,只有精神家园没有被遗弃,才可能有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并存。
关仁山善于“将遥远的政治话体转化为近距离的文学问题”[5],但关仁山不是政策的歌颂者,而是反思者。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他始终保持着理性的眼光,既关注到它给农村带来的便利,也关注到变革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其中,小说客观地向读者展示了土地流转政策给农村带来的优点,例如,利用不可耕土地创收,机械翻地减轻劳动力,科研进乡发明农副产品等。如果改革能够如政策制定者预想的那样行之有效地实施下去,其结果必然是改善民生的,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必然存在着鸿沟,其中就有改革所造成了自然环境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危机等。城市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改革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车轮,其中对旧有体制的变革伴随着时代的阵痛,其中的掠夺与流血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仅仅靠依恋土地,固守土地只能保持贫穷。时代的必然和农民生存的困境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关仁山在小说最后以土地对曹双羊等人的精神救赎结束,笔者认为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土地流转究竟能不能够做到不以破坏土地为代价而使农民生活得到富裕,这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无论是自然生态危机还是精神生态危机,或者说社会生态危机,都应当意识到:改革的有效实施和社会制度的完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如果真的等到“亡羊”时才知“补牢”那就为时已晚。关仁山意识到从社会制度根本出发去解决生态危机这种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正确,但在现实中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容不得等到制度完善后再去解决。因此,改革与环保需要同步进行。所以白立国必须先把曹双羊拉回到土地上,才可能有苍鹰之眼的想象。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M].郜元宝,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陈国和.乡村小说视域下的当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书写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陈国和.乡村小说视域下的当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书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