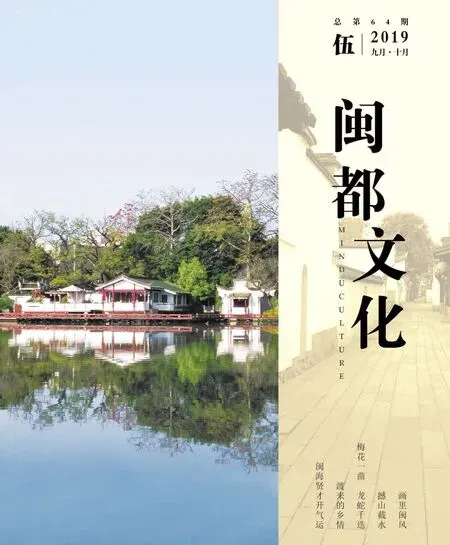黄叔璥笔下的闽粤驿道
黄绍坚
清代康熙六十一年(1722)农历正月二十一日,40岁的北京大兴籍进士黄叔璥(1682-1758,一说1681-1757),与满洲御史吴达礼一起,被任命为首任巡察台湾御史。黄叔璥是位老实人,一生宦位平平,但为官踏实本分,撰有《台海使槎录》等多部重要著作。此次赴台,他留下一部日记体著作《南征纪程》,逐日、逐站记录下他由京经闽入台之旅程。
尤为珍贵者,黄叔璥记录下从福州经泉州至厦门的闽粤驿道北段的详细行程。根据《南征纪程》的记载,我仔细对照一下今日地名,黄叔璥当年行程如下:1722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黄叔璥离京出发,沿大运河—钱塘江—富春江一路乘船南下。四月八日,经闽浙交界处“仙霞古道”,越南平市浦城县九牧镇“梨岭关”,进入福建,先沿建溪,陆行至南平市区,然后再次登船,沿闽江南下。四月十七日,乘船至福州“洪山桥”上岸,入福州城。他没有住官驿,而是住到朋友家。四月二十日,出福州南门,经福州台江区“万寿桥”(他写作“南台桥”),过闽江,宿南台岛上的福州仓山区三角埕(他写作“山角埕”)。二十一日,渡乌龙江,宿福州闽侯县青口镇坊口村。有人请他吃鲎,他觉得味道一般。二十二日,经闽侯县青口镇东台村“相思岭”(他写作“常思岭”。福州话读音相同),入福清市,宿福州福清市渔溪镇。这天他留下两则重要记载:一是在相思岭下,当年有明代大学士叶向高墓(原墓已毁,遗址在今福州闽侯县青口镇东台村戊辰自然村);二是关于福建廊桥的记录:“自浦城至福州,桥梁或五里,或十里,矗立水中,翼翼楚楚,憩足偃息,可蔽风雨。周栎园(周亮工)每以两隅覆木板为憾,谓其俯栏有致,游目无余,良然。”

洪山桥旧桥墩
远在康熙末年,黄叔璥已敏锐地注意到福建独特的廊桥及廊桥两侧护桥的裙板。二十三日,过福州福清市新厝镇蒜岭村的“蒜岭”,渡木兰溪,宿莆田市荔城区“兴化府考院”。二十四日,过木兰溪上游的“濑溪桥”(位于莆田城厢区华亭镇濑溪村),经莆田仙游县枫亭镇时,寻找著名的莆田荔枝名品“延寿红”,未果,宿泉州泉港区涂岭镇。二十五日,早上赶到泉州惠安县城螺城镇吃早饭,中午经著名的宋代古桥“万安桥”(又名“洛阳桥”),过洛阳江,入泉州城,宿“泉州府试院”。二十六日,经泉州晋江市磁灶镇五龙村(时称“古陵”)“熊公庙”(祭祀明代泉州知府熊尚初),越大盈岭、小盈岭,宿厦门翔安区内厝镇前垵村“沙溪铺”。黄叔璥注意到,闽粤驿道泉州至厦门段,行人“往来如织”。二十七日,经厦门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他写作“刘武店”),乘船30里渡海,至厦门五通(他写作“浯通”)登岸。从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的8天时间里,黄叔璥赶了至少560里路,翻山越岭,渡河跨海,直抵厦门。其尽忠职守的为官态度,令人感叹。
我注意到,在黄叔璥从福州赶赴厦门的行程中,他极少住官驿,更多时候选择住在朋友家或试院这类可供借宿的办公场所。我猜,黄叔璥急着赶到厦门、转赴台湾公干。不住官驿,可以省却不少官场繁文缛节。
闽粤驿道福建段全长1030里,约合593公里,全线共设17驿又2处“塘驿”,沿途须跨越闽江、龙江(福清)、萩芦溪(莆田)、木兰溪(莆田)、枫慈溪(仙游)、洛阳江(惠安)、晋江(泉州)、安海港(晋江)、东西溪(同安)、九龙江(龙海)、鹿溪(漳浦)、漳江(云霄)、东溪(诏安)等大小河流、港湾,须翻越蒜岭(福清与莆田之间)、白水岭(仙游与惠安之间)、大小盈岭(南安与同安之间)、九龙岭(龙海的程溪、长桥镇之间)、盘陀岭(漳浦与云霄之间)、油柑岭(云霄与诏安之间)、黄石山(闽粤交界)等大小山峰。换句话说,官商行走在闽粤驿道上,正常应该走16天,平均每日行程64里许(约合37公里)。其间山高谷深,滩险流急,跋涉维艰。“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诗经》里的诗句,几乎就是八闽大地交通的真实写照——但是,客观来说,在清代闽地出省的5条官驿中,闽粤驿道是最好走、最安全的一条。
闽粤驿道的起点——从“崇轺驿”到“三山驿”。宋代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记载,王审知在福州城“登庸门”内,建“崇轺驿”,接待朝廷派来册封的使者翁承赞。唐末福州城南,筑月城,月城的南城门即“登庸门”,位于今天福州鼓楼区南门兜一带。“崇轺驿”是福建最早设立的驿站之一。到宋代,福州城内设5驿、10铺。5驿分别是:使星馆、迎仙馆、崇轺驿、如归馆、皇华馆。其中,“迎仙馆”设在“南禅寺东”,后废,改设“如归馆”。福州地方文史学者王铁藩先生考证说,宋代“迎仙馆”,其址在今天福州鼓楼区华林路的福建省政府大院内。唐代日本来华的空海法师,便由此出发,北上进京。还有一处宋代接待宾客的重要驿站“皇华馆”值得一说。它位于宋代福州城“还珠门外,旧‘春风楼’地”,即今天福州市鼓楼区东街口附近,始建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7)。福州城“还珠门”,始建于唐哀帝天祐三年(906)。自宋代至今900年间,还珠门/东街口一带,都是福州城最繁华热闹的所在。福州女性风情万种,“转桥祈福”之俗历历在目。在“还珠门”外建“皇华馆”,接待远方来客,足见福州人的细心与体贴。“还珠门”外再往南面,有“镇闽台”,后代改建为“狮子楼”,至民国时期扩建福州南街时方毁。更南面,今天福州鼓楼区道山路“安泰桥”边,则是当时福州的外城门“利涉门”(址在今福州道山路“冠亚广场”附近)。宋代福州知州曾巩作过一首著名的《夜出,过利涉门》诗:“红纱笼烛过斜桥,复观翚飞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当年,“利涉门”外,便是闽江入海口,樯桅如林,风帆如堵,商旅云集。著名的乌山,还只是海边的一座小岛。而鼓楼、还珠门、镇闽台、利涉门这条南北中轴直线,构成福州“南大街”,即今天福州八一七北路,从古至今都是福州城最重要的街道。可惜,经过宋元战火焚劫,宋代福州5驿皆废。乾隆《福州府志》记载,到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福州城内改设“三山驿”,位于今天福州鼓楼区通湖路驿里社区一带,就在著名的三坊七巷的“衣锦坊”西侧。“三山驿”也是清代所有5条出闽驿道的起点,可惜民国年间已毁,现在仅存清代古桥“馆驿桥”及“驿里社区”名字,顽强保留着对“三山驿”的纪念。“三山驿”四周现存的几座古桥,都很有意思。通湖路上短短的“馆驿桥”,原名“车弩桥”,最早是木桥,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改建为石桥。桥边,原有一座祭祀“医官大王”的俗神宫庙。清代翻译大家、福州人林纾说,这尊“医官大王”十分灵验,不仅保佑本社民众,外境人来拜神禳灾祈福,亦无不应验。大家口口相传,最终,宫庙、里社,都以“车弩境”闻名;就连巷子,也名“车弩巷”。不过,随着“三山驿”及附设二公馆(驿馆)的建设,连接“衣锦坊”与“三山驿”的重要桥梁“车弩桥”被叫得越来越少,桥名渐渐变成“馆驿桥”,俗称“驿前桥”。“馆驿桥”南不远处,还有一座重建于清代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古金斗桥”,也在“三山驿”附近,今存。这里原是唐代福州“罗城”的城门“金斗门”的城濠,故桥名“金斗桥”。不知怎么一来二去,大家都传说桥下埋有一斗金子,谁挖到,谁发财。这算是典型的民间望文生义吧?南涧寺建在乌山上。福州习俗,将祭祀疫神的寺庙称为“涧”“殿”。乌山上的“南涧寺”,便在寺旁空地上,另建祀疫神的小庙。当年站在乌山顶上,可远眺闽江入海处波涛汹涌,将福州城里与台江一分为二,“南横一道见溪流”。其时闽江口海水水位远高于今日。闽粤官道,只能出福州南门,渡闽江、乌龙江,循五虎山脚而行。唐宋时期,福州城里与台江、台江与南台岛之间的通行,靠的是浮桥。当年福州城里至台江、南台岛之间,江面宽阔,风高浪急,交通确实不便。到元代时,和尚王法助(约1227-1314)及其弟子们发愿为民修桥,于元大德七年(1303)始建,历时10多年,终于建成闽粤驿道上重要的跨海大桥——福州“万寿桥”(当年台江一带还是闽江入海口)。据说福州长乐闽江口的“金刚腿”原有一对,为采巨石建“万寿桥”,毁了一腿,如今只剩孤腿入江;又据说“万寿桥”石柱上的石狮子,姿态各异,“据说每一狮子都体现南少林‘金狮拳术’的迹形,雕工也极为精致。”其后,海水渐渐退去。闽江入海口,终于退到福州连江县川石岛和福州长乐区梅花镇一带。闽江中的小洲“愣严洲”,变成福州台江区著名的商业街“中亭街”。“万寿桥”则屡经重建、改建,成为今天福州“解放桥”。“千艘横系大江心”的壮观景色,一去不再。

洪山桥旧桥墩
从乌龙江到木兰溪闽粤驿道。自“三山驿”往南,出福州南门70里,经南台岛(今福州仓山区),坐船渡乌龙江,至福州府闽县“大田驿”。“大田驿”位于今天福州闽侯县青口镇宏屿村附近。对照地图可知,黄叔璥没有住在“大田驿”,而是住到大田驿以南3公里左右的坊口村,大约是到朋友家做客,才被招待吃鲎。我喜欢的建宁籍诗人张际亮,走的也是这条驿道。和黄叔璥一样,张际亮也从南台岛坐船渡过乌龙江。不同的是,感情丰沛的诗人,渡江时被乌龙江边五虎山(位于福州闽侯祥谦镇)、鼓山、旗山(都在今福州市区)的巍巍雄姿所吸引,并遥想闽江入海口的川石岛等三岛海天一色的壮阔景象,顿起人生奋进之心。从“大田驿”往南50里,至福州府福清县“宏路驿”,即今天福州福清市宏路镇。张际亮和黄叔璥都未作停留,匆匆赶路。两人都住到宏路镇以南13公里左右的福清市渔溪镇。乾隆《福清县志》中说,渔溪镇有闽粤驿道上的“渔溪铺”,可供行人食宿。那里原来还有明代所建“渔溪公馆”,可惜早已塌圮。福清市渔溪镇,就在兴化湾边上。“宏路驿”往南40里,至福清县“蒜岭驿”,即今天福州福清市新厝镇蒜岭村。越蒜岭,位于宋代诗人刘克庄的家乡——莆田。从“蒜岭驿”再往西南50里,过木兰溪,至兴化府莆田县“莆阳驿”,即今天莆田荔城区雷山路一带。欲过木兰溪,可以走“宁海桥”。宁海桥建在木兰溪入海口附近,即今天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桥兜村,全长225米,始建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现存古桥为清代雍正十年(1732)重建,历时15年告成。宁海桥两侧,至今立着4尊明代风格的“守桥石将军”,其中桥北东侧一尊,低眉慈目,喜气盈盈,让人见了心生欢喜,兴许就忘了旅途劳顿。

渔溪镇郞官村郞官古渡
从“枫亭驿”到“深青驿”。“莆阳驿”往西南行60里。黄叔璥和张际亮都经过木兰溪上游的“濑溪桥”(位于莆田城厢区华亭镇濑溪村),至兴化府仙游县“枫亭驿”,即今天莆田仙游县枫亭镇枫贸街附近。张际亮并留有一首《濑溪》诗:“历历前朝贵客坟,野风吹断赐碑文。清溪莫笑渔翁老,看尽苍崖幻白云。”“贵客坟”,指的应该是清代威略将军吴英的墓道坊及神道碑,位于枫亭镇枫贸街上。这条枫贸街,历史上为闽粤官道的组成部分。枫亭镇是一处特别有故事的地方,这里既是宋代名臣蔡襄的故乡,也是宋代名奸蔡京、蔡卞兄弟的故乡,还有一位令人感慨万千的蔡荔娘“活水亭”的传说。从“枫亭驿”出发往南行50里,过“陈同关”,越“白水岭”,便进入闽南文化圈,到达泉州府惠安县“锦田驿”,即今天泉州惠安县城螺城镇驿顶街一带;再往南50里,过著名的宋代跨海大桥“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抵达泉州府晋江县“晋安驿”,即今天泉州市鲤城区西街与中山路交会处附近的驿内巷一带;再南行60里,过另一座著名的宋代跨海大桥“安平桥”,至泉州府南安县“康店驿”,即今泉州南安市水头镇;又南行70里,至泉州府同安县“大轮驿”,即今天厦门同安区大同街道后炉街果子园一带;又60里,至泉州府同安县“深青驿”,即今天厦门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
从“江东驿”到“临漳驿”。从闽地全省地貌来看,漳州的九龙江中下游平原,是闽省最大的一块沿海平原,也是闽省最富饶的鱼米之乡。闽粤驿道由此而过,当年汲汲于途的官商行旅,大约可以松口气。唐代诗人、写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章碣,作过一首《送谢进士还闽》诗,便在闽北、闽中危崖耸立、滩险流急的背景下,映衬出漳郡生活的几分悠闲、几分从容:史书记载,闽粤驿道从泉州府同安县“深青驿”西行50里,过九龙江,至漳州府龙溪县“江东驿”,即今天漳州龙海市榜山镇长洲村,那一带如今有厦门人熟悉的“江东鲈鱼一条街”。再往前走,须经过漳州门户“万松关”。险峻的“万松关”及万松关古道,至今犹存,位于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梧浦村山上的隘口处。这里是漳州东大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惨烈大战。从“江东驿”西行40里,至漳州府龙溪县“丹霞驿”,即今天漳州芗城区南山路驿前街,当年位于漳州城南门外。又西行40里,路中经过著名的“木棉铺”,位于漳州龙海市九湖镇木棉村。南宋末年,郑虎臣杀奸臣贾似道于此。其后,冯梦龙将这段故事写进《喻世明言》中,广为人知。再往南,越“九龙岭”,抵达漳州府龙溪县“甘棠驿”,位置在今天漳州漳浦县官浔镇溪坂村马口自然村。再西南行50里,抵达漳州府漳浦县“临漳驿”,即今天漳州漳浦县城绥安镇麦市街一带。对漳郡这几处驿站,前人多有吟咏。清人王有喜有《宿江东驿》诗:“江东驿里凭栏望,一片孤城一字桥。两岸垂杨渔棹聚,满江暮雨送寒潮。”
从“云霄驿”到“分水关”。从漳浦县“临漳驿”出发,越盘陀岭,总计行程70里,到漳州府云霄厅“云霄驿”,就在今天漳州云霄县城云陵镇北门,即云平路、元光路一带。再西南行80里,至漳州府诏安县“南诏驿”,位于今天漳州诏安县城南诏镇东门一带。诏安县是一处让我惊讶的地方。虽然“南诏驿”和诏安古城墙大多不存,但诏安明代所建“文昌宫”(文庙)、城隍庙、关帝庙、诏安明清时期至少合计13座牌坊组成的“诏安牌坊群”,却基本保存至今。此外,诏安南部梅岭镇“悬钟守御千户所”、诏安北部客家乡镇官陂、秀篆、霞葛等地多座“前方后圆”或“四角抹圆”形土楼,也屹立不倒。自“南诏驿”南行140里,抵达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今广东潮州市饶平县)交界处的“分水关”,即今天漳州诏安县深桥镇樟朗村。闽粤官道福建段,至此结束。历史上的诏安分水关,居高临下,扼守闽、粤两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民风彪悍,明代郑燮《南诏道中书事诗(六首其二)》诗称:“行人半荷戈,杀气怒相逐。”分水关原有石关门,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诏安知县杨庆容在关门上题署“津南第一关”,但民国时期修建公路时已毁。幸好,分水关一侧纪念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牌坊“功覃闽粤、声震华夷坊”,依然矗立。还有一座“胜利亭”,亭中保留着一块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由民国诏安县长钟日兴撰写的《抗倭胜迹》碑,碑文云:“……今者敌降战息。回顾吾诏,前后抗战3次,皆有可歌可泣之功绩……军民奋勇,敢死一战,(将日寇)驱出此关,可谓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