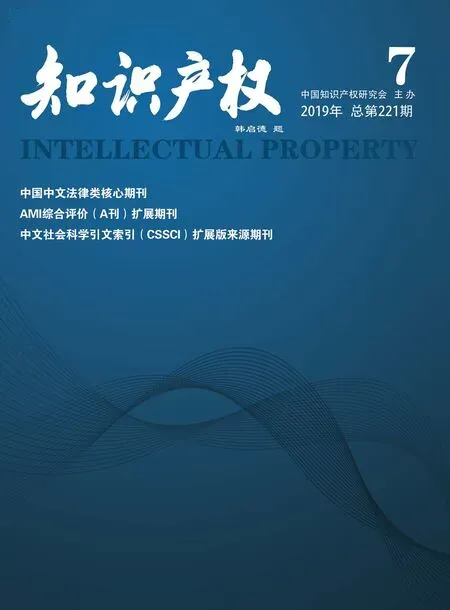认真对待商标权: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规制体系的修正
戴文骐
内容提要:《商标法》第13条、第15条与第32条后段共同组成了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规制体系,但其法律后果被区分为“不予注册”和“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从规则体系的内在规约性看,规制恶意抢注行为的各条规则的构成要件属于同类,应当关联相同的法律后果。从商标法对权利义务的恰当安排和有效治理恶意抢注的角度,应当明确权利与法益保护范式的区别,将法律后果统一为“不予注册”。制定法上,《商标法》第13条涉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可以保留“禁止使用”,但第15条第1款应当删除“并禁止使用”,改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请求权基础。
2019年4月23日公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为解决恶意商标注册问题颇费心思,于第4条新增“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这显然是为衔接同款上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提出注册申请的规定,并增加法律后果使之成为完全法条。①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援引原《商标法》第4 条的案件,一方面指出该条立法精神为防止商标囤积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根据该条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交存在使用意图的证据,也不能仅以申请人未实际使用商标为由驳回申请或撤销商标。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字第1459 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字第18 号行政判决书。恶意商标注册基本反映为恶意抢注与商标囤积两类现象。可以预期,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正在制定的《关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相配合,第4条新增条款能够有效约束商标囤积行为,但对恶意抢注则关注不足。与商标囤积行为相比,恶意抢注表现形式的复杂性及危害私人权益的紧迫程度均更胜一筹,这对法律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恶意抢注现象的长期存在,恰好说明有效法律规制的匮乏。因此有必要梳理和完善当前我国商标法中的恶意抢注规制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新修订《商标法》第4 条的不足
《商标法》第4条新增条款言及“恶意商标注册申请”,直观上与《欧盟商标条例》第59条第(1)款(b)项“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存在恶意的,应当在第三方提出申请后宣告无效”的规定有些类似。②考虑到《商标法》第4 条修改的目的之一是将规制恶意注册的关口前移至审查阶段,这实际上更加类似于《欧盟商标指令》第4 条第2 款的规定“商标注册申请基于恶意的……成员国可以规定不予注册”,但《欧盟商标指令》的规定是成员国可以而非必须转化为国内法的。但是,两条规定中“恶意”的含义截然不同。③实际上,欧盟知识产权局(内部市场协调局)曾经认为,不能仅以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没有真实使用意图而认为构成“恶意”(协调局撤销部第C000053447/1 号决定,转引自查尔斯·吉伦等编著:《简明欧洲商标与外观设计法》,李琛、赵湘乐、汪泽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187 页),这一点与《商标法》第4 条构成鲜明对比。标志性的Lindt 案(Case C-529/07 Chocoladefabriken Lindt &Sprüngli AG v Franz Hauswirth GmbH)指出,“申请注册没有使用意图”可以用来推定“注册申请仅为阻碍他人从事市场竞争”,而“阻碍他人竞争”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要素才能推定存在“恶意”。可见,单纯的“没有使用意图”与得出“不予注册”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与针对所有恶意注册行为的《欧盟商标条例》之规定相比,《商标法》新增条款只能涵盖商标囤积与一部分恶意抢注,无法全面规制恶意抢注行为。
首先,该新增条款订入《商标法》的位置,决定它必须衔接前文“生产经营的需要”而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这使得该条款所称“恶意”并非概括各类恶意注册现象的“恶意”要件,而是进一步限定“使用目的”以豁免一部分确实没有使用意图的“非恶意”注册。④《商标法》修正案草案原本无“恶意”要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商标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报告中表示,“已经取得商标注册并实际使用的企业为预防性目的申请商标注册,不宜一概予以驳回”,因此增加“恶意”要件。这类防御性注册可视为诚实经营的商标权人向公共权威购买的法律“保险”,用以降低商标授权确权与维权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此增加其主商标权利的安定性。这说明如果申请人确实存在使用目的,即使其使用是不正当的,也无法利用该新增条款予以规范。其次,该新增条款适用范围不足的实质在于不能兼顾商标囤积与恶意抢注行为特征的差异,使得恶意抢注行为与该条款的涵摄关系是偶联而非必然的。依据经营常识,商标囤积者不可能使用大量商标⑤参见宋健:《商标权滥用的司法规制》,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10 期,第34 页。,因此“不以使用为目的”要件足以涵摄现实中的囤积行为。但恶意抢注既包含“不以使用为目的”而意图不当阻拦或胁迫未注册商标所有者的情形⑥对于此类抢注行为,《商标法》第4条新增条款中的“恶意”要件对于推定主观恶信而言是多余的,因为恶意抢注之“恶意”已经得到第13条、第15 条、第32 条针对性的规定,辅助裁判者推定抢注恶意存在的要件反而是“不以使用为目的”,这是上述条款没有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包含“搭便车”攫取他人商誉、从而“以使用为目的”的情形,这已然超出了《商标法》第4条的适用范围。商标囤积近似于“广泛撒网”,而恶意抢注相当于“定点狙击”,虽然这两类恶意注册行为在现实中往往混合出现,但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应当根据其行为特征予以区分,以便建立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之间必然而非偶联的涵摄关系。
(二)区分商标抢注与恶意抢注
商标抢注之“抢”,指的是一种时间上的客观先后关系,即注册申请早于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时晚于未注册商标形成的时点。此时商标权取得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将独占性权利分配给 “先占有”未注册商标的主体,抑或 “先申请”商标注册的主体。商标法对抢注行为可能采取三种态度:其一,一概承认抢注的正当性,严格贯彻先申请原则;其二,一概不承认抢注的正当性,彻底保护未注册商标(如果将在先使用等同于“占有”,即为商标权使用取得模式);其三,部分承认抢注的正当性。商标权注册取得模式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前两种制度安排都不尽合理⑦在“纸上所有权”(paper)与“占有性所有权”(possession)之间无法作绝对化的制度安排,必须兼采二者。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9-30 页。,消除全部抢注行为的目的在注册取得模式下是非可欲的,可欲的是从中析出并遏制不正当的恶意抢注行为。
质言之,第一,一概承认抢注正当性将加剧权利寻租。在决定权利归属时,确定“先申请”事实的成本总体上低于回溯“先占有”的事实。立法者期望利用低成本的注册制来实现有名权利的高度安定性,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行为法保护模式相区别。⑧王太平:《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之限度——兼评“金庸诉江南”案》,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0期,第8页。然而,商标的财产价值并非来源于注册,这导致商标法在赋权阶段必然遭遇一个系统性困境:注册取得模式可能导向不公平的后果。绝对的先申请原则将加剧单纯追求纸面权利的寻租行为。第二,一概不承认抢注正当性将导致注册取得模式名存实亡。现代商标注册制下,商标抢注的发生基于三项基础:(1)由于注册自愿,存在大量被“先占”但未注册的商标⑨“先占”至少包括“在先使用”和“在先采纳”(常常表现为准备使用)两种类型。以往一般认为“在先使用是未注册商标权益存在的基础”(参见黄保勇:《论商标法对普通未注册商标的间接保护》,载《知识产权》2013 年第2 期,第60 页),但从恶意抢注规制的角度看,其规范目的在于惩罚恶意而非保护权益,不应否定某些场合下“在先采纳”可作为拒绝注册的理由,比如《商标法》第15 条。,这构成了抢注的事实基础;(2)注册模式在权利取得阶段不拒绝未实际使用的商标,构成抢注的制度基础;(3)一旦注册取得商标权,商标权人可方便地藉此提高他人参与市场竞争的成本,构成抢注的价值基础。因此,商标注册取得模式本身就是商标抢注现象的“制度本源”,将抢注行为违法性落足于“抢注”本身,将不可避免地与注册取得模式发生冲突。
因此,商标法必须在“商标抢注”之下,另设法律概念“恶意抢注”,以便在“占有”与“申请”之外寻求其他事实作为抢注正当性的判断依据。换言之,抢注的规制体系紧密关涉两个相互啮合的问题:抢注行为的正当性与未注册商标权益的保护范式,其“啮合点”,亦即决定抢注行为违法或合法的分界点,是“恶意”。
(三)恶意抢注法律后果的相互抵牾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包含“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⑩[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39 页;雷磊:《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82-83 页。,商标法在规制恶意抢注时,也应当区分为两步工作:抽象出恶意抢注的构成要件以求尽可能涵盖现实情境、为上述构成要件链接适当的法律后果。目前,针对恶意抢注规制规范的分析基本针对前者,包括界定抢注行为⑪参见钟鸣、陈锦川:《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10 期,第8-14 页;张鹏:《我国未注册商标效力的体系化解读》,载《法律科学》2016 年第5 期,第137-144 页;冯晓青:《〈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恶意抢注”认定研究——兼评“捕鱼达人”案》,载《武陵学刊》2017 年第5 期,第47-56 页;田晓玲、张玉敏:《商标抢注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治理》,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1 期,第27-32 页;王太平:《我国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 年第8 期,第135-150 页。、恶意的认定等问题⑫参见刘自钦:《商标权注册取得领域的客观诚信和恶信》,载《知识产权》2016 年第11 期,第67-73 页;苏志甫:《恶意抢注行为认定中抢注恶意的推定与排除》,载《中华商标》 2017 年第8 期,第41-45 页。,对法律后果的论述较少。⑬有学者提出应当增加返还标识和损害赔偿两种责任形式,参见田晓玲、张玉敏:《商标抢注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治理》,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1 期,第27-32 页。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判决赔偿因恶意抢注后提起侵权之诉,导致善意商标使用人交易失败所产生损失的案例,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 民初267 号民事判决书。但以上观点和案件大多从禁止权利滥用角度讨论不正当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未直接涉及目前《商标法》针对恶意抢注行为本身所规定的法律后果是否适当的问题。这种讨论状态重恶意抢注的事实构成——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相对忽略了在法律上应作出何种具体反应才是合适的,导致目前对恶意抢注规制规范的探讨并不完整。
当前我国商标法为规制恶意抢注的各条规则设置了两种法律后果⑭本文只考虑狭义恶意抢注未注册商标行为的法律治理,不考虑第32条前段规定对商业标识类权益以外的其他“在先权利”的侵害(参见钟鸣、陈锦川:《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10 期,第8 页)。实际上某些“在先权利”的客体也必须潜在具备商标符号功能才能被纳入《商标法》的保护,因此这些权利到底是基于自身的排他性,还是应当先被转化为“商品化权”才能发挥排斥恶意抢注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乔丹”案中的论证明显突破了民法上姓名权概念的外延,是以姓名权之名行保护商品化权之实。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27 号行政判决书。:(1)“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即《商标法》第13条抢注他人驰名商标、第15条第1款代理人或代表人恶意抢注;(2)单纯“不予注册”,包括第15条第2款其他特殊关系人恶意抢注、第32条后段恶意抢注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不予注册”和“禁止使用”为未注册商标所有人提供了提出两种积极主张的权利,为何要采取这一区分?直观来看,在上述规则用于解决同一问题的前提下,其法律后果存在区别,说明规则体系本身存在抵牾,除非构成要件的差异足以支撑这种区别。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质是逻辑或价值判断上的矛盾,将影响规则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将厘清“不予注册”与“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并存是否合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进行两重论证:(1)我国商标法规定的恶意抢注法律后果是否应当保持同一;(2)如果保持同一,应当选择哪一种法律后果来保证其适当性。
二、恶意抢注法律后果同一性的证成
本文认为,为了消除矛盾,我国商标法规制恶意抢注行为规定的法律后果应当具备同一性。证明以上观点需要考虑两个问题:规则体系下“法律后果”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到规制恶意抢注的规则体系时,确保法律后果同一性的理由。
(一)规则体系的内在规约性:同类事物相同对待
法律后果是对经过特征化、抽象化的某种事实集合(构成要件)作出的法律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和回应。⑮参见雷磊:《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82-83 页。“法律后果”指的是法律对于符合构成要件之事实的姿态,往往表现为行为义务的创设、变更、消灭(参见[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 页),但作为规则逻辑要件的法律后果不等于行为义务的具体承担。“命令式”的规范结构理论上能把任一后果与任一构成要件关联起来⑯参见[德]卡尔·恩吉施著:《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36 页。,但是,规则体系保证内在和谐的系统要求导致这种关联必然走向某种程度的规约性。⑰参见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510 页。这种规约性的表现之一是“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⑱[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258 页。这意味着对于应归于同类的若干构成要件而言,其法律后果必须是相同的⑲Henrique Jales Ribeiro,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Argument by Analogy, Argumentation Library 2014, vol.25, p. 49.,否则将引发规则体系的矛盾。首先,构成要件抽象化和一般化的本质,导致在检验规则体系规约性时应当以类型为基础。法是根据价值观念对生活事实的剪裁处理20李琛:《法的第二性原理与知识产权概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 年第1 期,第96 页。,而生活事实彼此之间必然体现为客观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结合21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著:《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9-120 页下文逻辑结构参考了陈景辉:《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0 年00 期,第173 页。Henrique Jales Ribeiro,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Argument by Analogy, Argumentation Library 2014, vol.25, p. 50. 陈景辉:《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0 年00 期,第180-181 页。莫如说文义实际是对这种“目的相关”的具体实现。,因此构成要件可以被看作去除了无关要素后的抽象化事实构成。这样,“同类事物”意味着存在客观差异的比较对象(事物)在规范意义上相同,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中“事物”指生活事实:若干生活事实经比较后归于“同类”,应当被等同评价,这种类比关涉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次中“事物”指构成要件:通过比较将若干事实集合归于“同类”,应当关联同一法律后果,这种类比关涉规则体系的内在和谐。
其次,类比过程存在可误性。进行构成要件类比的目的是厘清到底是差异特征还是相同特征,能够在保持规则体系内在和谐的要求下与法律后果关联起来。该过程容易出现无法准确扬弃特征的情况,结果导致原本应当关联不同后果的构成要件被归于同类,或者应当被归为同类的构成要件关联了不同后果。因此,需要完备的逻辑结构帮助完成论证,该论证以相关性为核心。22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著:《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9-120 页下文逻辑结构参考了陈景辉:《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0 年00 期,第173 页。Henrique Jales Ribeiro,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Argument by Analogy, Argumentation Library 2014, vol.25, p. 50. 陈景辉:《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0 年00 期,第180-181 页。莫如说文义实际是对这种“目的相关”的具体实现。
第一,从构成要件的文义中析出相同和差异特征作为类比的前提:(1)构成要件x和y都具备F、G等相同特征;(2)构成要件y(或者x)具备x(或者y)不具备的I、J等差异特征。
第二,单纯罗列相似或差异特征没有规范意义,还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命题:(3)I、J等差异特征在规范意义上没有压倒F、G等相同特征。
第三,此处“没有压倒”是指差异特征与法律后果不相关,同时构成要件x和y都因相同特征而与同一法律后果成功关联。“相关”指的是该特征令构成要件成为某一法律后果的前提条件。而哪种特征与法律后果相关联取决于规则目的而非文义。23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著:《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9-120 页下文逻辑结构参考了陈景辉:《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0 年00 期,第173 页。Henrique Jales Ribeiro,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Argument by Analogy, Argumentation Library 2014, vol.25, p. 50. 陈景辉:《规则的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构与正当化》,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0 年00 期,第180-181 页。莫如说文义实际是对这种“目的相关”的具体实现。因此,命题(3)的证立可以被进一步界定为:(3.1)根据规则目的,F、G等相同特征与某一法律后果相关;同时,(3.2)I、J等差异特征与某一法律后果不相关。24显然,此处相关与否是相对的,某一相似或差异特征在某规则体系中具备意义(相关),不表示在其他规则体系中同样如此。参见雷磊著:《类比法律论证——以德国学说为出发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59-261 页。 《商标法》第15 条第2 款的表述为“明知”,表面上不包括“应知”的“知晓”,但这只是法条表述的问题。参见冯术杰著:《商标注册条件若干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6 页。 根据2014 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及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3 号),“驰名”指的是“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这意味着抢注者必然处于明知或应知的主观状态下。
总而言之,若干构成要件是否可以被归于“同类”的论证步骤为:罗列相同和差异特征、确认规则目的、分别检验各个特征的相关性。
(二)恶意抢注构成要件的同类论证
利用上述逻辑结构分析商标法规制恶意抢注的规则体系,首先将构成要件的相同与差异特征罗列如下表1。

表1 恶意抢注构成要件相同与差异特征对比表
其次,明确该规则体系的目的。规范目的的作用是决定规范保护对象获得保护的可能性和限度28规范目的与规范保护对象不容混淆,否则容易导致过于重视规范保护对象的“重要性”而疏于考虑他人行为自由的不利后果。参见李波:《规范保护目的:概念解构与具体适用》,载《法学》2018 年第2 期,第29 页。,目的应当完整涵盖保护对象以发挥其拘束作用。抢注行为涉及抢注者和未注册商标所有者,但给予某些抢注行为不利法律后果的目的不是保护未注册商标权益,而是惩罚抢注恶意。二者的根本区别为:保护对象是“未注册商标权益”还是“商标权取得的正当秩序”。适用条件上的区别为:前者以在先使用为前提,后者以是否存在恶意为前提。通说认为,“未注册商标权益”的客体是商标使用后形成的商誉29参见冯术杰:《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与保护模式》,载《法学》2013 年第7 期,第40 页;孙山:《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的逻辑基础与规范设计》,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 年第2 期,第60-62 页;田晓玲、张玉敏:《商标抢注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治理》,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1 期,第28 页。,因此如果以“保护未注册商标权益”为目的,意味着必须将“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作为规制恶意抢注的前提。但是,显然这无法完全涵盖商标法有关恶意抢注的规定:《商标法》第15条第1款不要求在先使用30“不要求在先使用”当然意指,在第15 条第1 款适用的场景中,本人是否在先使用不具备法律意义,无需加以考虑。,第2款不要求形成商誉31对该条款的解释可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12.5 条,“……商标使用的规模、时间、知名度等因素不影响(第15 条第2 款)‘在先使用’的判断”。。若将该条款也纳入“未注册商标权益保护”的目的范围,将导致商标法场域内的“未注册商标权益”的构成要件在不同场景中伸缩不定32学者往往以“未注册商标权益的保护”为立法旨趣,合并讨论恶意抢注、在先使用抗辩、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标识的保护几个方面的问题(参见王太平:《我国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 年第8 期,第137-139 页)。但可获得保护的“未注册商标”是否以“在先使用并形成商誉”为要件则含糊不清:总体上强调商誉是保护的基础,在解释第15 条第1 款时转而强调基于特殊关系而非商誉来认定行为不正当性。,损害规则体系的统一性。如果转而将规则目的确立为“惩罚抢注恶意”,意味着以“商标权取得的正当秩序”作为保护对象,这与商标法保护正当竞争秩序的最终目的相吻合33《商标法》的多重目的(保护商标权、正当竞争秩序、消费者利益)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学者有不同意见。有认为三者为层层递进关系,保护商标专用权仅为手段,保障消费者利益才是统领性质的最根本目标(参见卢海君:《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标法(上)》,载《电子知识产权》2017 年第3 期,第25 页)。有认为“保护商标专用权”为重要目标,但对三者关系有分歧:或认为保护正当竞争秩序为终极目标,消费者利益被反射保护(参见王太平著:《商标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37 页);或认为正当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均为附带作用(参见刘铁光著:《商标法基本范畴的界定及其制度的体系化解释与改造》,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8-12 页)。对三者关系的不同认识发生了“手段与目的”的分裂,并成为决定商标法政策倾向性的关键:为了实现“目的”,必要时“手段”是可以被解释、代替甚至推翻的。但商标法的最终立法目的应是维护正当竞争秩序。商标是消费者与经营者联系的纽带,商标使用包含消费者识别来源和经营者指示来源两个维度,两类使用共同组成竞争秩序,割裂二者、只求其一是狭隘的偏见。正当秩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在商标权取得阶段体现为权利取得的正当秩序(同时反射性保护未注册商标),在商标权行使阶段体现为注册商标的保护。,并能完整涵盖各条规则。在围绕该目的确定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间的关联是否恰当时,能够正确地关注抢注者与被抢注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及其认定途径,以此甄别不同特征各自的规范意义。
再次,在上述目的下,如果能证明相同特征“知晓”即“恶意”,同时各差异特征不能独立地用于判断抢注行为违法性,就能证明各构成要件为“同类”。“知晓”即“恶意”降低了恶意认定的标准,当然有利于实现大力规制恶意抢注的政策目标。但是在政策之外,这种认定方式实际也是注册取得模式自我纠偏的应然要求。根据排中律,抢注时申请人要么不知晓,要么知晓他人商标已经存在。不知晓状态下进行的抢注行为为商标法所允许34张玉敏著:《商标注册与确权程序改革研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年版,第51 页。,而将知晓等同于恶意是为了适当提高商标权取得的代价,从而降低注册取得模式下的寻租风险。第一,恶意认定标准不宜过高,不宜递进式地区分规定“知晓”与“投机或妨碍竞争意图”。如前所述,规制恶意抢注的目的是维持“商标权取得”场景下的竞争秩序,即防止其中一方凭借注册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商标注册可看作申请人与公共权威之间的交易:商标权人获得的是以排他效力武装的“定价权力”,即有权决定他人通过使用商标的方式进入特定竞争领域时应当付出的成本,因此取得商标权意味着利用法定垄断终结自由竞争状态。申请人付出的代价过低但却从这种交易中获得过高回报,这一情况本身即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极易引发纯粹追求法定垄断的寻租行为。因此,在先申请原则下必须引入有条件的“先占有规则”来抵消寻租行为对整体竞争环境的不利影响。35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21 页、第219-221 页。这种抵消作用毋宁说是通过将商标“先占”者拉入上述“申请人—公共权威”交易之中的方式提高申请人获得定价权的代价。因此,能合理预期他人“先占”的情况下仍然提出注册申请,本身就破坏了交易公平状态。第二,“先占”认定标准不宜过高。偏向于“先占有规则”的使用取得模式通过将“先占”等同于在先使用的方式降低“先占”的证明成本,这种认定标准以其符合商标价值逻辑的一面加强了说服力。36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20 页。而在偏向“先申请原则”的注册制下,“先占”的制度功能是在具体的“申请注册”行为所圈定的场景下阻碍抢注者获权,是对注册取得模式的纠偏,而非单独设置商标权取得条件,因此无需特地降低“先占”证明成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商标注册成本,合理避让被先占的商标。而避让的原因和限度取决于先占者与抢注者的内部关系,亦即“知晓”。这样,除非能够证明他人“先占”状态消失,如得到授权或他人明确放弃了商标37通过证明商标所有人放弃商标满足抢注正当性要求的观点,参见[奥]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段瑞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85 页。,否则无论由哪种渠道(他人在先使用产生的影响或特殊关系)知晓他人已经先占商标,申请人的抢注行为都不再具备正当性,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最后,根据规则目的,上述各条款的差异特征均不具备直接、单独成立的相关性。第一,被抢注商标商誉度量的差异不具有独立的规范性意义。38“商誉”应当是一个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的中性概念:相关公众知晓的标识与来源之间的联系能力、相关公众对标识指示的特定来源商品或服务的评价,前者“知晓”的范围即“影响力”的边界。参见冯晓青:《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恶意抢注”认定研究——兼评“捕鱼达人”案》,载《武陵学刊》2017 年9 月,第51 页;熊文聪:《论商标法中的“非法使用”与“一定影响”——“捕鱼达人”案引发的思考》,载《中华商标》2017 年第3 期,第85 页。其中,《商标法》第15条几乎不考虑商誉的度量,而是以法律或事实上的特殊关系作为恶意认定的基础。第32条后段中的“一定影响”,本身是指通过实际使用商标令其在相关行业或一定地域内凝结相当量的商誉;但其法律意义必须结合“不正当手段”才得揭示:根据商标使用所造成的“影响力”推定注册者已经知晓其存在。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 号)第23 条;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 条。这种两个构成要件要素相互限定的规定方式,有些类似于《欧盟商标条例》(EUTMR)第8 条第4 项规定中“不仅具有区域性意义(more than mere local significance)”的解释,参见Case C-96/09 P。第13条则将驰名作为推定抢注者是否知晓在先商标存在的事由,这在事实上杜绝了“善意抢注”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可能性。40参见钟鸣、陈锦川:《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10 期,第11 页。因此,表面上似乎依照商誉的大小体现为“第15条(无商誉要求或少量商誉)——第32条后段(‘一定影响’)——第13条(驰名)”的梯度规定方式,只是为了揭示不同情境下“知晓”的认定渠道,实际为主观恶意客观化的不同方式:“第15条(借助特殊关系认定知晓)——第32条(不存在特殊关系也未驰名的情况下借助商标在先使用的影响范围认定知晓)——第13条(借助商标全国知名的事实认定知晓)。”
第二,是否“跨类”(不相同或近似)不影响恶意抢注违法性的判断。41有观点认为应区分为“一般驰名商标”与“高度驰名商标”,前者给予防止“跨类混淆”的特殊保护,后者给予反淡化保护。参见祝建军:《驰名商标跨类别保护应受到限制——两则案例引发的思考》,载《知识产权》2011 年第10 期,第52 页。实际上所谓上述“跨类混淆”中的“类”指的应当是《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类表》中为方便商标行政管理而预先进行的形式分类,这与根据动态实时的市场运行状况而判断是否构成混淆的实质分类在法律意义、认定标准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类表》为了协调与实质分类的关系也大量列举“跨类混淆”)。对这种形式“跨类”更准确的称谓应当是“关联混淆”,普通注册商标也能享受这一保护,无须归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第13条第3款包含“跨类”特征而与其他条款形成显著差异,但这一差异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相关性特征。针对普通商标,通过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混淆,即足以实现公平竞争秩序,因此不能“跨类”认定抢注违法性。但对驰名商标而言,商标符号结构和功能发生了质变42Barton Beebe, 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rademark Law, UCLA Law Review, Vol. 51, Issue 3 (February 2004), p. 693.,公平竞争秩序的实现不能再局限于反混淆保护。在行为结果要素(“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限定下,43参见刘维:《我国注册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的理论反思——以2009 年以来的35 份裁判文书为样本》,载《知识产权》2015 年第9 期,第23-24 页。可以“跨类”认定抢注违法。这说明“跨类”与“不跨类”可以沿着不同的路径在相同规则目的下获得统一,因此,不能认为这一差异具有规范意义。
第三,被抢注人是否在先使用的差异不影响恶意抢注违法性的判断。有观点认为,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注意义务大于“其他关系”人,抢注恶性更加明显,因此必须在第15条第2款增加“在先使用”要求进行平衡。44冯术杰著:《商标注册条件若干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6 页。这一观点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应当消除这一差异特征才能贯彻遏制恶意抢注的规则目的。一方面,上述观点为了解释为何唯独代理人或代表人抢注不以被抢注者“在先使用”为前提,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代理关系的特殊性,导致差异特征的规范意义被不当夸大。实际上两个条款的目的均为指明某种恶意认定渠道,具备规范意义的是恶意的有无而非高低。45从裁判规则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 号)第16 条列举的“亲属关系”“营业地址邻近”等具体“其他关系”直接说明抢注者的注意义务是帮助裁判者得出“明知”他人商标在先使用结论的理由,只对结论认定的难易程度有影响,但不影响结论本身的法律意义(严格来说“营业地址邻近”不属于特殊关系,不适合作为《商标法》第15 条第2 款涵盖的事例,应当归入《商标法》第32 条后段)。退一步说,如果代理或代表关系根本无涉本人的商标,也无法从中推定代理人或代表人的知晓状态,该条款就没有适用余地。46《商标审查和审理标准》言及,“……代理、代表关系尚在磋商阶段,代理人、代表人知悉被代理人、被代表人商标后进行注册……”。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法》第15 条第1 款的适用也必须检验本人出示的证据是否包含涉案商标,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提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44 号行政判决书。这说明代理或代表关系本身不是恶意抢注的规制基础。另一方面,既然第15条第1款和第2款用以判断抢注违法性的特征没有规范性差异,自然也没有必要以“在先使用”平衡两个条款。因为这类情形是以“特殊关系”而非未注册商标的影响力范围作为认定渠道,与商标是否使用无关。两款分列两个子类型更多的作用是尽可能清晰列举“特殊关系”的具体态样以方便裁判者正确适用法律。
总的来说,上述各条规则的目的是排除恶意的抢注,其他的差异特征仅体现出“恶意”认定渠道上的差别,可谓殊途同归,并没有令各条款的构成要件在规则体系中占据不同地位。因此,该规则体系的构成要件应当被判定为“同类”,并关联相同的法律后果。
三、恶意抢注法律后果的修正及其证成
恶意抢注治理规则的核心是将“恶意”作为抢注行为违法性的判准并导向不利法律后果。尽管表面上“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更有利于保护未注册商标权益,但法律后果应当统一为“不予注册”。下文将从两个方面论证该观点:商标法理论如何调和未注册商标权益与注册取得模式;制定法上如何处理当前采取“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法律后果的《商标法》第13条第2款、第3款与第15条第1款。
(一)商标法上未注册商标权益保护的应有姿态
商标法在处理注册商标权与未注册商标权益时应当具备不同姿态。前文已述及区分商标抢注与恶意抢注的制度意义,换言之,与注册取得模式伴生的先申请原则本身是鼓励抢注的47参见钟鸣、陈锦川:《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10 期,第8 页。,这与注册制的功能有关。前现代与现代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其基本理念从“创造”到“对象”的系统转向。这种转向的特征在于,法律不再建立在对创造性劳动过程的田园牧歌式的描摹之上,而是集中在“作为一个闭合和可靠实体”的保护对象的经济价值和社会贡献之上,因而可以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知识产品的合理分配。4知识产品也不再仅仅是一种难以厘清排他边界和明确支配的自然事实,而是可被纳入现代权利框架的制度性事实。为了构建这种条理清晰、范围明确的权利框架,注册、登记等具有潜在自组织性的制度工具应运而生。通过注册程序,法律得以尽量清晰地划定权利的边界。通过鼓励“抢先提出注册”,商标法实际上意欲将未注册商标“驱赶”向能够确保权利安定性和交易安全的注册状态。49参见[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著:《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英国的历程(1760-1911)》,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6-210 页。因此,尽管脱胎于反假冒制度的商标保护贯穿未注册商标和注册商标,并且以商誉作为协调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抓手50Bone, Robert G., Hunting Goodwill: 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Goodwill in Trademark Law,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86, no. 3(June 2006):pp. 572-575,但是,优先保护注册商标是商标法的应有姿态。这种姿态的实现需要如下保障。
首先,在商标法的场域内,以“注册与否”来区别权利义务的安排模式,除非符合严苛的例外条件,只有注册商标权利人享有禁止使用请求权。商标法通过注册行为构建了封闭的有名权利,并预先规定了该权利的取得条件和保护范围,从而显著降低了界权成本。质言之,注册取得制是将个人“占有”商标并获取排他权利的意志,以成本较低的方式与他人意志相协调的结果。由于本质上相互平等的个人意志与这种意志的彼此协调共同构成了权利取得的整体条件,从而导致寻找外在事物对他人的重要性皆为一律的统一评价51参见朱庆育:《权利的非伦理性化:客观权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载《比较法研究》2001 年第3 期,第18 页。——亦即就自己获得排他性权利之事实取得他人“同意”这一取得权利的过程无法单纯依据个人的主张来完成。在商标法的情境下,这种整体条件的理想状态就表现为商标权取得的递进式条件:(1)个人通过中立性劳动(使用商标)创造商标符号并主张权利;(2)对中立性劳动进行理性批判以确定权利。很明显,从规范角度看满足该条件的关键在于第二步。因此,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其一,注册制将部分证明成本转嫁给注册机关52包括商标符号本身的合法性——体现为绝对禁止注册事由,以及商标权利的合规范性——体现为相对禁止注册事由。,并利用公示制度构建商标权利信息平台,令个人更容易地完成获权意思表达的宏观建构,以协调他人的平等意志。因此,一旦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获得同等保护,即无法实现《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其二,上述成本转移方式以劳动与劳动之理性批判的相对分离作为前提。53注册机关事实上假定利害关系人(在先使用者)最关心商标权利合规范性之检验,于是进一步将提出反对意见的成本转移给不同意注册者获权主张的人,通过程序分流(受理根据相对禁止注册事由提起的异议、撤销和无效宣告请求,而不是一概主动审查)降低注册机关的审查成本。注册制度只是一种框架假定:商标申请人最终会通过使用行为创造商标符号意义,并实现商标功能。继而对劳动之理性的审查就成为预先推定,而非对既存中立性劳动的事后检验。因此,注册制度必须促使“理性”与“劳动”重新吻合在一起。措施之一即反对恶意抢注54另一重大措施即为注册取得模式必须伴随的“使用强制”要求。从弥合注册与使用要求的总体视角看,授权确权阶段对恶意抢注的排除可谓“前封”,使用强制要求可谓“后攻”。:如果商标权人的初始目的就是利用这种理性与劳动相对分离的状态——知晓他人未注册商标存在,仍然抢先要求确定权利,则必须赋予其不利法律后果。将该措施的直接目的坐落在对抢注行为违法性的消极评价或是积极保护未注册商标权益,即为上述商标法的姿态问题。显然,商标法求取权利的安定性,依靠的是前者而非后者,采取这一姿态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未注册商标没有经过获权意义上对商标使用行为的理性批判。因此,商标法受该直接目的所指引,只能通过提供“不予注册”请求权的方式间接、有限地保护未注册商标。
其次,应当认真对待注册商标权,留下一部“干净”的《商标法》。质言之,商标法在设定权利义务时必须“厌恶”未注册商标。部分未注册商标因凝结商誉而具备财产价值,但商标法不应将其视同注册商标。第一,整部《商标法》应当围绕商标财产权利的取得、维持、行使和消灭展开,打开该场域的钥匙即为商标注册。因此,作为财产法的商标法一般只能以拒绝他人恶意抢注的方式间接保护未注册商标权益。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未注册商标权益本质上不是财产权。从财产权的理论构架上看,学者将对象与权利的关系化约为“财产体”与“财产权”,通过这种区分,财产权制度具备特殊的形式价值。然而,二者相对分离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作为处分对象的财产体的内容和范围是确定的,以及存在占有之外财产权变动的表征方式。55参见冉昊:《制定法对财产权的影响》,载《现代法学》2004 年第5 期,第11-12 页。因此,注册而非使用帮助完成了商标符号的从共有到私有,这与前文所述“劳动的理性批判”同义。而未注册商标未能完成这一特定化和公示过程。继而,从法律关系的形式上看,商标法原则上只能为注册商标设定禁止使用请求权。反过来说,在该法的视野中,未注册商标仍然处于共有状态,亦即“向所有人敞开胸怀,任何人都有权使用”。56当然这并不妨碍其他法律提供禁止权。第二,更新认识商誉要素在商标法中的地位。一方面,商标法只能通过商标权间接保护商誉,而非越过该权利确定过程直接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商标法应当通过“使用强制”确保商标权利框架被商誉所填充,防止出现“僵尸权利”或“标识财产权”。因此对商标法而言,形成商誉是法定义务,而不是请求权基础。57对于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商誉是请求权基础,这是因为商誉积累使得商标功能发生质变。
总而言之,商标法的具体条款如果不加区分地平等保护未注册与注册商标,是对该法基本价值取向的盲目和恣意,严重背离了预先划定商标权利边界的制度设计。
(二)第13 条第2 款、第3 款: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合并规定
我国《商标法》第13条第2、3款规定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实际合并了两个法律规则:第一,通过“不予注册”在权利取得阶段为注册制设置唯一的使用取得例外;第二,通过“禁止使用”在权利行使阶段特殊保护驰名商标。该条款实际可以分解为“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以及“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禁止使用”。
我国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权利取得与权利行使安置在同一条款中。根据《商标法》的章节安排,第13条处于“总则”,其前后条文均为商标注册条件;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一章中并无对驰名商标保护的任何规定。但从驰名商标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明显将《商标法》第13条同时作为授权确权和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5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 号)第2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3 号)第2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12 号)第11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 号)第12 条、第13 条。这与《欧盟商标条例》及德国、日本、美国等国清晰区分商标权利取得与权利行使两大部分内容的规定方式大相径庭。这种略显怪异的规定方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商标法有关权利行使的规范被封闭在“注册商标权”内;另一方面,考察我国商标法律的立法史可以发现,2001年《商标法》第二次修订时加入了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只不过该法第13条转化国际公约的痕迹非常明显,第1款显然来自《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第2款则来自《TRIPS协议》第16条第3款。于是国际公约中不区分权利取得和权利行使,而是统一要求成员国国内法提供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特点也一并继承下来。这既说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必须依靠权利取得阶段的“不予注册”以及权利行使阶段的“禁止使用”才能被完整实现,也意味着两种规则的构成要件存在可通约之处。这样一来,将不同目的的规则予以合并规定在立法技术上不存在大的障碍。
但是,驰名商标因其商誉度量受到特殊保护,并不表示必须利用禁止权保护其他类型的未注册商标。在注册模式下,一国商标法承认不通过申请注册获得禁止权是一种例外。为了确保规约性,这种“例外”不能超出原本法律规范体系自身弹性和解释力的最大射程——也就是说,必须提取某种根植于“申请在先”原则内部的因由来完成“原则”与“例外”之间的和谐共处。由于注册制度的公示作用,对于注册商标而言,裁判者得以推定一个法域内的其他所有人都接触了该商标符号。因此,当且仅当商标达到驰名的程度,即使商标未注册也能够在全国范围阻却在后申请的商标注册。59有观点认为,由于驰名商标数量少,所以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享有禁止权不会对注册制度造成过大冲击。实际上,驰名商标数量少的原因在于满足“驰名”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的难度很高,为规则的例外设置较高的前提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不正确地扩大驰名商标认定才会冲击商标注册制度。这种保护方式相当于豁免了取得商标权必经的注册程序60参见王太平:《论驰名商标认定的公众范围标准》,载《法学》2014 年第10 期,第59 页。因此,驰名商标上建立的是绝对性权利,据此成立的禁止使用请求权是典型的原权请求权,符合商标法请求权体系的要求。,令第13条第2款、第3款在权利取得规范意义上等效于第30条。这是注册取得模式下罕见的近似于“使用取得”商标权的情形61参见冯晓青:《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及其制度完善》,载《法学家》2012 年第4 期,第124 页。,与《巴黎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也保持一致。62《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 条之二的目的之一是协调两种商标权取得模式,避免注册和使用易于与在该注册与使用国已经驰名的另一商标相混淆的商标,尽管该驰名商标因未注册而在该国未得到或尚未得到保护。参见[奥]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段瑞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60 页。
(三)第15 条第1 款:公约义务的适当履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针对该条款的权威释义明言,63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2013 年修改)》,载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minshang/2013-12/24/content_18199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5 月20 日。当前《商标法》第15条第1款采用“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法律后果是为了履行《巴黎公约》义务。64《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 条之七规定,(1)如果本联盟一个国家的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该所有人授权而以自己名义向本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申请该项商标的注册,该所有人有权反对所申请的注册或要求取消注册,或者,如该国法律允许,该所有人可以要求将该项注册转让给自己,除非该代理人或代表人能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2)商标所有人如未授权使用,在符合上述第(1)款规定的前提下,有权反对其代理人或代表人使用其商标。(3)各国立法可以规定商标所有人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合理期限。原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也指出,2001年《商标法》修订时增加该条款是为了“履行公约义务”。65参见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编著:《商标法理解与适用》,中国工商出版社2015 年版,第48 页。然而,“履行《巴黎公约》义务”并不意味着必须将其分别列明的各项请求权一概转化为商标法中的规定。66从该条款的文字表述看,显然利用区分第(一)项、第(二)项的方式作了最低限度的区分:第(一)项包含不予注册和强制转让,针对的是授权确权,“禁止使用”在第(二)项单独规定。事实上,该条款中“禁止使用”基本没有被实际适用,67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进行检索,与《商标法》第15 条有关的案件共计236 宗,其中39 宗的裁判实际适用了第15 条第1 款(或2001 年《商标法》第15 条),没有任何一宗案件判决“禁止使用”。这本身即说明该条款中“禁止使用”后果如同商标法“阑尾”一般的尴尬地位。
前文讨论《商标法》第13条时提出,存在合并规定权利取得与权利保护规则的可能,这正是《巴黎公约》规定的方式。68《巴黎公约》第6 条之七第(一)项规定的反对注册与第(二)项规定的反对使用相互独立,参见[奥]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段瑞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85 页。但公约没有要求仅通过商标法履行全部公约义务,相反,取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协调正是公约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69参见冯术杰:《知识产权条约视角下新型竞争行为的规制》,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12 期,第4 页。将公约的相关规定转化为国内法是国际公约成员国俱应承担的义务,《巴黎公约》其他成员国通过两种方式完成该转化。第一,转化为商标法规定,以《德国商标和其他标识法》及《欧盟商标条例》为典型。前者第11条规定“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以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名义注册商标的,得撤销该商标注册”;第17条第2款则为本人提供了禁止权。后者第8条第3款和第13条采取了类似的规定方式。第二,转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以《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典型。《日本商标法》本身没有单独列举代理人或代表人恶意抢注的情形70可以考虑适用《日本商标法》第4 条第1 款第(十五)项“与他人业务所述商品或服务产生混淆之虞的商标”,其法律后果仅为“不能获得商标注册”。参见森智香子、广濑文彦、森康晃著:《日本商标法实务》,北京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年版,第48 页。,《巴黎公约》中“禁止使用”规定的转化实际是利用《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第(十五)项列明的构成要件和第3条提供的差止请求权。71具体法条参见https://wipolex.wipo.int/zh/text/182395,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5 月20 日。前一种立法例中,《德国商标法》实际包容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商业标识保护的规定,这种立法方式力图造就统一封闭的标识法,以便清晰切割两部法律之间的囫囵关系。72参见[德]安斯加尔·奥利著:《德国商标法导读》,载《德国商标法》,范长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版,第9 页;郑成思:《浅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交叉与重叠》,载《知识产权》1998 年第4 期,第7 页。而《欧盟商标条例》第11条提供的“禁止使用”应当援引第8条第3款的规定,该款规定中的商标“在欧盟范围内不享有任何保护。”73否则依据欧盟注册、成员国注册或成员国驰名推定抢注恶意(《欧盟商标条例》第8 条第2 款)。参见查尔斯·吉伦等编辑:《简明欧洲商标与外观设计法》,李琛、赵湘乐、汪泽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69 页。EUIPO Trademark Guidelines Part C Section3.1, at https://euipodev01.sdlproducts.com/trade-mark-guidelines/en/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19-05-20.这说明《欧盟商标条例》第13条的规定不以商标权利为基础,这并非《商标法》提供请求权基础的适当逻辑,更接近于通过认定本人“先占”的商标被代理人或代表人“盗取”这一行为的不正当性而禁止后续使用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逻辑。74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欧盟商标条例》和《德国商标法》为被代理人、被代表人提供禁止使用请求权的条款均位于“权利的保护”部分(《欧盟商标条例》第13 条属于该法第二章“欧盟商标权的效力”,《德国商标法》第17 条属于该法第三章“保护的内容、权利侵害”)。换言之,这一请求权基础对应的是一种援引代理人、代表人恶意抢注规定作为构成要件的侵权之诉,无论如何不是授权确权相关规定。但我国商标法难以作出类似规定,原因一是《欧盟商标条例》承担协调成员国商标与联盟商标权的任务,《德国商标法》是包含反不正当竞争规范的广义标识法,这与我国商标法调整对象存在较大差异;二是商标法的权利保护被限定在“注册商标权”范围内,除“驰名”外不应当过多规定权利取得的例外方式,否则将动摇注册制度。以上立法例说明,一国商标法并非承担公约义务的唯一途径,视乎该国部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决定《巴黎公约》第6条之七的具体转化方式是较好的选择。
论证只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设立上述禁止权,需要以下几块“拼图”: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保护的充分性;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保护的合理性,且商标法反之;特定情形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未经使用的商标提供保护的正当性。
首先,与商标法保护注册商标类似,反法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足够充分。《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前,第5条规定中“商品名称、包装、装潢”扩大解释为未注册商标,“知名”与“特有”与商标显著性同义,并通过制止混淆来保护商誉。75参见王太平:《我国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法律保护制度之完善——基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项的分析》,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180-187 页;姚鹤徽:《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制度辩证与完善——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载《法律科学》2016 年第3 期,第126-134 页;张伟君:《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条款的修改和完善》,载《知识产权》2017 年第6 期,第22-23 页。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欧盟商标条例》和《德国商标法》为被代理人、被代表人提供禁止使用请求权的条款均位于“权利的保护”部分(《欧盟商标条例》第13 条属于该法第二章“欧盟商标权的效力”,《德国商标法》第17 条属于该法第三章“保护的内容、权利侵害”)。换言之,这一请求权基础对应的是一种援引代理人、代表人恶意抢注规定作为构成要件的侵权之诉,无论如何不是授权确权相关规定。但我国商标法难以作出类似规定,原因一是《欧盟商标条例》承担协调成员国商标与联盟商标权的任务,《德国商标法》是包含反不正当竞争规范的广义标识法,这与我国商标法调整对象存在较大差异;二是商标法的权利保护被限定在“注册商标权”范围内,除“驰名”外不应当过多规定权利取得的例外方式,否则将动摇注册制度。该法修改后第6条明确了商业标识保护的范围,“有一定影响”也与商标法中的类似概念相互衔接。76参见刘丽娟:《确立反假冒为商标保护的第二支柱——〈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 条之目的解析》,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2 期,第56-66 页;王太平、袁振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商业标识保护制度之评析》,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5 期,第3-14 页。另外,两部法律的规范目的有重合之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正当地吸引消费者的行为”,典型如仿冒商标和虚假标识等行为因导致消费者误信而被认定为不正当。77李友根:《论消费者在不正当竞争判断中的作用——基于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案的整理与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第51 页。而商标法的直接目标是保护注册商标权,根本目标则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但两目的应当以何者为优先则争论不休,故而产生规范的二重面向。谢克特指出:“法院须解决一个问题:在(商标权救济)案件中,真正的基础是公众被欺诈导致的损害,还是对商标所有人造成的损害”。78Frank I. Schechter,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Law Relating to Tradema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p. 5.于是,在商标权概念形成前,商标所有人假道“消费者保护”的目标求取“禁止使用”的正当性。79参见卢海君:《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标法(下)》,载《电子知识产权》2017 年第4 期,第4-5 页。但是,注册制建立后如果仍然拘泥于总体目的的重合,任由商标私益与消费者利益在事实层面的相互粘连影响具体权利义务,显然会影响规范的安定性和行为的可预见性。
其次,设权模式和行为法模式在基本范式和规范供给范围上的差异决定了只能将非驰名未注册商标所有人的禁止权设置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其根本原因在于未经注册或驰名的商标权益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因此其权利归属效能无法彰显,自然也不应当赋予其强大的排除效能。这意味着在保护未注册商标权益时无法从侵害结果直接“征引”出违法性,而必须考察行为本身是否违法80有关权利的“归属效能”“排除效能”与“社会典型公开性”之间的关系,参见于飞:《论德国侵权法中的“框架权”》,载《比较法研究》2012 年第2 期,第69-76 页。,也就是两类模式的分水岭。质言之,从正面看,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存在“合法权利”“正当竞争利益”和“法律放任的自由竞争”三个领域,三者内蕴的法秩序有所不同,靠前领域相较靠后领域,法律规范的介入更加积极。第一,合法权利对应设权模式:利益不再保持中性,破坏其完满状态的行为必然不正当,因此,法律救济的前提是证立被请求保护的利益符合法律预先设定的权利构成要件。第二,正当竞争利益对应行为法模式:保持利益中性,其立足点不是预先规定的静态权利,而在明确行为不正当性的基础上主张“禁止使用”。81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范式》,载《法学家》2018 年第1 期,第57-58 页。第三,尽管自由竞争行为必然附带对其他市场主体的损害,却不能获得法律救济。可以看到,两种保护模式俱因涉及正当性批判而在原始意义上有同源的可能,但是二者批判对象不同:一为静态利益,一为动态行为。显然,理想中商标权的实质是经过针对商誉的正当性批判后成立的合法权利,其最终目标是合法利益的正确归属。82这只是理想中的完整商标权,前文已经述及商标法必须通过使用强制要求促成理想商标权的实现,此时完成了“保护商标权人”“保护消费者利益”“确保市场竞争秩序”三个立法目的的融合。而未注册商标利益是中性的,对其造成的损害并不必然具有可救济性,能否主张“禁止使用”,以针对使用行为的正当性批判为前提。从反面看,未注册商标上成立的禁止使用请求权不能以所谓有限的“相对权保护”为由而设置在商标法中。有观点认为,为了防止对注册制产生冲击,《商标法》第15条第1款的禁止权是囿于特殊关系的债权性“相对权”保护,以此证明该禁止权的合理性。83王太平:《我国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 年第8 期,第145 页。这种观点的含混之处在于既希望证立代理或代表关系的特殊性应当关联更加严苛的法律后果(禁止使用),又希望消弭这种“相对性禁止权”对注册制的冲击。然而,这种“两头讨好”的意图实则难以成立。由于请求权必然针对特定人,这里的“相对性”指的不是禁止使用请求权本身的相对性。因此该观点的实质是商标法同时基于两种关系提供“禁止使用”请求权:特定主体之间的相对关系、标的(商标权)与主体之间的归属关系,84两类关系参见[德]梅迪库斯著:《请求权基础》,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19 页以下。前者是债权性的本权请求权,后者是基于类物权的原权请求权。85各类请求权的区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论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及其内部关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年第4 期,第56-66 页。但是,商标法无法容纳前者。如前所述,在商标法秉持的设权模式下,提出特定请求的前提是判断某项事实是否符合预先设定的权利之定义,该判断过程体现为商标权的取得。除非承认所谓“未注册商标权”,否则只能依行为法模式从行为不正当的角度提出禁止使用请求。因此,所谓“相对性禁止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注册制的抵触,违背了商标法请求权体系的基础逻辑,并不会因其数量稀少或针对特定人而具备合理色彩。
最后,须强调上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标识相关竞争秩序的保护范式不以商誉的存在为必要。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对的是利用不正当手段破坏标识与其指代对象之间特定对应性的行为。这种特定对应性的总和即以商标为体现的竞争秩序,可以是已经形成的,典型如商誉;也可以是通过合意即将形成的,比如代理或代表关系。86典型如“雷博公司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家园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3 号行政判决书。该案审理意见表明,虽然未注册商标所有人没有使用商标,但鉴于抢注者和所有人之间预先达成的合意,抢注者理应认识并同意涉案商标归属于所有人,因此其抢注行为不正当。该理由同样适用于要求禁止使用的场合。即使本人还未使用商标(只是为使用商标做准备),如果代表人或代理人使用行为不正当,仍然有权禁止其使用。87代理人或代表人行为的不正当性不取决于代理或代表关系本身,而取决于其使用行为是否违背其与商标所有人间在先达成的关于商标使用的合意。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巴黎公约》第6 条之七的解释可以适当放宽代理或代表关系的解释范围,不以与商标使用有关的明示授权为必要条件,并将商品批发商、授权经销商等也纳入其中。参见[奥]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段瑞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5 页。另外,在授权确权案件中,如果代理或代表关系与涉案商标无关,严格来说应当适用《商标法》第15 条第2 款驳回注册申请。这似乎与反法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不相协调,因为没有产生商誉的情况下不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而最初依靠仿冒之诉实现商标保护的深层理由是“商誉始于商标所有人的使用、终于消费者的认知记忆”这一事实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在法律层面紧密联系起来。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历时性的层面达成“维护竞争秩序”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目的的相互统一,在纠纷发生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关注的重点应当是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而非消费者利益当时是否受损。竞争行为的目的均为争夺消费者和交易机会,只是部分行为因违背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而被判断为不正当。因此这些行为的结果短期内既可能不利于竞争者但有利于消费者88比如“腾讯诉世界之窗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的一审和二审均承认浏览器屏蔽视频网站广告短期内有利于消费者。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 民初70786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 民终558 号民事判决书。,也可能无关竞争者但不利于消费者89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5)朝民初字第3251 号民事判决书;谢晓尧著:《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 页。,自然也可能不利于竞争者但无关消费者。出现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受损害是竞争行为正当性批判的非充分非必要条件90参见焦海涛:《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1 期,第165-166 页。,二者只是在部分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时恰好重合。换言之,即使未注册商标已经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所谓“一定影响”的商誉,由于缺乏商标权的框定,这种利益仍然是中性的。这使得“禁止使用”立足于使用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之上。91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范式》,载《法学家》2018 年第1 期,第59 页。因此,结合“使用”和“注册”这两种法律应当关注的行为,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未注册商标权益的保护可以区分为多个层次:(1)存在抢注行为时,由商标法规定“不予注册”并根据抢注恶意认定渠道的区别划分子类型;(2)不论是否存在抢注行为,使用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如果双方均存在使用行为,损害的是以商誉为表现的竞争秩序,当存在仿冒、诋毁等不正当行为时应“禁止使用”;如果请求保护者自身还没有使用行为,仍然应围绕对方使用行为是否不正当决定应否“禁止使用”,商标的来源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应当成为重要的判断因素。92法律上的诚信和商业道德作为权利边界的约束,应当区别于日常生活语言中的诚信和道德。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推论:在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如果商标所有人没有通过自己的使用在中国境内建立起以商誉为表征的竞争秩序,那么只有当被告使用商标的行为违背了事先与所有人达成的关于涉案商标如何使用的合意时,所有人才能反对被告的使用(类似禁反言)。换言之,商标法上恶意抢注规制规则涵盖的“不予注册”事实情形必然大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应当“禁止使用”的事实情形:《商标法》第15 条第2 款指涉的许多情况如果不包含上述“合意”,不能作为反法禁止使用请求权的事实基础;即使存在第1 款中的代理或代表关系,如果涉案商标与代理或代表合意无关,也不能要求代理人或代表人禁止使用,否则将过度侵犯他人的竞争自由。
余论:恶意抢注法律治理的两个面向
恶意抢注法律规制之铃须向注册制这一“系铃人”求解。前文总结了商标抢注与注册制直接相关的事实、制度和价值基础,遏制恶意抢注行为应当从事实和价值两个方面着手,亦即规制恶意抢注行为的两个可能面向。本文所讨论的正是面向之一:在授权确权的场合针对抢注行为本身,以削减商标抢注的事实基础为导向。由于自愿注册原则,无法也不应当谋求彻底消除未注册商标,因此通过法律规范的指引减少未注册商标的数量就成为“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93“减少未注册商标的数量”不等价于“增加注册商标的数量”,前者激励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及时申请注册,后者则可能导致恶意囤积和抢注。这不仅需要提高注册程序便利化程度,还须商标法差别对待注册和未注册商标,通过赋予注册商标权人效力和安定性更强的专有权利,才能激励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尽快完成注册。而另一面向则从抢注的价值基础出发,在侵权之诉的场合针对恶意抢注后的权利滥用行为,及时削减其请求权,降低乃至消除恶意抢注获得的不当收益。这既意味着应当在理论准备层面关注商标注册与使用的关系、民事侵权诉讼与无效宣告行政诉讼的合理衔接等问题,也需要在制定法层面考虑分别针对“禁止使用”和“损害赔偿”增加被诉侵权人的抗辩事由、商标权的直接转移(标识返还)、恶意诉讼行为的赔偿责任等多种方法。两个面向应当呈现为相互配合的关系,恶意抢注者滥用商标权时强化未注册商标所有人的抗辩事由,与激励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及时注册并行不悖,才能令规制恶意抢注的效果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