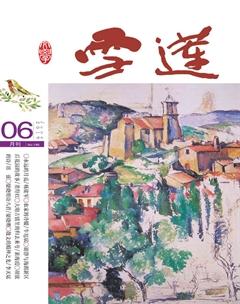一声蛙鸣(外三篇)
秦娥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来到高原许多年,稻花自是无缘,蛙鸣你听到过吗?我听到了,就是刚才。
暮雨潇潇,像给城市噪声覆了一层膜,河流、山岳、草木,还有沿岸楼房窗口里透出的各色灯光,都显得格外安详。举伞独步在杨柳岸,没有残月相照,只有不须归的斜风细雨,沙沙沙,沙沙沙。我尽情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光,心里只被年华虚度的怅然充塞着。在这个城市,身边许多人调了、升了、迁了、走了,只有自己,仿佛是一块石头,孤独立在原处。紫陌红尘,半世沧桑,苦涩于我,成了习惯,却总是在怀疑自我的时候,被一种躲不掉的愁怅缠绕,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呱哇——”,突然,一声久违的鸣叫从远处传来,初闻以为是假声,再闻才觉是真唱。这一叫,颇有几分空山不见人,蛙噪林逾静的感觉。记忆中蛙的形象奔突而来。伊索时代的蛙,是善于雄辩的。而到了芥川龙之介的笔下,苇叶上一只蛙,会摆出大学教授的姿态讲话,认为水、草木、虫子、土地、天空、太阳等等万物都是为了他们蛙而存在,包括蛇。要是蛇不来吃,蛙必然会繁殖起来,世界必然会狭窄起来。被吃的蛙,也可说是杀身成仁,为多数蛙的幸福而献身。“是啊,蛇也是为了我们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悉皆为蛙!”一只老蛙这么回答小蛙的疑问。儿时溜出指缝的小蝌蚪,找到妈妈后居然成了思想者、哲学家,天天喋喋不休,根本停不下来。而在莫言的《蛙》中,蛙是图腾。蝌蚪“我”为了个人的前途,把自己的妻子和差不多足月就要降生的孩子推上手术台,最终导致两人死亡。莫言借“我”之口,说出社会人生的荒诞:姑姑先是给人接生,后为人堕胎,晚年被一群哇哇乱叫的青蛙纠缠,她嫁给捏泥娃的,而养蛙的却替人代孕生娃,蝌蚪则在写一部叫《蛙》的话剧。
莫言说,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最不堪回首的记忆、最尴尬的事,最狼狈的境地。大作家总是对自己够狠。而我,每每一不小心碰到自己难堪的过往,总是唯恐避之不及,而越是如此,那伤疤越是表现出坚不可摧的存在感。说到这儿,聪明的你应该预料到,我得闪离一下。瞧,我就是这样一个怯懦的人。我佩服那些自信十足的人:“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百余年前,年仅16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冲,前往五十里外求学。面对富家子弟的歧视、讥笑与嘲讽,听到春天的蛙鸣,挥笔写就《咏蛙》。
刚才发出叫声的,是这一只吗?
其实,天灾人祸,每天都在发生,而我,没有成为那只被蛇吞噬的蛙,至今健在,多么幸运。相信吧,一条道儿走到黑,总会天亮!
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患得患失,每每计划做点什么,一句话就会跳出来嘀咕:“唉,还不知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也许是因为肠道病的折磨,也许是荨麻疹的骚扰,或许是关节疼痛的震慑,我的神志陷入一片虚无的沼泽中。然而,自那次因病泪洒天路行,半途而废之后,几年过去,除多几道皱纹之外,我还是那个每天忙于编杂志、修史志、庸庸碌碌的我,时间缝隙里偶一灵光乍现,也都被消极懒散悉数截流,我的心在沦陷,虽拼命挣扎,却动弹不得,要喊,怎么也发不出声来。
是梦魇,总要醒来。夕阳无限好,哪怕近黄昏。不论这声蛙鸣是出自哪个,都希望自己视作当头棒喝,振作起来。
骑行的快乐
曾经写过一篇《夜跑》,记录我在湟水河边的“夜生活”。我在文章里雄心勃勃地说,要把夜跑坚持下去,Run fun forerer!不料事与愿违,当我终于习惯了夜跑之后,右腿膝盖突然出了问题,不能打弯,不能用力,有时即使不动也会疼痛。到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退行性关节炎,没什么治疗的好法子。所幸几个月后有了好转,不过不敢再跑了。可是锻炼还是得坚持,要不然,怎么才能脱衣有肉、穿衣显瘦呢?当今社会,可是个刷脸时代啊。幸好,湟水河边,不光有人行道,还有彩色自行车道。而且,几年前,自行车租赁系统一投入使用,我就办了车卡。别说,这一路风景,云、山、水、桥、树、草,曲径通幽,林壑优美,喜欢。现在,一出家门习惯左转,就去河边。
过去脏乱差,天一黑连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来的治安乱点,现在成了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更是我的乐园。沿河人行道、自行车道贯通东西城区,一头连着蜗居,一头连着机关大院,且向两头更遥远的地方延伸,听说长达一百五十余公里。由是,远离生活许多年的自行车摇身一变成了健身工具,有时候,我会从家骑到办公室,乘风而来,驾风而去,比挤公交车爽多了。想起20年前刚从老家来宁时,那个骑行去参加插班考试的情景,至今心有余悸。
由南向北行至小桥十字大下坡处,当迎面一辆大车驶来的时候,我用几乎冻僵的双手使劲捏闸煞车,可手就是不听使唤,我在心里呼喊:天啊,车祸应该就是这么发生的吧,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连同自行车要被卷入巨轮之下,或者被那钢铁巨侠削去一只胳膊,撞得血肉模糊、顷刻间碾成肉泥……我不敢想,我甚至绝望地闭上了双眼!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逃过了一劫!
多年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心里一直纳闷,当年父母亲怎么敢让刚来没几天的村里小孩在这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骑车呢,又没有自行车道,且是寒风刺骨的冬天?
还有一次,放学回家,我脑袋一热把自行车推进门房,没上锁就回了屋,转眼间自行车就不翼而飞了,当时那个懊恼,那可是刚买的变速山地自行车啊,我喜欢的藏蓝色,该死的盗车贼啊,我懊恼自责了好久。
再后来,时间惊风而过,女儿居然也初中毕业了。那会儿,中心广场刚修好,健身热正悄然升温,广场上玩滑板的、骑双人自行车的很是流行。女儿也要辆自行车。我们俩在西门商场逛了一圈儿,看中一款粉白相间、小巧可爱的自行车,轮胎直径只有30厘米大小,低矮的车梁上白底黑字印着英文“FOREVER”,好萌,宛如春天里笑春风的碧桃,也像我电脑桌面壁纸上那个“人面不知何处去”转入此中来的小姑娘,和女儿很配。后来我还想到,那个英文,恰巧是我大学最要好的闺蜜私下給我起的名字,而我给她的昵称则是“一字”,谐音“easy”。就在商场外的中心广场,女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骑车。而今天,当我写这篇小文时,她正在上海外滩骑行小黄车呢。
女儿的萌车,停泊在我的阳台上,一直赋闲在家,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用了,毕竟上下楼不方便,况且有了河边的健身车,也没必要再去费力搬动它了。这辆萌哒哒的小车,未来要么留它作个纪念,要么就等亮亮放假回来挂到“闲鱼”上,转手给用得上的朋友好了。
购物方便
周末,我不用去上课。吃过午饭,母亲交待我去把当月供应的米面买回来。能帮家里做些事,我是很乐意的,虽然我嘴笨,手也笨,好在去粮店买供应的米面是不需要讨价还价的,说是买,更像是领取。于是,我接过母亲递来的粮本愉快地出发了。
从西山巷骑行到“西关街粮店”,把自行车停在东侧的一个角落,锁好,就往粮店里走去。粮店不大,可一派忙碌景象,身穿白大袿的男女店员们头发眉毛都覆盖着一层白,像是刚从面缸里爬出来一样。因为供应限量,品种单一,只有大米白面两种东西,所以无需挑选,无需废话,进门我就把粮本交给白大褂,我看见白大褂将粮本塞在最下面。然后,我就出来等候,只等着喊母亲的名字。我家户口本上户主一栏是母亲的名字,粮本自然也是。
要说人也不算多,但络绎不绝,不一会儿,窗口外就站满了人,男女老少,啥人都有。我站在人堆里,并不着急,凡事只要按次序来,总不会错,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何关系呢。
可是眼看人们一个个都买回米面走了,母亲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喊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焦急起来,越过一颗颗黑压压的脑袋往窗口里张望、询问:“我等很久了,怎么一直没轮到啊?”
“啥名字?”白大褂问。
“徐秀英!”我答。
白大袿上上下下地翻了个遍,又问我是哪个字,我告诉她是双人徐。
没有啊,其他售货员闻声也走过去,看看我,再翻翻粮本,都说没有。
这下,我更急了。起初出门时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感觉到口干舌燥。
我这边急不说,在家等米下锅的母亲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也急了。
“就这么点路,早该回来了啊?”母亲念叨起来。
“咋办啊?”我自己问自己。店员又开始给其他顾客提货、登记。
无奈,我只好空手而回。
正在路口张望的母亲,手里还剥着一棵葱,见车上空空如也,连问米面呢?此时的我,再也忍不住委屈、焦急和无奈,泪水夺眶而出。
“咋能没呢?你没跟人家说名字吗?”“我说了啊,徐秀英!”
“咦,不是跟你说了吗,是借你香亭婶家的粮本啊?”
“啊——”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哭笑不得。只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母亲啥时跟我交待过这句话。
幸亏,现在是网络时代。以前,要么是试衣时被窃了包,要么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喜形于色,被店员掐住“三寸”宰杀得不轻,事后后悔不迭。凡此种种,窘态百出。自从有了网购,一切便都迎刃而解。网络,给我最大的福利就是购物方便。万能的淘宝,没有什么是买不到的。大到直升飞机,小到针头线脑,应有尽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用支付宝、微信支付还有收益,有买有赠,就连乘公交车扫码付也比现金优惠。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跑断腿地去找、磨破嘴地侃价,越想省钱越吃土,一不小心还有假币流入手中,那叫抓狂!唉以前购物的血泪史都过去了。瞧,怀府上品的老式爆米花、家乡的红薯面粉、云南的雪莲果、江南的橘柚、越南的榴莲……只需动动手指,不费任何口舌就能送货上门,如果你不满意,还可七天无理由退货。
那个粮店也早就没了,装修时尚的塞奇西饼取而代之,每次从那里经过,糕点的香味会穿过门缝,扑鼻而来。
涨知识
整天整天宅在家里,偶一出门,目光总是游移在蓝天白云或花草树木身上,所以我手机里的照片也总是这些无言的朋友。“八怪”房前的芭蕉、瘦西湖的烟柳、松江的栾树、天山的冰草,高原的格桑,尖扎的杏儿,故乡的水萝卜棵儿,家门口的榆树、槐花,阳台上的散尾葵、幸福花……只要是足迹走过、目之所及的地方,我总会把那儿的花木珍藏。这些花草,惊艳了我的双眸,丰富了我的文章。难怪女儿会嗔怪地说:“就知道拍树!是啊,我的心总是和它们贴得最近。有一年,高原已经入冬,我出差到扬州参会,那里还是花草繁盛,一场雨过后,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三三两两地落下来,叶子比张开的手掌还大,我捡了几片小心地捏住叶柄,一边走着看着,一边和那些树木合影,一位来自安徽的同行大叔看我拍个不停,面色诧异,这些东西有啥可拍的,到处都是!他不知道,如果不是来出差,我这高原的孩子一辈子也只是看得见而摸不到啊。这些花木,我有的知道名字,大多却不知道,问身边的人,往往也问不出答案。遗憾。为此,我这个很少打电话叨扰朋友的人,倒是为了识得花草殷勤为探看,一次是在去往果洛的山坡上,发现一种貌似郁金香却浑身长满绒毛的花,一次是在民和黄河边上,初见满身红云的小树。两次惊艳,时间相隔却有好几年。第一次我致电仁青老师,那个时候,他还任职在广播电视报社。后来,我把这事写在《寻找格桑花》里,发表在《西部人》杂志上。第二次,仁青老师其实就在身边,同行的七八个人也都叫不上树的名字。返回后,我电话请教农林行家董得红,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说,是紫叶李。这次,我的《三棵树》里另外的两棵树,一棵是见证十世班禅为转世灵童的菩提树,一棵是骆驼泉边,像是我失散多年的亲人的悬铃木,文章就发表在当时自己任职的《青海湖·视野》(半月刊)上。
感怀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起因是结识了一位新老师:识花君。
昨天下午,突发奇想,网络这么发达,既然有“传图识字”,应该也有“传图识物”吧?这一想,再一搜,果然就查到若干识花小程序。大喜。捱不到下班时间,我招呼一声,就先溜了。已经是四月末,不少花木芳菲已尽,再迟恐怕就要等到明年再见了。匆匆赶回,路过家门而不入,我径直赶到我的“百草园”、我的“瓦尔登湖”,那里有好几位久处不累的好朋友,只见其人而不得其名呢。
傻傻分不清是碧桃还是榆叶梅的粉色花树,不明白是连翘还是迎春的金色灌木……我连连摁动快门不停地拍拍拍,再迫不及待跑回家,用wifi一张张地传图识花,“识花君”不负所望地一一给出答案。原来,这些倩影分别对应:北美海棠、滨海山茱萸、东京樱花、巴天酸模等等。就这样,大观园里林妹妹所咏“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的白海棠,我知道也叫八棱海棠,是蔷薇科苹果属,花3—6朵呈伞状花序,以5朵居多。识花君还说,它果实酸甜,营养丰富……相见恨晚,为啥没早点认识这样渊博的好友呢?
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宅在家里,偶爾才出去开个小会,或者到印刷厂去一趟,大把大把的时间就耗在瞎琢磨上,就琢磨这些无言的朋友,琢磨人生之谜底。没有来得及认真地年轻,剩下余生,我想认真地老去,就和它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