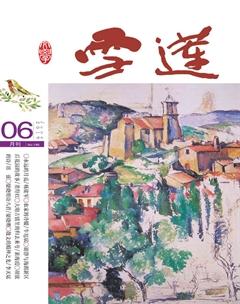乡间变奏
惟刚
听 溪
我是在十一月初走近它的,如同一个迟到的赴约人,错过了它花香馥郁的时光。每次途径,一条安静的溪流在车窗中一闪而过,它所囊括的诸多美好,被我的匆忙忽略了。心中想着,总有机会亲近它,这便是我对每棵树,每座山,每条河许下的诺言。此刻,山雾氤氲,四野寂寥,舒爽的凉意裹夹着泥土湿润的气息,盛满山涧。
一条溪流静静淌在苍荒的山色中,水里的草茎,砾石清晰可见,它太安静了。顺流而上,溪流的随意绕行不断给我造成障碍,双脚一次次陷进淤泥中,我沾满泥巴,也满心欢喜。有时,它也备好宽阔的滩涂請我和它并行一段。行走在这样一条安静的溪流身旁,如同和一位久违的老友相逢。平缓处,流水划过水草,咕噜一声,多么惬意啊。水流好像在换一个更好的姿势,翻一翻身,舒一舒筋骨,伸一伸懒腰。遇到石涧或落差,一串从不间断的音符从水花中喷出,白色的水花跳跃着,水流跌跌撞撞一路前行,卵石铺就的河床成了它欢舞的剧台,一到平缓处,即刻便恢复了平静。蹲在水流飞溅处,永远不会觉得厌烦,我的躁动和不安都在这水花中破灭了。在寂静的高原深处,有这样一条跃动的溪流滑过,真是难得的恩赐,它把整个高原都唤醒了。
溪流边匍匐的草丛,冲刷开的河床,被灌木丛拦下的泥草,此刻却静若处子,此刻的安静如同忏悔。整个山涧一片萧瑟,就在前一阵,霜来了两次,大多数草木经受不住而偃息了。我逆流而上,溪水顺流而下,在这逆差地相随中,我如同一个飘游的浮标,遁着清澈的诱惑,在这水声哗响,雾气弥漫的山涧中,搜寻着从我身上丢失的记忆与翅羽。我粗砺的脚步声和溪水的潺潺越发协调了。山涧两侧的断崖高耸,崩落的石块棱角分明,荒草中石块上的苔藓,在水气中被腌渍的得愈发沧桑而沉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环顾四周,眼前宏大的山崖,流淌的小溪,凋敝的荒草,渐渐隐退的山雾,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顿觉清爽。放佛我的每一根骨骼都得到了清洗和晾晒。
孤 树
在延绵无尽、起起伏伏的内蒙古草地,在沟壑密布的黄土高原,在烈阳高照的沙丘腹地,在那些裸露、贫瘠、开阔的干旱地区,我的目光总被那些孤零零生长的树吸引,它们没有壮硕的枝干,阔大的叶片,树种也较单一,常见。都是耳熟能详的柳树、榆树、杨树等这些植物界平凡而永久的常驻民。
远远望去,它们宿命般矗立在那里,与整个山丘浑然一体,尤其是在盛夏,它们托举起一簇幽深的绿色,贫瘠的山头不再显得荒寂,无论阳坡,还是在阴洼,在群山间,在村庄与村庄之间,在奔涌的大河沿岸,它们如同持久的信念,天和地精心孕育的长子,仿佛又是某个佑护之神的化身,无论是谁都会向它投去敬畏的一瞥。这毫无遮挡的高处啊,它经受着最强劲的风雨,无论是湿润的南风,还是凛冽的北风,只朝向它们吹,匍匐在它们旁边的小树或荒草,只是些多余的点缀而已,它俯瞰着群山浩荡,与远处同样的孤树遥相呼应,只有它们之间能互相感知彼此那些经由强风劲雨浇铸的枝叶。不因风雨流动,不随季节迁徙,它不孤独,那来自遥远的神秘信息,来自大洋、雪山传送的隐隐暗示,在这里全部得到转译,日月星辰的光芒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它们身上,最雄健的鹰隼、这天空的娇子,会歇息在它的肩头,纵然季候风赶着荒草一层层漫过去了,河流被冰封又被阳春解冻,但它作为某种担当或象征永久地挺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与鸟儿为伴
夏末,我在神木南部的乡村观察。此时正值庄稼成熟之际,远远望去,一片接一片的谷物在热烈的太阳下闪光,此时是土地在一年中最富有的时刻了,天地一派欢舞。我在地头畔遇见了一个手持细木棍的老农,不停地在一片谷地边走过来走过去,在绿汪汪的谷地间,零星插放着一些用破衣烂衫、碎布料简易扎编的人偶。我上前询问事由,他笑盈盈地席地而坐,递给我一根香烟,他说鸟雀每年在这个时候最猖獗,谷粒还未完全成熟,成片成片的鸟雀就过来争食,他每天过来看守着,我问这有作用吗?他说开始几天还好,等鸟雀识破了这些虚设的恐吓时,就完全为所欲为了,他笑呵呵地说,来这里也是装装样子,起不了多大作用。我看到他手里的细木棍,也无非是稍微加大了他挥舞的幅度。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说起节令、耕种、雨水,至始至终,他脸上洋溢着知足满意的神情。期间,鸟雀呢,不时在地里飞进飞出。说完老农又乐呵呵地走向他的谷地,嘴里哼着小调。与其说他来这里是为了驱鸟,倒不如说他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殷勤地陪着这些天空的来客分享他的收获。鸟雀在这片繁盛的高原上,提早收割着农人的大度和善良。
远去的先知
山脊之上,一些圪针和蒿柴之类的野草密密麻麻地占领着这块高地,这些荒草承受着最强烈的风寒、干旱。山脊之下,都有一条忠实的河流趟过,硬岩层、砂质岩层被一路切开,裸露的岩层就是镌刻着真理的书页,这条河千万年都在书写和阅读着这部大书。大自然对只倾慕名山大川、江河湖海的人永远心存芥蒂,绝不会将自己真正的秘密倾吐半点儿。唯有对那些将足迹遍布在草丛中,将眼睛定格在它最微小的事物上的人才会敞开自己所有的门扉,展现它全部的美。对于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的小溪流,大多无人问津。无论春夏,它都恪守着做为一条溪流所有的准则静静流淌,它没有明确的方向,山川造就了它们的路途,时节首先向它们发出诏令,它是自然界最忠实的顺民。它们没有“河润千里”的宏愿,只是滋养着沿途的草滩和饥渴的昆虫,一些杂草就可以将它们完全隐没。在平缓处,溪流便沉寂安逸地淌过,跌落处则倾泻而下,不做任何迟疑和停留,如遇高处,不急不躁,安然地等待蓄满,当汇入浑浊的大流时,它依然澄澈明净。所到之处全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些朴素的小村庄,牛羊小憩反刍的滩涂,鸡鸭嬉戏打闹的洼地,清澄的流水一路携带着农人恬静的歌谣蜿蜒而去,弥漫着先知沉寂而孤独的思想渐行渐远。
鸟 鸣
清晨,公鸡最先跳下栖架,照例抖抖它的绒裙,扯开嗓子,为这崭新的一天鸣钟奏乐。
高亢的鸡鸣声,从院落传出,抵过墙头,漫过树梢,回荡在氤氲笼罩的山前村后。母鸡慵懒的咕咕声也蠢蠢欲动,迫不及待地附和几声。麻雀的唧唧喳喳如密集的鼓点,顷刻间,喧嚷起来,整个村落,被这从树梢中洒下来的活跃之声点燃了。炊烟、小路、栅栏如同被包裹在一座银色的音乐水晶宫中。
日渐高升,鸟雀从这一边浓密的树荫里飞出,加入到山的另一个树丛,好像经过几番试音,觉得那里更适合自己的音调。农人敲击农具的叮当声也零星加入这场合奏,清脆的金属亮音,比鸟儿的歌唱更沉稳、娴熟。期间,也会有一两声孩童的嬉闹声传出,便又迅速隐没在某个院落当中。
太阳一杆高时,光影交错,雾霭逐渐退去,此时,如沸腾一般,鸟雀们格外卖力,它们鼓足了劲,越唱越熟。一顿饭的功夫,农夫们开始下地,在路上不时相遇,寒暄几声关于雨水和时令的话语,浑厚、爽朗的谈话声一经发出便融入这盛大的伴奏中,如同西方教会颂歌中的伴唱。
有一种鸟,一直以均匀、清澈、声调一致的呖呖声,贯穿整个乡村的清晨,直到太阳高悬,土地暖和起来,它才戛然止住了它的鸣唱。
林间夕照
风静止了,傍晚到夜幕降临总会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恬静时刻,为这繁忙的一天轻奏一曲祥和的尾奏,明亮、低缓、柔和,太阳开始极力挥霍它的余光,盛夏的草木被这日常的恩施映照的格外肃穆。我从路边停下车来,径直走入这片被闲置的空地,想急切地同这些青绿的草丛没入温和的夕照之中。六月的原野,庄稼刚露出尺把个儿,树叶像刚破茧的蝶翅,在闪光中耀动,浅绿的草丛间夹杂着去年的枯枝碎叶,我就走在上面,我是他们之间唯一可以走动的生命体了,目光所及之处,皆尽善尽美。在四月,被翻耕过的土地伤疤似的裸露着,而现在,被庄稼抚平了,齐楚的稼禾同杂草树木开始一道共度这不羁的青春时光。
夕阳在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映照之后,开始变得暗淡,红晕仅弥漫在梢头,做摇摆状,仿佛代表这片林草地向西方作别。当夜幕升起,这地上的蛙虫渐渐亮起了嗓子,整个田野浸入在清风和虫鸣回荡的谐和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