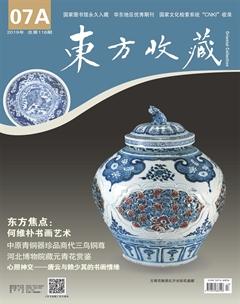以“戏”入画 以“画”品戏
沙伟



关良这一名字,对于了解近现代国画史的人无不知晓,这出于其在画坛成就卓著,对后人影响深远。而他集戏剧艺术与写意人物绘画于一体,熔两者于一炉,做到“画中既有唱念做打,戏中又有笔情墨趣”的戏剧人物画,更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可谓以国画写意人物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戏曲经典剧目中的重要桥段所展现的人物造型、身段手势,能够以笔墨语言跃然纸上(图1 关良和他创作的戏剧人物画老照片)。
艺术创作的成因
幼时父亲偶得的几张“洋片”(香烟牌子),十来岁“会馆听戏”的经历,就引领少年关良于朦胧中,走进一个集社会、历史、文化于一体的艺术世界。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这些生动的故事、有趣的造型、简易的线条、多姿的色彩,令他以古典小说与戏剧题材为主,“绞尽脑汁”地收集数百张香烟画片,并从此开始意犹未尽地模仿涂鸦。
青年时代的关良原来是留学海外学习西画的,但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回国后的他却形成了回归传统的意识。他加入了当时群贤聚集的“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学术研讨活动,并主动结识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中国画坛领军人物。且在这些文化名人的影响下,临摹明清大家作品、观摩参观国画展览、欣赏名家收藏画作。同时与沈雁冰、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大家开始交往,并在坚定“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的艺术追求之时,为更多地借助中国画笔墨与观念,而探索一条新的“表现中国”的绘画主题之路。且在国画与文学的相互交融中,他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从小热爱的戏剧,正是他苦苦追寻之新的契机。
关良走入中国画创作道路的动力之一,就是戏剧中演员的身段眼神、布景道具的程式化意识、灯光服装的色彩构成,这些均成为了他笔下的构图、造型、气韵、色彩之创作元素。并由此开始以“戏剧人物画”为创作主题,成功实践了西画与国画的结合,出现了第一次重要的转折。如他创作的《游龙戏凤》(图2 1944年作,80×99.9厘米,中国美术馆藏)、《白蛇传》(图3 1956年作,67.5×70厘米,中国美术馆藏),不仅为关良实现“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艺术境界找到了方向,而且还体味出他的写意画高度,以及其概括的笔力神韵与艺术趣味。
稚拙浑朴的画风
纵观关良的戏剧人物画风格, 首先是线条语言的运用。在中国传统绘画中, 最具表现力的造型手段、最具审美意味的艺术语言就是线条。而在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中,线条的内涵却更加丰富。用线除了轮廓造型之外, 结构也随动势用短粗的线条写出, 犹如行草的书写,却又气韵流动而贯通。故此种意义上,他的戏剧人物造型“似乎”结构比例不准,殊不知这正是他不拘泥人物解剖结构本体及细枝末节的简单肖似,而求神夺势、笔从气来之高妙手法。以《乌龙院》(图4 上世纪60年代作,67.5×44厘米,中华艺术宫藏)、《空城计》(图5 上世纪60年代作,34.5×34.5厘米,上海中国画院藏)和《武松打虎》(图6 1974年作,68×43厘米,中华艺术宫藏)为例,三幅作品的线条指向重在传达神韵气势,并不在简单地塑造结构。仿佛一笔写出画中人物, 气息连贯整体。同时充分利用戏剧人物脸谱的造型与色彩,匠心独运、大胆生辣地进行面部处理, 令造型夸张、用色饱满之余,线条恣意勃发。作品虽看似稚拙的“儿童画”, 用笔功力却透出凝滞、舒缓、力透纸背, 完全是一种中和内敛、深沉朴茂的审美意味之体现。
在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中,其强调脸谱、服饰、动势、道具等戏剧本身的造型元素,而人物则趋于平面建构,弱化了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如他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7 上世纪70年代作,31.5×34.5厘米,中华艺术宫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图8 上世纪70年代作,68×68.5厘米,中华艺术宫藏)。这是他吸取了民间艺术的造型特点,可谓与汉代石刻艺术异曲同工。同时他不求面面俱到, 但求大胆概括,重点刻画艺术形象的动态与情感流露,注重整体动势造型, 似得其意而“忘”了其形般,以势夺人地传达出不同人物的精神气息与神态之美。特别是在表现塑造人物的动态方面, 他更是汲取到汉代画像砖的精华, 不仅极具蓄势待发之力, 更充满一种潜在的生命力度。而开张生动的简洁造型,亦形成了饱满充实、凝重浑朴的画作构图。
“他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这是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其《漫谈戏曲画》中谈到的关良。与关良为莫逆之交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亦曾评价“关先生的(戏剧人物)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这说明关良对戏剧十分懂行,能选取戏里最为生动传神的动作神态入画。由于戏剧中的看、瞟、盯、瞧、观、见,全得凭借一双眼睛观察,是对戏剧艺术家、画家的考验,因此关良点睛目也是把画全部完成后才进行。而不同的人物、场合看不同的对象都有不同的感觉,故画家和戏剧艺术家一样,对此要把握分寸、细细揣摩,最后才能大胆准确地落笔。如关良的《打渔杀家》(图9 上海中国画院藏)、《鸳鸯楼》(图10 上海中国画院藏)、《春香闹学》(图11 1983年作,67×67.5厘米,中华艺术宫藏),眼神就抓住了戏中人物的转瞬即逝,并将单纯的舞台动作,提炼成倾吐角色内心活动的肢体语言;再进一步将肢体语言提炼成笔墨精妙、极具写意性的绘画语言,且使之跃然纸上。
传世佳作赏析
关良的戏剧人物画《晴雯补裘》(图12 1985年作,68×46厘米,中华艺术宫藏),描绘的是《红楼梦》题材,即晴雯带病连夜织补贾母送给宝玉的孔雀氅之场景。作品不拘泥于对人物的解剖和透视,并以戏剧人物造型为基础,不加修饰地将夸张、变形之手法传神写照,甚至带有儿童画的稚拙。且画家力求质朴平易、凝重自然的笔势笔趣,让笔墨变化多端。同时演员的“看”“瞟”“盯”“瞄”等眼神捕捉到位,令人物情态纯真幽默、惟妙惟肖。
《捉放曹》(图13 1980年作,68×68.5厘米,中华艺术宫藏)是关良创作的《三国演义》题材。作品中陈宫身穿黑袍、手持宝剑,而曹操身穿红袍、伏案假寐。作品在色彩上一黑一红形成强烈的对比,观众的视线瞬间就被抓住了。而在色彩的运用中,画家对色彩的过渡与对比很注重,并且吸收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手法。您瞧位于陈、曹中间的黄色桌案,不仅弱化了由于色彩对比过于强烈而产生的视觉刺激,还令画面显得更加和谐统一,让黑、红两色有了融合和与过渡的空间,使得观者看来更加平和舒适。另外,“点睛”之笔是关良的戏剧人物画创作中之鲜明特色。其看似粗枝大叶,实则细腻严谨。同时戏剧内容、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同,决定于人物眼神或喜或悲、或瞋或怒的明显差异,宛如此作中陈宫眼里流露出的犹豫与悔恨,皆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了充分表达。
《苏三起解》是京剧《玉堂春》中的精彩片段,“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均曾有过精湛的表演。关良作为现代水墨戏剧人物画的开创者,亦非常钟爱此剧并反复画过这一题材。关良创作此幅《苏三起解》(图14 1979年作,96×90厘米,上海中国画院藏)时年近八十高龄,当时正是画家迎来晚年创作的一个新高峰。此作《苏三起解》中,画家采取了背景留白之画技,对人物的神态进行了着重凸显。而苏三和崇公道两人稍微错开的左右之势,亦极具舞台效果,暗示出一个戏剧发展的纵深空间。由此可见,中国戏剧艺术强调“动作语言”的内在精神,与关良的戏剧人物画所具有的简练概括、写意传神之画风,具有相通之处。
关良的这幅水墨戏剧人物画《太白醉写》(图15 关良79岁时创作),绘的是同名京剧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内容取材于《今古奇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国传统戏剧是写意文化的产物,全凭角色的唱、打、做、念表演之“神”才有“戏”,舞台上人物和道具实在是不多,故别具一种简练传神的韵味。关良在这幅作品中正是抓住了“简”与“神”两点,完全描绘出了自己的意趣。画作以若不经意的线条,中部绘出李白自信酣畅的神情,左右两侧再巧妙地表现出高力士与杨国忠既惊又怕的眼神,最后又在李白后方巧妙地写出杨贵妃顺服的表情。其处理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满是关良灌注其数十年对戏剧情节的熟识、对戏剧人物性格的把握,才使得其运用线条、墨色的睿智一览无余。此作的妙趣在于虚实相生,尤其是画纸上的人物如戏剧场景定格的瞬间般跃然纸上,因此作品极富表现力。
热爱戏剧的关良以“戏”入画,以“画”品戏,曾言“戏剧表演与绘画相通”。 华美的戏剧,写意中国画,夸张变形的西方现代绘画,使得他以戏剧人物为题材,以东西方绘画技巧为手段,对此披荆斩棘、继往开来地进行了一生的探索和创造,成为了中国绘画史上筚路蓝缕的先行开拓者。并通过戏剧人物的情感, 在作品中抒发阳刚、浪漫的个人情怀, 彰显出一种乐观、刚正的民族精神,且令戏剧人物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标签”和“品牌”。现今笔者在此浅析其独特艺术语言,企盼能为当代的中国画坛提供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