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如何加速沙皇俄国的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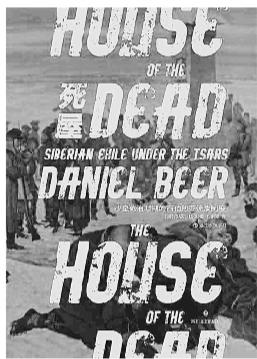
随着西伯利亚的监狱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革命的群众基础也在西伯利亚迅速扩大。
钱冠宇
对于深受苏俄文学影响的一代中国人而言,西伯利亚是一个遥远而熟悉的地名。提起这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一群戴着镣铐的犯人,在冰雪茫茫的苦寒之地,艰难地前行或劳作,内心充满悲愤和绝望。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从十二月党人到波兰革命者,关于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故事和诗句始终令人难以忘怀,其中既有对道德灵魂的无情拷问,也有对自由人性的赞美歌颂。然而在文学精神之外,一般人很少了解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具体是如何起源并运转的;这种意在维护沙皇统治权威的制度,为何却加速了帝国的覆灭?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The House of the Dead: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出版于2016年,作者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此书问世后备受瞩目,并于次年赢得全球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坎迪尔奖”(Cundill History Prize,奖金为7.5万美元)。丹尼尔·比尔利用藏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中央档案和西伯利亚城市的地方档案,以及各种文学作品、回忆录和信件,还原了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这段历史时期内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种种遭遇。
一般认为,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始于16世纪末的“铜钟流放”。
1591年,伊凡雷帝之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他的居住地乌格利奇猝死。德米特里的母亲一方家族认为,德米特里是被皇位争夺者戈都诺夫谋杀的,为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号召当地人起义。戈都诺夫下令军队开进乌格利奇平息叛乱,并在第二年春天实行审判,起义者在遭受刑罚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一同遭到流放的还有那口象征着乌格利奇人政治团结的铜钟。
在俄国人开发西伯利亚之前,乌拉尔山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的统治者是蒙古人。1582年,哥萨克雇佣军首领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击败了日渐衰落的西伯利亚蒙古统治者,打开了俄国人通向西伯利亚的大门。此后,俄国便向整个西伯利亚地区迅速扩张。
在丹尼尔·比尔看来,“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18世纪起,沙皇政府开始重视流放人员在征服西伯利亚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已经把流放制度发展成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殖民项目。为了维护俄国欧洲部分的稳定,政府将叛乱分子、宗教异见人士、罪犯、妓女等人群成规模地流放至乌拉尔山以东,同时促进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丹尼尔·比尔充满洞见地指出,西伯利亚对于俄国来说,兼具惩罚与殖民的双重作用,而这两种作用本质上是相互抵消的。
借助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的光照,19世纪的俄国掀起了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浪潮,在思想和实践上对沙皇权威形成挑战。尤其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出现了十二月党人、波兰革命者这两次著名的西伯利亚流放事件。
十二月党人与希望之地
1825年12月14日,三千多名俄国陆海军士兵聚集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发动反抗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最后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战略规划而宣告失败,后人把这群勇敢的贵族起义者称为“十二月党人”。事后,尼古拉一世为了表现沙皇的怜悯和宽赦,只判处了少数主犯死刑,另外一百多名军官则被褫夺公民权并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整个西伯利亚流放史上,十二月党人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令沙皇始料未及的是,西伯利亚不但没有消磨和囚禁十二月党人的抗争意志,反而敞开怀抱,为这批壮志未酬的革命者提供了传播启蒙思想的舞台。
十二月党人的到来为荒凉野蛮的西伯利亚赋予勃勃生机,在流放途中,其中一位流放者这样写道:“我们越深入西伯利亚,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国农民,尤其是农奴,那里的平民百姓看起来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养。”他们仿佛在乌拉尔山以东发现了可以对抗俄国欧洲部分沉闷僵化等级制度的社会现实。
在流放地,尽管十二月党人的苦役生活充满压抑和绝望,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对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作为俄国贵族精英阶层的流放者,十二月党人为西伯利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将俄国欧洲部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传播至此。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有人从事园艺,有人进行昆虫收藏,还有人开展民族志研究、编纂布里亚特语-俄语词典等等,不遗余力地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丹尼尔·比尔高度赞美了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而且,“下一代政治流放者会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脚步。在被剥夺了在当地追求民主目标的机会后,一些政治流放者会在西伯利亚找到释放他们的改革能量和进行公民活动的地方”。
在十二月党人崇高精神的引领下,西伯利亚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地狱代名词,它甚至成为鼓舞新一代革命者实现理想的希望之地。
帝国瓦解的加速器
西伯利亚除了俄国本国革命者外,还留下过许多波兰人的足迹。18世纪,波兰三次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瓜分而亡国,从那时起,就有许多波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沙皇两次将波兰起义者作为政治犯大规模地流放到西伯利亚,天主教信仰亦随之传入。
波兰犹太画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的名作《再见欧洲》描绘了1863年波兰起义者在冰天雪地中穿过亚欧界标的凄苦情景。尽管穿过界标的波兰人特别注意保存自身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避免过度“俄罗斯化”,但整个19世纪,大部分西伯利亚的波兰人还是通过与俄罗斯女人结婚完成了民族融合过程,譬如从天主教改信东正教。
那么,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究竟是如何变为俄罗斯帝国瓦解的加速器的呢?
丹尼尔·比尔在书中不断向读者表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惩罚与殖民的根本性矛盾,这两项功能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相互拆解,使得西伯利亚很快沦为腐败和罪恶的渊薮,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越狱、强奸、暴乱等事件频发,加剧了沙皇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正如十二月党人展示的那样,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形象在后世被塑造成革命偶像,激励着一代代的革命者前赴后继。在流放者群体内部,共同的苦难经历也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西伯利亚流放殖民地越来越像密谋反抗沙皇统治的学校,“新成员可以在这里学习革命学说,资深成员可以在这里创造出大量革命理论和文章”。例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年都有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由于出身等级和财富,他们在流放地生活得较为舒适,甚至还可以自由读书和写作,构想激进的革命蓝图。
在1917年二月革命终结沙皇统治之前,1905年帝国境内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行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就像列宁说的那样,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沙皇政权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使俄国民众与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隙,同时也为西伯利亚制造了大批政治犯,这些政治犯让西伯利亚的监狱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
丹尼尔·比尔指出,“随着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动农民、罢工工人、哗变陆军士兵和水兵、银行劫匪、大屠杀参与者、盗贼和坚定革命者,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这就意味着,革命的群众基础在西伯利亚迅速扩大,从上层精英走向社会底层,来自帝国不同角落、族群的人们开始同仇敌忾,为1917年的革命风暴积蓄力量,加速了帝国的倾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