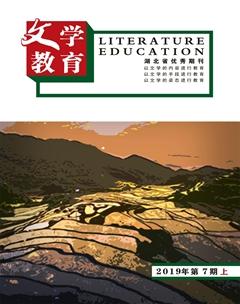论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
内容摘要:王小波杂文读者众多,影响深广,与其独有的“假正经”腔调密切相关。首先,戏拟与反讽在杂文中相辅相成,共同形成“貌似正统,故作庄严”的叙述语调,同时腔调自身又实现对历史的戏拟。其次,“假正经”腔调作为语言的艺术,在语言层面就实现对历史、权力、话语的解构,并在此之前竭力消除言说本身可能形成的“话语制造者”痕迹。再次,“假正经”腔调展现相对独立的文学意义,文体成就体现于其独特鲜明又相对稳定成熟的语言,在外部标志上使杂文文体得以确立,将道义感与幽默感相结合,从审美走向审智,最终使王小波杂文自成一格。王小波杂文写作后期,面临内在生命力不断消亡的问题。
关键词:王小波 杂文 语言艺术 腔调
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占篇幅尚不多,但文学影响不可小觑,他被戴锦华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位极为独特且重要的作家。”[1]王小波在大陆首先以杂文名世,1992年他从大学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后,曾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读书》、《东方》等知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后有多部杂文集出版,一生写作杂文共计35万余字。“他比学者可读性强,比作家学理深,加上文体别致,可以称得上杂文家里的一线。”[2]王小波杂文能有如此接受广度、影响深度、成就高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独有的叙述腔调。本文聚焦于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重新发现王小波杂文的语言艺术,继而从文学性入手,探讨这种腔调在本质上的解构倾向与文体追求。
一.作为语言艺术的“假正经”腔调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往往被视为审美的语言作品。诸多评论者均认为“王小波他思想的深刻,或者说所涉及的自由主义话语并不艰深,是他把它讲出来的这种方式,很有特点,是别人所做不了的,让人看了击节赞赏。”[3]可见这种独特的“讲出来的方式”(讲述方式),是王小波杂文语言艺术的重要体现。对此,本文提出“假正经腔调”这个概念:“腔调”在叙述学里称为“叙述语调”,指“叙事作品本文表面的语词声音以外,在叙述代言人的后面所具有的贯穿于整个叙述结构的语调。”[4]而“假正经”的定义出自林贤治《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他(王小波)的文章,经常出现一种貌似正统,故作庄严的东西,这种‘假正经,正是他借以亵渎神圣,毁坏偶像的利器。”[5]阅读王小波的杂文,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就是他的这种“貌似正统,故作庄严”叙述语调,从遣词造句、形态结构中渗透出来的一种情绪气质,几乎可成为他的语言风格的表征。因此,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正是属于他的独有的讲述方式。
本节分析“假正经”腔调在文本中的具体展现。“戏拟”可谓王小波实现“假正经”叙述的重要手段,“戏拟(parody)”即“一种滑稽性的模仿,将既成的、传统的东西打碎加以重新组合,赋予新的内涵。”[6]从中可看到作者带有明显的故意性,对自己要批判的对象话语进行模仿,从而起到消解对手的效果。王小波向来反对在杂文中掉书袋,故作高深,卖弄学问,他于1996年底发表的《有关天圆地方》中明确说到:“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一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写。”然而,在1997年发表的《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一文开篇却是:“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显然这是模仿了“学者型”作家、批评家故作高深的叙述语调,他并未进行直接批判,仅仅用故作一本正经的模仿,却更姿态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鄙夷和嘲讽。
事实上,“假正经”三个字在王小波杂文中多次出现,最为典型的是他在杂文集序言里说:“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7]乍一看,这出现了论述的自相矛盾处:“假正经”无一例外都成为王小波批判的对象,其本身如何又能具备批判性?林贤治就此指出:“在这种话语形式中,他可谓如鱼得水,使叙述省去许多笔墨,是超乎传统‘文章作法的一种凝炼,充满张力。”[8]王小波正是借助着这种自古有之的话语形式给他的庇护,行文的言说在无形中具备了合法性,他珍视这有利位置带来的每一分好处,借以施展自己异乎寻常的才能——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假正经”腔调自身就是对历史、传统最大的戏拟。
除了戏拟,“反讽”也是王小波实现“假正经”叙述的常用手段,异质性的嫁接往往被视为反讽的本质特征,所谓“异质性的嫁接”,是指将截然不同的事物放在同一个论域,差异得以彰显,使人们重新审视之。在一个深深体悟到荒诞感的精神世界里,反讽无疑是极具抗争色彩的写作手法。王小波杂文中随处可见“阴阳对立”的两界、悖立的结构,如《沉默的大多数》中将“鼓风机”、“钢铁”与“屎壳郎”、“牛屎”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奇妙地组合,前者伟大神圣,后者粗鄙低俗,加以作者讲述时明显的刻意态度,反讽的效果就在强烈的反差、悖立间产生了,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发现那个时代浮夸风气的荒诞之处。又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将“猪”以“兄”相称,并冠以“特立独行”、“浪漫”等词,人反而非“人”,加之作者很强的叙事意识和故意态度,那个时代里人的生存状况受到无尽的讽刺、挖苦。值得注意的是,反讽的手法还见于“归谬”、“证伪”中,如《积极的结论》里,当“亩产三十万”的口号铺天盖地而来时,王小波并不直接批判,而是一本正经地进行逻辑推理:“一亩地上堆三十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玛拉雅山了。”他先假定“亩产三十万斤”的命题为真,最后得出合理却离奇的结论,使人们意识到原命题的荒谬之处,谎言不攻自破,随着反讽效果土崩瓦解。
戏拟与反讽,在王小波杂文中更多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形成“假正经”的叙述语调。且以《拒绝恭维》为例:“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今天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在这段文字中,“最最敬爱的”明显是当时盛行的革命语录,“敛芝麻”则是民间话语,庄重宏大对低俗渺小,明显的悖立性质形成对时代话语的讽刺。而且,汇报者是不识字、连话都不大会说的农民,让政治流行语从他口中自然说出,即为作者对政治口号的戏拟,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汇报人处在自信而无知的状态,汇报时竟然兴奋得连鼻涕都顾不上擦,可见对当时主流话语的自觉依附并以之为荣,构成对当时政治生态的无限反讽。最后,王小波使用“在萧瑟的秋风中”这样正经的开头,贯穿始终的正儿八经的语调,与整段文字表现出的荒诞现实,构成整体上的悖立,可见严肃背后深藏的讽刺与诘问。
总之,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是借戏拟与反讽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堪称语言的艺术。下节继而从语言层面入手,探讨“假正经”腔调在本质上的解构倾向。
二.“假正经”腔调的解构倾向
王尔德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从情感到形式,而是从形式到思想和激情。”[9]这里所说的形式就是语言。语言是作家创作思想、审美情趣、情感蕴藉的直接承担者,语言的选择、讲述的方式是与内容相适应的,并能反作用于表达内容,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具有内容的性质,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艺术,在语言层面就实现其对历史、权力、话语的解构。
第一,“假正经”腔调实现对历史、传统的解构。这里的“历史”和“传统”,既包括了中国古典文明,也延伸至其背后的传统文人心态、生存状况。在王小波的言说里,“假正经”即等于庄严肃穆、了无生趣,他认为中国历史“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在他看来,中国文明形成一种传统模式,人们“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管别人”,钻研精神只会产生学堂式气氛,即“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而这种气氛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高度严肃性,于是“无数的聪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在文学观念上,他尖锐批判“无智无性无趣”的世故说教的中国纯文学,坦陈文学的使命应当是阻止整个社会向无趣发展;在生活观念上,他深深厌恶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磨砺”成没有趣味的“崇高人”的社会现实。不得不提的是,传统里并非不存在“幽默”、“趣味”,却往往是士大夫式的自恋,在本质上是笼子里的自我慰藉,是无我的奴性,千百年来一直重复罢了。总之,王小波的这种“假正经”腔调,通过对历史、传统的戏拟实现对其本身的解构,将一切视为合理的无趣撕裂掉,随之衍生的幽默、趣味,是站在了窒息生命的僵硬教条、虚伪的说教、矫情的对立面,實际已提升到思维的自由、创造、本真状态这样一个高度,走向一个通往未来的无限空间,爆发出醒世的力量,如他所言:“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另外,“历史”和“传统”也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少作家的笔下虽有幽默,文字背后的自我却尚未从“堂皇”的地位跌落下来,居高临下,将读者看作需要启蒙的受众,难免也有故作高深、卖弄学问之嫌,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同时也消解了文人“正襟危坐”的架子。
第二,“假正经”腔调实现对话语、权力的解构。这涉及福柯“话语即权力”命题:“权力是透过话语而运作的某种东西,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策略因素。”[10]“话语”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单纯”,它可以视为古老权力的代名词,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着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在任何特定的场域中都有一套特定的话语形成机制,使得该说的东西得到明确的言说,而不该说的东西则严格地受到排斥。结果导致一种话语的产生,必然以牺牲和剥夺其他的知识话语的资格为代价。”[11]话语的“暴力”就在于它与知识、权力是紧密相关的,王小波对话语极为敏感,源自他的痛苦历史记忆和荒诞生命体验:“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像一池冷水的话语,实际指向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的严肃话语系统。不难想象,主流话语支配着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个领域,一切都是在这套话语设定好的体系内运作。王小波自然看到了人在“话语霸权”下浸入肤髓的思想戕害,呈现出思维方式和整个生命状态的畸形。对主流意识形态,他并未选择直接批判,而是自如地运用他的语言、文学才能,“假正经”腔调即是他充分的语言能力的自我扩张、自我强权的展示,对此有学者指出:“(王小波)打破了掩盖在语言或叙事之上的强权性和贵族性,以此来否定语言的神话,元创作的神话,因而使元创作的中心角色被边缘角色所取代。”[12]当他用戏拟的方式暴露底层百姓对话语极力的依附、蹩脚的模仿,当他将日常生活背景、具体语境纳入主流话语系统而悖立凸显时,虚伪事物的外壳被迅速剥离,假大空的理念从神圣高堂掉了下来,其不合理的一面得以一览无遗,因此在语言层面就实现了解构目的。有人曾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评说王小波的小说,其实他的杂文何尝不是用充满反讽的对比、夸张变形的戏仿而营造出“狂欢化”情境。因此,“假正经”腔调正是王小波解构话语、权力的出发点和手段。甚至可以说,当他能够避开主流话语,用自己的方式发声时,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如他所言:“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
以上论述,可以说明“假正经”腔调对具体历史(凡是过去,都可称为历史)的解构倾向,但也许只能成为“常识性”的解读,尚未触及作者使用这种腔调的本质用意,因为王小波的杂文写作,所指涉的还是一种“元历史”。戴锦华认为,“他所书写与戏仿的并非一段特定的历史;他所拒绝或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自身。”[13]王小波看到了权力轮盘永恒的运转、无所不在,因此他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也有意避免无形之中将自己塑造成真理的化身——也许,他离开学院,与主流文学保持距离,在社会边缘进行写作的行为也可说明这一点。总之,为了不使自己成为面对社会与公众的话语制造者,“假正经”腔调无疑是一种十分智慧的、有利的言说方式,从读者角度而言,在所谓解构式阅读之前,他已经用一种充满戏拟、反讽的有趣书写解构了各种话语、权力模式自身。
三.“假正经”腔调的文体成就
王小波杂文的“假正经”腔调,无疑和他身处的时代、他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语言是他时代诉求的外化,上节的论述不难说明这一点。但倘若只将杂文的语言艺术置于特定的历史中看,就实在“委屈”了这位20世纪中国文学中“特立独行”的天才,他的杂文最具有文学、艺术成就处,恰恰在于超越时代的那部分。他的“假正经”腔调,不仅具有对历史、权力、话语的解构倾向,同时也展现相对独立的文学意义。
文体的确立,可视为王小波杂文抵达文学性的努力。上文已提到“腔调”这个概念,且看高行健的定义:“至于语言的调子(腔调),则建立在字句的感情色彩之上,贯穿于一部作品或部分章节之中,或隽永,或严谨,或幽默……一千个成熟的作家至少有一千种不同的调子,不能找到鲜明而独特的调子的作者是苦恼的。”[14]因此,独特的腔调是一位作家作品风格化、特质化的重要表征,并不夸张地说,这也是衡量作品的语言成熟与否的准绳。由此看王小波的杂文,“假正经”腔调在遣词造句和形态结构之上,呈现出一种独特又相对稳定的情绪气质,李银河曾说:“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15]此种极具有辨识度的文字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其独一无二的“假正经”腔调,这无疑是他的语言才能,他使之不断得到锻炼,以达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事实上,“腔调”之于杂文尤为重要,从区分文体标志的角度看:情节之于小说,分行之于诗,对白之于戏剧,都可视为文体得以确立的显著的外部标志,显然杂文并不具备此种标志,致使其与散文、随笔乃至其他一切言论性文字的界限模糊不清,所以,杂文唯有借助“叙述语调”,才能使自身与其他文体区分开来。
当然,语言的调子本身远不足使杂文自成一格,将王小波置于与他同时期的作家中相比较,“假正经”腔调的无可替代性、成就不难彰显:“机敏”、“幽默感”在九十年代杂文中并不缺乏,却多流于无聊的噱头、油滑的调侃,如林贤治所言:“在九十年代,甚至因此酿成一种可恶的风气。幽默而可恶,就因为没有道义感,甚至反道义。”[16]杂文归根到底是以议论和批评为目的的文体,放眼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杂文自鲁迅始,林贤治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写作,是对鲁迅有意或无意的承续:“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惟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难以替代的。”[17]由此可知,杂文若要成其博大与深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必须具备内在品格,即针砭时弊、关切民生、追求真理的道义与使命。“假正经”腔调的卓异之处,在于以“幽默感”引起读者的警觉,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展现一种“审智”意识的自觉。而语言的处理又十分得当,避免读者对戏拟、反讽造成误读(例如,将反用的“假正经”当成真的“假正经”)。
综上,“假正经”腔调的文体成就,首先体现于其独特鲜明又相对稳定成熟的语言,并且在外部标志上使杂文文体得以确立,更重要的是,将道义感与幽默感两相结合,从审美走向审智,最终使王小波杂文自成一格,在文学史中得以“沉淀”。
回到王小波自身,其对杂文写作的文体问题十分重视,他坦言“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又追求“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从《我的师承》中的这句话,可见他对杂文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洞察:“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他对杂文文体的自觉追求,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在“假正经”腔调中合而为一。
最后,本文将“假正经”腔调置于王小波的杂文写作历程中,探讨其在后期面临的困境:内在生命力不断消亡的问题。王小波曾自得于以沉默面对社会,在偏离“话语”中形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当他无法再保持沉默,必须用“话语”面对社会时,他借助“假正经”腔调,竭力消除言说本身可能形成的“话语制造者”的痕迹——反讽与戏拟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形式(上节已论及),以此面对主流话语和严肃精神的合围,用他的话说即“跳出手掌心”,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谋取也不代表任何权力话语。然而王小波毕竟无法阻止读者、社会对他的接受态度,不觉间自己还是成为面对大众的“话语制造者”。更重要的是,“跳出手掌心”(意即跳出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予自己的一切)提供一种解放、逃逸,但不提供支撑,因而“假正经”腔调显现的只是被主流话语和严肃精神所遮没的边缘的生存,在“对立”中其生命力才得以维持(况且,即使对传统进行戏拟,首先也要借助这种言说方式的合法性)。他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新的理论支撑的架构,1996年底,他被自己无法再超越的言说困境控制了,进入一个无法突破的叙述层面,或者说由悖论组成的圆圈。这种极度的精神空虚,与他当时疾病的加剧不无关系。
四.结语
从目前王小波研究来看,“重小说、轻杂文;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轻文体”已成不争的事实,甚至因其“超文学”的影响力,作品的“文学性”反成争议的话题。现代杂文自鲁迅始,其批判性、启蒙性、思想性广受关注,而文学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杂文能否视为一种独立文体、艺术作品,至今未有一致答案,杂文的边界也因此模糊不清。发现王小波杂文的语言艺术,是为本文希冀对王小波研究、杂文研究尽绵薄之力。不得不提,王小波杂文还展现一种诗化的语言(内在韵律与节奏美感)、诗性的语言(诗性思维、诗性情感、浪漫情怀),更接近文学的独立性与完整性,笔者在此提出,留待未来探讨。
参考文献
[1][13]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J].当代作家评论,1998(2):34,27.
[2]葛维樱,武鹏,陈超.王小波艰辛的成名[A].王小波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59.
[3]李银河,韩袁红,藏策.关于王小波的对话[A].王小波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
[4]兰晓胜.王小波杂文修辞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16.
[5][8][16][17]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J].书屋,2000(3):57,57,57,57.
[6]梁培先.“戏拟”与“颠覆”——“学院派”与民间书风的本质比较[J].中国书画,2005(3):10.
[7]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序[A].王小波全集.第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3.
[9]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A].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74-175.
[10]冯俊.后现代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78.
[11][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0.
[12]王绯.文学调侃:集体仿同与“反堂皇”仪式[J].当代作家评论,1999(6):104.
[14]高行健.现代文学语言[A].现代小说技巧初探[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62.
[15]李銀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A].王小波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60.
(作者介绍:顾绅楠,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