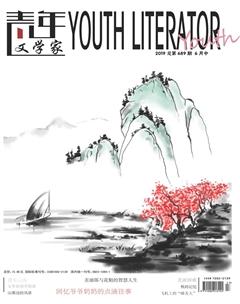吾心安放于自然
高方圆
摘要:华兹华斯作为杰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一直都是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他自己也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的主张,华兹华斯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对抗新古典主义,倡导大家回归到自然,从自然界和普通大众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哲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不仅是热爱自然,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又应该如何和谐平等地相处。华兹华斯从观察儿童出发,提出“儿童即成人”,人只有保持童心,才能融入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华兹华斯认为只有大家认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获得智慧、力量和幸福。
关键词:自然;童心;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146-03
序言:
华兹华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被冠以“湖畔诗人”和“桂冠诗人”,他被雪莱称作为“自然的歌手”。他热爱自然,从自然之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写诗风格。在自然之中,华兹华斯寻找快乐,治愈心灵,同时感悟人与自然的生存发展的奥秘。华兹华斯对自然里的一花一木都饱含深情,回到自然就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他独特的“自然观”也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华兹华斯通过书写自然不仅是对自己的心靈治愈,也是在对人类进行心灵救赎,更是给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花木皆有情一回归自然,找寻快乐
华兹华斯的诗歌大多都是对自然的歌颂,在这位浪漫的诗人眼中,万物都有灵性,花草树木这些看似静态的植物,也都被诗人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咏水仙花》是诗人描绘自然的代表作之一,诗人在观察和捕写水仙花的过程中,也表达了对自然独特的感情。
在首段展现了一幅“我”与自然近距离接触的画面,“我独自漫步如浮云,在青山翠谷上飘荡”。(黄杲忻256)我们可以看出,在诗的开篇,诗人用到了“孤独地”(lonely)这样的词汇,说明诗人在回归田野之前,虽有姊妹爱人陪伴自己,诗人的内心深处仍没安放之处,十分孤独落寞。紧接着诗人就描绘到水仙花,诗人在一瞬间(all at once)发现了绽放着的水仙花,“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它们在那湖边的树荫里,在阵阵微风中舞姿飘逸”。水仙花在光影里,湖岸边盛开的场景正是诗人一直热爱的自然的模样。“象银河的繁星连绵不断,辉映着夜空,时暗时亮,水仙就沿着湖湾的岸边,黄灿灿的一片伸向前方。”(黄杲忻256)[1]这句诗中,水仙花被诗人比做成银河里的繁星,眼前的水仙花对于诗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盛开在自然的鲜花,也是生命的象征。诗人本人也说过,“人于自然根本相互适应,人的心灵能映射出自然界中最美、最具有趣味的东西”。(刘若瑞70)[2]正是因为热爱自然,向往自然,诗人才将自己所见之景幻化于心,并有了非常快乐和美妙的情感体验。
诗人越来越走近大自然,心情也回归孩性般的天真与活泼,“水波在边上欢舞,但水仙比闪亮的水波舞得更乐,有这样快乐的朋友作伴,诗人的心儿被欢愉充塞”[3](黄杲忻256)。在诗人心中,水仙花从生长在田野间的花儿变得灵动起来,她是大自然的象征,是生命的象征,她充满灵气的模样给诗人带来了欢乐和慰藉,诗人将其看成是陪伴自己的“伙伴”。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的原本落寞寂寥的心情也如同摇曳在风中的水仙花一样变得炊快活泼起来,这种内心的欢愉和自在是诗人在重返自然后重新获得的,从诗的最后也可以看出来,诗人说到:“这水仙花常在我眼前闪现,把孤寂的我带进了天堂,这时我的心被炊乐充满,还随着那水仙起舞翩翩。”(黄杲忻257)。
诗人即使是离开此地继续远行,也会将他此刻经历的那份来自自然的美好和欢乐藏置心中,这是自然给予诗人的力量。从诗人别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比如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诗人也强调如果我们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就必须回到自然去激发自己的灵感,抒发出自己最真挚的感情,而不是简简单单寻找“并不强烈的刺激”。诗人看到水仙花,感受到了快乐,轻松以及生命的美好,而这些都是从自然之中获得的,自然给予了诗人想象,灵感和继续前行的力量。
二、性本爱丘山一重回旧地,治愈心灵
华兹华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其带来的负而效应就是人们开始远离自然,农民走进城市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底层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窘迫。在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是对年轻的学者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年轻的华兹华斯也投身革命之中,试图去为人类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去奋斗。但是革命却受到了镇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也使华兹华斯对革命产生了幻灭感,自己追求的信仰成了非现实性的乌托邦。
诗人在亲身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他痛斥资本化和物质化的社会,感叹“早晚之营求和消耗而耗尽毕生的精力”,“为了卑污的利禄把心灵出卖”[4](杨德豫131)。此刻诗人的心境不仅仅是个人孤单和落寞,还有对人民和社会的关心,他越来越坚信只有自然可以救赎人们被工业和物质社会毒害的心灵,他也相信自然可以治愈自己和世间万物的创伤,给饱受苦难和束缚的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也是在《丁登寺》中,诗人提出了自己是大自然的“崇拜者”,自然是人类心灵的护士、向导和监护人。
当华兹华斯五年后回到丁登寺的时候,他内心充满感慨。《丁登寺》中充满了诗人内心的各种抗争和比较,在诗歌的开篇,诗人就写到“五年过去了;五度炎夏还加上五个漫长的冬天!我又再一次听见这水声”,诗人重新回到旧地,过去的经历与眼前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但是自然界中的“山泉”“危崖陡壁”“村舍院落”和“森森的果园”都让诗人年轻但饱经风霜的心灵得到了治愈,诗人在丁登寺旁看到了那些未受工业文明破坏的原始的村庄和田园,安静与祥和,在《丁登寺》里诗人也提到“这些美丽的景象在我的长久别离中,对我来说,并不像盲人眼前的风景那样。而在城镇和都市的喧闹声里,在我困乏地独处屋中的时候,这些景致会给我甜美的感觉”,[5](黄杲忻77)“会使我的血脉和顺、心头舒畅;它们进入我心灵深处,使那些沉睡着的往日欢乐感情开始渐渐地苏醒”,[6](黄杲忻83)这些诗句都充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之情,在他重新返回这片属于他自己心灵的家园时,他被金钱和物质社会伤害的心灵逐渐被自然的宁静和祥和而治愈,而属于他的那份快乐和自在也被自然唤醒,痛苦的感觉也消失了。与《咏水仙》一诗不同的是,《丁登寺》中的自然对于诗人心灵的治愈和保护作用更加明显,诗人多用“血脉顺畅”,“心头舒畅”“甜美”这样的词语来直接和强烈地表达出自己回到自然后的感受,而非单纯描绘白然的美景。
诗人在《丁登寺》里也提及“我在精神上多少次求助于你!穿过树林蜿蜒去的葳河啊,我的灵魂曾多少次求助于你!”[7](黄杲忻79)诗人在远离城市的各种喧嚣嘈杂后,终于又在丁登寺寻觅到了治愈内心的良药,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诗人自己也在这五年的时光里改变了许多,经历了世事的锤炼和打磨,但是在诗人又一次回到故地的时候,诗人还是被欣欣向荣的树木,郁郁青青的草原,曲折蜿蜒的山脉,重新找回了自我和天性。在《丁登寺》的最后,诗人又一次提到他对自然的崇拜和信仰,他说“而我这大自然的崇拜者,精神抖擞地来到这里朝拜;或者说我来这里时怀着更热烈的爱啊,是更圣洁的爱”[8](黄杲忻82)诗人也是通过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直接地表达了自我的情绪,抒发出他内心对自然的热爱,以及自然带给他的激动的感情。诗人此刻不仅仅是回到自然,更像是一个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获得安慰和安全感。“诗人与自然之间可以产生那样亲密的交流,也是由于诗人将自然看成母亲。自然母亲自始至终都在哺育诗人的灵魂,给他安慰和力量”。[9](王萍)这时的诗人远离城市和社会文明,奔向自然,和自然合二为一。也正是因为诗人自己在自然之中获得了快乐,欢愉以及治愈,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美好,他才会呼唤众人回归到原始的自然,亲近自然,治愈心扉,找回欢乐和本性。
三、人在天地间一初心不泯,天人合一
作为诗人,华兹华斯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诗风格和诗歌理论。诗人热爱自然里万物生灵,也将自己看成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一方面,诗人在肉眼可见的自然界中去观察万物,接受来自自然给予他情感方面的滋养和熏陶,这种情感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激发出诗人写诗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另一方面,诗人也是将自然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治愈心灵的良药,结合自身经历和思考,关注人如何生存和发展,人该如何维护和处理自身和自然的关系。
从《咏水仙花》,《彩虹》和《丁登寺》中我们都能看到,诗人虽然描写的全是自然景物,但是总会在诗的中间和结尾处提及他与自然的关系。
诗人在描写自然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盲目崇拜自然风光,他探寻到人本身和人的存在。诗人关注自然风光,也关注人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发现诗人除了写抒情诗歌,还会有很多儿童诗歌,比如诗人在《永生的信息》中,歌唱并赞美儿童对这世间万物寻根求底的天性。华兹华斯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点放到人性之初——儿童时期,在《彩虹》一诗中,诗人就提到“一见彩虹挂上天庭,我的心儿就欢跳不停”“儿童是成人的父亲,愿这情愫依旧,直至我老态龙钟”。[10]而“儿童是成人的父亲”这句话含有这样的意味,崔莉(“重返自然的桥梁 试析华兹华斯的儿童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提到即儿童是在自然界是超越成人的地位的,因为儿童阶段作为人性成长之初,受到外界的影响最小,想法最简单和质朴,而他们的内心也是最容易受到自然的教化和熏陶,更能和自然自由地相处并融入其中,故成人也应该和孩子样,恢复其天真的本性,有“寻根”和“归家”心态,这是解决人类文明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11]。这种和谐的相处方式是诗人所向往的,他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人如何保持这样的相处模式,可以一直与自然和谐地相处下去,实现持久的发展。
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诗人一直向往的也是平等、自由與和谐的生存模式,华兹华斯的自然观立足于人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是人性、理性与神性的结合体,实际上这“三位一体”也是人的最高属性。人和人应该遵循这样的价值观,人与自然更应该平等和谐。诗人在描写自然时,将自然之景以及自己对自然的感情都呈现在他所写的诗歌之中,将这些有形存在的幻化成无形的精神信仰,并将自己和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整体。在诗人眼里一个人若善于凝神观察,他就能意识到无尚的存在,感觉到整体的存在[12] (Hutchion,Thomas)。这种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而想要获得这样的力量,人和自然得合二为一,达到天地共生。在诗人看来,人只有有纯真善良的童心才能真正融入自然之中去,也才能和自然达到合二为一的理想状态。因为儿童在诗人心中是人性完美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儿童成了成人、人类的父亲,也是人与自然沟通的重要桥梁,而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也处处流露出儿童所具有的“童真”“善良”“简单”的阶段特征。诗人爱自然,爱人类,所以希望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并存,在文明社会也要保持着对自然的虔诚,这是诗人的理念,也是人想要走出文明困境,是解决与自然冲突的最好的办法。
结语:
华兹华斯作为浪漫主义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抒写和刻画自然之景。每当诗人回归田野山间,诗人的内心就会被自然的纯净和美好所唤醒,诗人也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中之中流连忘返,忘记城市的喧嚣和吵闹,找寻欢乐和自我,治愈心灵的创伤。诗人也发现只有自然可以启迪人类的智慧,净化人类的思想,触发人类的激情,孕育出“追求崇高理想的信念和向往理想境界的心态”[13](刘宝安)。
诗人结合自己的主观体验,创作出抒情诗歌,通过诗歌来描绘出自然的美景和自然的力量,以此来呼唤大家回到大自然,融入自然。虽然诗人在《丁登寺》中曾说自己是自然的信仰者,但从诗人所写的诸多诗歌来看,诗人不单单只是向往和追随自然,他关注自然美景的同时,也注重人在自然里的主观感受。在诗人心中,人性和自然同样重要,所以他向往和崇拜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的一种宁静又和谐的存在方式。身处一个商业社会的诗人,他感受到人们受到来自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对人本身的消极影响。他希望通过创作诗歌来呼唤人们走近自然,从大自然和人的纯真之初来寻找启蒙,从而治愈人们的心灵,这样人和自然才可以平等和谐地共处,也是解决人类文明发展的困境的重要途径。
注释:
[1]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56页。
[2]刘若瑞:《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中见《抒情歌谣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70页。
[3]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56页。
[4]《世事让我们过分劳心》杨德豫:华兹华斯诗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131页。
[5]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77页。
[6]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83页。
[7]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果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79页。
[8]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果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82页。
[9]王萍.从“人性自然”到“神性自然”——华兹华斯的人生哲思与其自然观的嬗变[J].文艺争鸣,2017 (01):169-173。
[10]此句引用于《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果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82页。
[11]原文中作者是说作为“一种相似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既连接着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形态,同时又蕴藏着相近的精神追求,反映了一种真诚的‘追根意识一种执着的‘归家心态,而且它作为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理想途径之一,对未来的人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崔莉:“重返自然的桥梁一一试析华兹华斯的儿童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25页。
[12]Hutchion. Thomas: 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Wordsworth. London: Society of Promoting ChristianKnowledge.1910:234.
[13]刘宝安:“大自然的歌手——论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和自然诗及其贡献”,外语教学,2003年第3期,第91页。
参考文献:
[1]Hutchion,Thomas. (ed). 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Wordsworth. London: SocietV of Promoting ChristianKnowledge,1910:234.
[2]Percy Bysshe Shelly. To Wordsworth in The Complete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y,ed. Thomas Hutchis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3]劉若瑞:《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中见《抒情歌谣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70页。
[4]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刘宝安:“大自然的歌手——论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和自然诗及其贡献”,外语教学,2003年第3期,第91页。
[6]崔莉:“重返自然的桥梁一一试析华兹华斯的儿童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25页。
[7]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杨德豫:华兹华斯诗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131页。
[9]王萍:从“人性自然”到“神性自然”——华兹华斯的人生哲思与其自然观的嬗变,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第169页-173页。
[10]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65页。
[11]伍蠡甫,胡经之: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1800年版)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