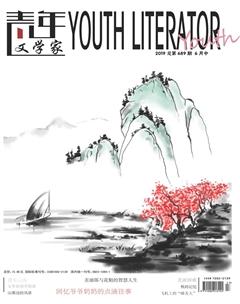蒲松龄、吴敬梓关于科举雅俗观的差异比较
赵欣雨
摘要: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均不同程度地对科举进行批判,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关于科举的雅俗观。蒲松龄批判的主要为考官、考场等制度漏洞,认为科举尚“良药可医”;而吴敬梓则更为彻底地看到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作出“无药可救”之判断。根据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以及其言行,可对人物进行雅俗定性,进而可对科举制度作出雅俗判断,即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的差别。
关键词:蒲松龄;吴敬梓;科举;雅俗观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101-01
雅俗观是历代文人学士们鉴赏文学作品并进行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将雅俗观的概念引入,分析两部作品各类人物形象,从作者对人物的讽刺抑或是赞扬态度,可对人物进行雅俗定性。当雅俗评判视野从人物推及到科举制度,即可看出两位作者隐含着地针对科举雅俗观的异同,从而构成一个隐性价值评价体系。
首先,在对科举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雅俗定性时,从科举的目的与行为上分析,“功名富贵”作为最直接、最明显的目的,不得不成为探究焦点,二者在而对“功名富贵”二字时,吴敬梓雅俗观明确,而蒲松龄则显得较为模糊与笼统。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1],吴敬梓正足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评价书中人物。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敬梓文中所提到并多次批判的功名富贵实际上带着一个限定词,即“无文行出处”的功名富贵。吴敬梓对于功名富贵有着泾渭分明的态度,即讲求文行出处去追求功名,不失为一种符合儒家提倡的“雅人”,相反,则为一种“大俗人”,书中对后者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刻画与批判。
与吴敬梓泾渭分明地对功名富贵雅俗判断相比,蒲松龄的雅俗观更加模糊与笼统。他没有看到“有无文行出处”这一方面,因此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并不像吴敬梓那样具有明确性,而是通通默许其合理性,将其看做贫困书生摆脱现状而进行的积极努力,似乎隐含着一丝“雅”的意味。《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批极度贫寒的学子形象,而蒲松龄对其也具有同情态度,同时他们身上也具有蒲松龄本人影子。所以贫苦书生借助科举力量去求得功名,进而获得富贵改变目前所处困境,这是一条合理的可行之路,并不去分析在科举過程中以及在获得功名富贵后,是否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道义,所以其雅俗观并不明确,而是一概而论,并似乎偏向于“雅”的方而。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因为二者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呈现明显的差别,所以进一步推及对于科举制度本身的雅俗定性上,蒲松龄与吴敬梓二者就有不同的观点。二者在对科举是雅制还是俗制这个问题上的不同: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
蒲松龄认为科举制度实质上尚为一种“雅制”,仍然为广大贫寒书生们提供一条通往上层的路,而之所以这条仕进之路困难、黑暗,就是因为不正学官等“俗人”进入体制内,从而让科举制蒙上了一层薄雾。蒲松龄在其作品《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失意苦闷的书生,也塑造了一批通过科举顺利走上仕途,获得功名富贵的成功形象。《阿宝》的男主人公孙子楚情痴得到了心仪女子阿宝的爱情,同时也因为自己书痴而使自己中得进士,供职翰林院,并获得皇帝赏识与夸赞,可谓是通过科举走上了成功人生。可见,从书中塑造的一个个成功书生形象可以看出,蒲松龄认为科举制度虽然有缺点,但是不失为“雅制”。吴敬梓看清八股取士实质,对其全然否定,因此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彻底地“俗制”,而且已经成为社会“俗化门”,“雅人”如果不避“俗制”,就会被俗化。匡超人就是一个鲜明例子。他出场就是一位勤学且孝顺的书生形象,在获得马纯上帮助见到父亲后,尽心照顾父亲同时也不忘读书到四更。而当匡超人走上科举路后,竞为了获得钱财行违法之事,包揽词讼、伪造文书、冒名替考,全然将其父亲死前“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的遗言抛到脑后。匡超人从一名理想“雅人”,经科举这道“俗化门”门,全然俗化成一名彻底地儒林恶少,可看吴敬梓认为科举为彻底“俗制”,对其无丝毫赞赏之意。
结语:总的来说,蒲松龄、吴敬梓二人关于科举的雅俗观和他们对于科举制度的看法是紧密相关的,对于科举的态度是作者进行雅俗评判的主要依据,同样也是科举雅俗观的形成基础;而作者对科举的雅俗观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科举的态度,双方是一种动态交流的过程。吴敬梓对科举作出“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的评判差别,认为无文行出处地追求功名为大俗,更为赞赏抛弃科举、辞官归隐的雅士行为,而蒲松龄则对科举雅俗观的表达较为模糊。
注释:
[1][清]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序;王丽文校点:《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华书局,1962年。
[2]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崔宏伟:《(聊斋)与(儒林外史)批判科举制度的不同》,《文学教育》,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