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学写作的流行及困境
本刊记者_高洪云

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阿什河公社,一位贫农女青年在对敌斗争大会上批判一位“漏划富农分子”_李振盛摄
“文革时拍普通百姓的生活,拍得太少”
国庆节前,笔者去了趟建川博物馆聚落。参观的第一个馆,是李振盛摄影博物馆。
李振盛生于1940年,可谓见证了新中国的整个发展历程。他在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1988年,因20幅文革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文革”期间,他拍摄了近十万张影像资料,其中有近两万张涉及当时发生的混乱惨剧:批斗、抄家、戴高帽、刑场处决
这些照片,是他于1968年10月偷偷藏在地板下才得以保存的。他认为,“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历史可以“忠实”记录吗?中国古代一直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
近些年,口述史很流行。但在李振盛看来,记忆太不可靠,有些人靠口述历史来洗白、洗红、拔高自己。
照片呢?几乎照相机发明开始,也可以篡改。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修改照片更是轻而易举。而更重要的,其实照片也只是记录一种视角。
李振盛因《红色新闻兵》广为人知,也因此被标签化了。这促使他反思。
2016年5月,他接受媒体采访时,遗憾表示,自己在文革时,拍普通百姓的生活太少了——结果好像净是些符号。“要是有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家里喝酒、朋友聊天……靠服装、周边的装饰,(让)人们能感觉到这是文革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别强调文革符号。”历史太复杂,存在各个人群的生活和视角。
这个遗憾,他在香港回归时弥补了,7月1日当天,他有意识地抓摄普通的东西:老人遛鸟,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看报、睡觉……
李振盛的反思,值得玩味。他作品里的文革,看起来是狂热的,残酷的,匪夷所思的。他也意识到,仅仅展示这些政治事件及意识形态,读者若以此来悬想或解读历史,是否会失之简单。

中国历史的真正传统是国家有国史,地方有方志,家族有家谱
文革充满悲剧,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言,“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新华社,2019年9月28日),但仅仅是悲剧,并不足以构成生活和时代。本刊2019年9月号封面报道人物温铁军,正是从文革时的知青生活开始,“是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成为他不断推进乡建的精神动因。他在《八次危机》中详细分析了那段悲剧的原因。工业化受挫,城市经济危机,大量人口失业,只能依靠“上山下乡”转到农村。这是一段悲剧,但也正是其间亿万普通人的努力,奠定了改革开放得以依赖的重工业基础。
被李振盛照片忽视的,同样能构成另一个“文革”,这或许正如人们在刚刚过去的70周年大庆群众游行方队中看到的“建国创业”。
生活的历史,是普通人的礼乐风景
传统史书,新文化运动以来,被人诟病最多的,“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叙述的事件,往往是历史大势。
但事实上,这并非是中国历史的真正传统。中国历史,国家有国史,地方有方志,家族有家谱,都是历史,正如国家有宗庙,地方有社稷,宗庙有祠堂,原本代表着不同的教育功能。
这正如诗经的“风雅颂”。而民国史家刘咸炘先生统称为“风”。在他看来,史学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察势观风,“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这样的风,有上下,有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代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重“时风”。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
孔子作《春秋》,国史的传统精神是拨乱反正,记载的都是大事件,正如司马迁在《史记》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方志的精神则与国史不同,方志看的是一个地方的人们,具体而微的生活,是普通人的礼乐风景。而在此之下,更有大量的文人笔记、野史小说,其实都属于民间生活的“风”。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随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占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类似中国方志的微观史学、新文化史也逐渐兴起,开始体现较平等或平民的史学关怀。
微观史学,研究对象多为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段时期、一种组织或制度等,侧重于阐述史实,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局部的和专门的。譬如“论明代内阁制度”“论汉武帝削藩”或“论美国内战原因”这类题目,均属微观史学。近几十年来更扩及普通人的生活。
新文化史学,又称社会文化史,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在研究方法上,从因果联系的分析转向文化阐释;在研究主题上,放弃了或政治或经济或心态观念的单一形象,转而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
这期间诞生的著名作品有很多,比如微观史学的三部代表作——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及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
这种史学观念的兴起,让人联想起印度思想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那句著名质疑:“底层人能说话吗?”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受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影响。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文化霸权,革命党得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这自然要求知识分子去关注平民及其日常生活。
汤普逊(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并非源于产业工人,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才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学科之间,新文化史也受人类学启发。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ord Geertz)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及论文集《文化的阐释》。其中他写到巴里斗鸡,背后是男人间的搏斗,村民不把赌金押在对立宗族或外村的鸡上,斗鸡就像“显微镜”,让人看到彼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样态。
在微观史学领域,金兹伯格的尝试,被视为带有反驳法国“年鉴”学派掀起的计量史潮流的理论指向。
他的《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被视为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研究的是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村一位有文化的农民,质疑上帝造人,被宗教法庭起诉,后被处死。作者通过探究这个小人物的阅读、交际、心灵活动,来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展示彼时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达顿(BobertDarnton)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从民间故事、手工工匠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来信等,研究社会与文化。
最有趣的是第二章,一个印刷工学徒,日常生活无聊,酗酒成性,时有暴力行为。他不满师母的宠物猫,吃得比他好,于是虐猫。但此行为有深厚文化渊源,当时法国有虐猫民俗,且猫在法国大众文化中与巫术有涉,故而民间有祓除猫魔的仪式,甚至有人在新房竣工时,把活猫封在墙壁里避邪。此外,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通过一个小工人虐杀女主人的猫,文化风俗、贫富阶级、反抗、猎杀女巫等诸多议题,被勾连起来。
但正如我们开篇提出的疑问,这样的研究又是否足够真正表达普通群众生活的样态呢?还是常常只是流于一种猎奇和想象?
中国微观史学创作
上文例举的著作或论文,可看出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研究风格。海内外学者,也用此类视角,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
提出大历史观的黄仁宇,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万历十五年》,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即1587年是“没有意义、不太重要的一年”,研究方式可谓微观式的,但聚焦的仍是帝王、高员、大文人,跟平民或大众生活无涉。
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就典型得多,讲的是山东郯城农村有一妇人王氏,与人私奔,没活路了不得不返家,丈夫在一个雪夜将她掐死,并嫁祸邻人,最终知县黄六鸿侦破疑案。史氏的资料来源主要为《郯城县志》、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以及《聊斋志异》等资料,然后用虚构的文学手法,来复现几百年前一个村庄的社会和生活,以及妇女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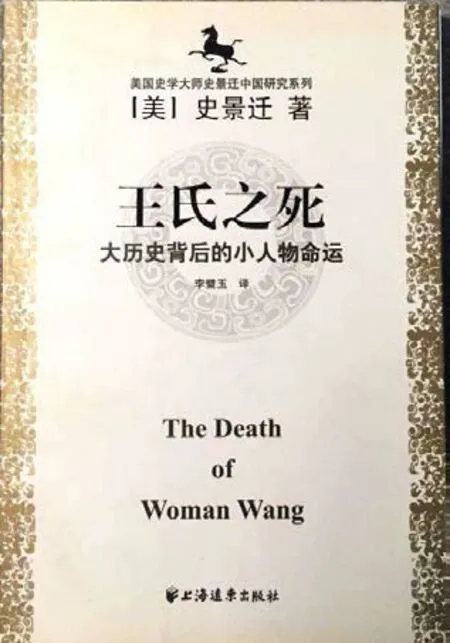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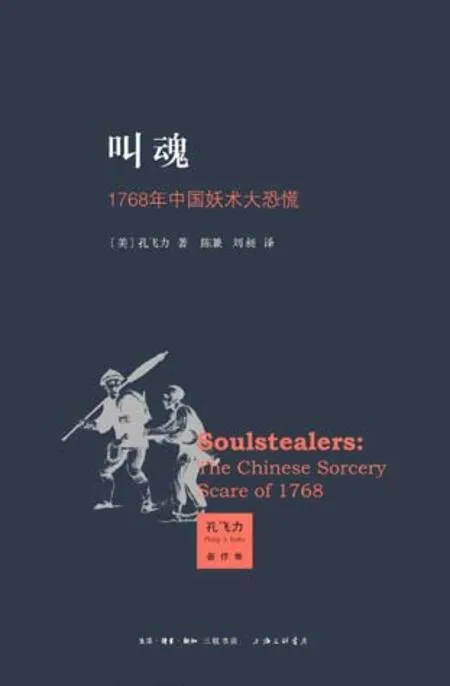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用微观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
西方人用微观史学书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不胜枚举,像孔飞力的《叫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都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
尤其是“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更是洋洋大观,涉及层面极广,如《闺塾师》《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国善书研究》《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等等。
国内历史学者中,王笛被称为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有《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
这些书,突出的特点是有细节、有故事,关注平凡人。人类需要故事,平民为主角,能降低读者的疏离感,从这些作品中,能更加熟悉祖辈生活的年代。
《袍哥》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微观史学的首部作品,中国版的《马丁•盖尔归来》。该书不是泛泛地谈整个四川地区的袍哥,而是聚焦于成都近郊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文中诸多叙事线条,最核心的一条是围绕三个人,袍哥雷明远,做田野调查的燕京大学女学生沈宝媛,以及作者王笛。乡村建设、抗战,袍哥的家庭生活等,被立体地展现出来。

历史学者王笛,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我想通过一个小人物、一个家庭、一些日常行为的研究,反观整个时代的变化。虽然不能说达到了最理想的结果,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背后,是王笛的历史观,在《时间•空间•书写》中,他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
但也正如作品引发的争议,主要在材料上。原始材料为一篇2万字的论文,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沈宝媛于1945年和1946年,在成都郊区做田野调查而写就的。但《袍哥》一书20万字,王笛征引了253篇中文资料,118篇外文资料。纵观全书,充斥着作者本人的想象和推测,“替传主抒情、代言”,更接近于话本小说。
在这里,我们要询问的问题,或许已不再是它是否足够真实的还原,而是:微观历史的写作到底是为了复原一个时代的想象,还是其他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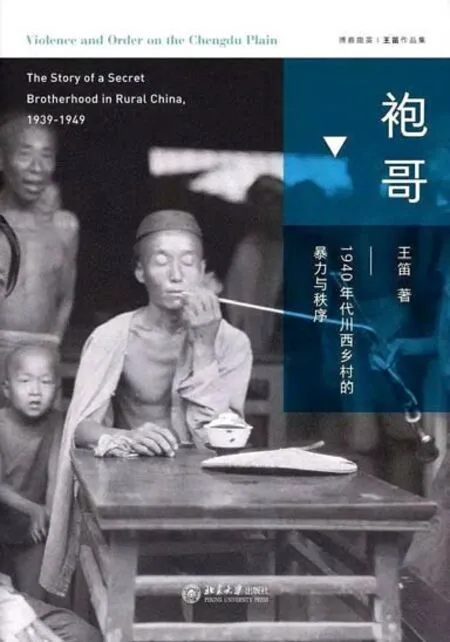
有评论指出,王笛的《袍哥》是中国微观史学的首部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