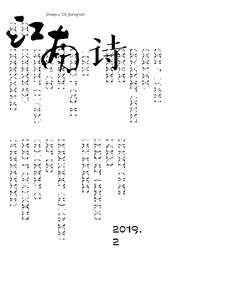父亲的蓑衣
清晨,车过德州见窗外有感
天地清朗,可惜那些人不愿醒来
我贴着车窗往外看
广袤世界里只有一棵树,一只飞鸟
一条蜿蜒的铁轨,还有一位
刚刚熬过这个夜晚的妇人
没有别的了,这是山东省
我曾经无数次憧憬着的那些事物
现在成为单数,但如此神奇
它们孤立、无边,甚至转眼即逝
我却偷偷爱着,并以此为见证
过了德州,廊道里有人举起了相机
那被征服的土地定然留下
剪影,可是,在更为遥远的地方
我的亲人都住在风里
他们长白发,世间竟无人提起
清晨,我所知道的山河都如此寂静
这趟火车偶尔发出轰鸣,于拐弯处
在地理所能拼接的地方
每一副身体都在摇摆
有迷失的表情,亦有黯然神傷的痛
在乡下看木偶戏,忽遇大雨
冬青树有它的去处,草垛也有
一群人要比它们复杂
他们围在一起看戏,看那晃动的木偶
以谁也不能触碰的方式
依偎,对抗,走完自己的一生
可是,突然间降下一场大雨
椅子全空了,场地上只有一个孩子
他要追赶脱手的气球
父辈们曾经都这样,痴迷于
那在内心无比祥和的事物
这就是村落,我躲在泥墙下
脑海扑腾着纸做的脸孔
有时在台上,有时却飘飘乎乎
树叶遮挡过他们的眼睛
而大雨,未来时,已覆盖了他们
接下来的演出也不知要到何年何日
这些回到黑瓦房里的乡民
他们将以时间也不能收存的方式
把木偶遗忘,在雨里
在成片新长出叶子的冬青树中
我听见有人正大声呼喊着什么
道路是旧时的道路,前行中的板车
拉着一位年老的母亲
她要赶来看戏,可雨幕庞大
谁也无法给她带去散场的消息
井然有序
出生那一天起,世界就这样
太小的东西要把它撑大,过高了
就要让它变矮。那个正在修剪枝叶的人
也这么想,从一棵盆景
到繁密的树,该剪的就剪掉
免得横生枝杈。接下来或许是身体
种族,国家,要井然有序
不能有多余的气味。我母亲说
这世间所有有着统一形状的东西
都不会是天然的,自愿的
问日月,它们不明白;问风
风已吹过异乡。那个正在修剪枝叶的人
此刻,他的工具已收藏腰间
地上是断枝和碎叶
心想,几十年都过去了
我现在到底像谁?看上去
有模有样,晨光中可与善者同行
黑夜里,又偷偷长着坏心眼
最为糟糕的是,每次走进人群当中
我就会想起那把大剪刀
一些人已倒下,而我左躲右闪
感觉就剩下那副坚硬的骨头
父亲的蓑衣
与母亲聊天时谈起那件蓑衣
父亲用它挡雨,劳作于丝瓜架下
他头上的斗笠在闪电中
有着最亮的轮廓
而那棕片包裹着的肉身
要大于闪电,漫溢着植物般的气味
蓑衣的下摆悬挂着满满的水珠
父亲从不抖落,他始终深信不疑
上苍的恩泽,有时
恰恰就投射于那小小的依附
母亲说那些年的丝瓜花
多么密集香艳,黄到灿烂时
父亲就会揉揉眼睛,他并不想
触碰什么,哪怕满园的蜂蝶
已从瓜架飞入他的心尖
我承认,我并不了解蓑衣
就像我不了解父亲在雨中的那份
执念:那贴伏着泥土却又能
从闪电中摸出骨头的
存在感、那镌刻于天幕却从未
收回底迹的夙愿,正是它
使我安康,得以完整
我和我的时代
我和我的时代,只有一段距离
是飞鸟与翅膀的距离,是
波光与河流的距离;与此同时
它也是,街角那个卷缩着的乞丐与黑夜的
距离,那个黑夜与富人手心里把玩着的
从古玩店淘来的一粒顽石的距离
山 中
那座山已经不在山中
我一个人,把它搬进自己的身体
树木开始疯长,我即将悬空
不知名的鸟儿全躲在枝杈里
它们用同一种眼神,静静看着我
从骨架里抻出亮晶晶的翅膀
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座更高的山
山中只有一个猎人,他已等了很久
我一出现,他就安然地离开人世
作者简介:俞昌雄,72年生,福建霞浦人,作品散见于《诗刊》《十月》《人民文学》等200余种报刊杂志,作品入选百余种选集,参加诗刊社第26届青春诗会,曾获“2003新诗歌年度奖”、“井秋峰短诗奖”、“中国红高梁诗歌奖”等多种奖项,现居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