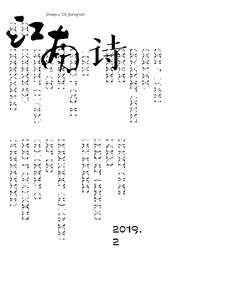在湖水边缘
彭杰
那还是在两年多前,我刚上大学,写一些只有引入死亡才能表现出一副深刻样子的诗。彼时我的诗歌写作似乎在生活层次又或者文本本身上,都显得可有可无。前者其实并不重要,在大学前一年里,我在家乡的一所封闭式中学复读。中学每个月有两天假期,每天七点早读,十一点结束晚自习,平时禁止任何学生出门。我在那年里基本每天要写一首诗,但从没有发给其他人看过,写作中因他人承认才具备的价值并不是必要的。在大学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让我困扰的是怎样让每一次立足于文本的写作都具备意义。
大学旁边不远有一个湖,也就是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很少去刻意避开的翡翠湖。翡翠湖位于合肥西南,是一个花两小时就可以绕完的小湖。在我的许多诗中,它是一个能够承载语言内部修辞的涟漪反复从水面上涌现、扩散并在触及湖岸时反弹回来,并与向外的力再一次交织,产生一种向上的通道的装置。
在学校的西门附近,有一条人不算少而又很狭窄的小道。因校区建成时间不过十余年,它的狭窄恰好促成了两边树木不算茂密的叶影,能在恰当的时间遮盖住它的全部。树木总能带给我在思维中一种渐变且模糊的视野,它们有着一个固定的朝向,像秩序一样统领着它的结构与表现;同时又因为不断向外拓展的枝杈,而拥有了更广阔的可能。尤其是当光照格外强烈的时候,它会给人一种与波斯细密画相类似的质感,色彩的整体结构丰富、庞杂而富有层理,呈现的效果是交杂且清晰的。
之所以要在开头引入这些大段的、近乎独白的文字,是因为我在两年前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环境对于我写作内在的冲击与更替。我在写作最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在更替阅读对象,很少有人能够被长久地读下去,它们本身局部的细节在某些时候具备吸引力,但整体的布局、运用的语言、切入问题的角度却始终具备天然的疏离感,时时刻刻与我正在思考的问题相排斥着,换句话说,我所始终经历、承载着的,难以借助我阅读的语言转化为文本。
有两个诗人对我在一段时间内的写作产生过影响。我反复读过很多遍读特拉克尔,他在当时对于语言气场的把握,对修辞的变革,譬如“死亡纯净的图像在教堂窗台边观望”(《林边隐匿处》)这样对语言中感受主体的置换,对尚未结束过严肃意义上现代诗歌的我而言,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去模仿的倾向;另一个我曾反复阅读的诗人则是顾城,他与特拉克尔的语言具备共同的一种深空般灰色的气质,譬如顾城《来源》中“泉水的台阶/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或者是特拉克尔《生命之魂》中“妹妹的嘴唇在黑色的枝头轻声轻语”至少影响了我一年时间的写作。我对词语的选用,对句式的掌控越来越靠近汉语语境下的特拉克尔和顾城,但当接近他之后,写作带来的更多的不是一种完成目标后所应有的喜悦,多数时候剩下的只是推着巨石抵达山顶后的疲惫。写作成为一种及其简单,甚至自动化的事情,它需要的只是纸笔,以及一下午的静坐;另一方面,它的每一次试图探出又极为艰难,想要跃出自身的认知,或者说语言惯性搭建的藩篱似乎没有任何途径。
我开始真正尝试现在形式上的写作,可以说是偶然,但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重复到一定次数后必然会出现的例外。大学二年级初始,偶然间我读到了复旦诗社的诗歌,他们的作品对于我当时的认知程度而言,进入仍旧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其与日常语言脱轨式的差距,修辞中隐隐可见的波光,就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尽管这种关注中仍充满着疑惑乃至不认同。后来我结识了游太平、陈建等人。他们语言中展示出的陌生的面孔以及熟悉的气息驱使我进一步去寻找这种写作运行的轨迹。在一次闲谈中,游太平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切都是在为一首诗作准备”,写作中的重复、单调乃至刻意错漏百出的表述,无非是在探索另一种可能的途径,写作的连续性并不是出自于文本在价值意义上的成功,而更多来自于失败的塑造。它们在诗学实践经验上有共同的作用,在每一次落脚点的寻找中都提供了可靠的讯息,并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文本向文明回溯,为个体经验提供了一种成为公共经验的可能。
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并不那么清晰,但至少给予我新的写作方向和动力。对我而言,写作不再是一件在个人的认知中不断循环、打磨,继而谋求其表达趋势更加圆满的过程,它更类似于一个工程,每个写作者都在熟稔既有的限制的基础上,充实它并为它添上新的边界,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不断去避开所有的成功与错误所有这些已经被我们熟知的表现方式。搭建这个工程的材料,因为人的局限性,我们只能使用和别人看似相同的东西,又希冀体现出每一个个体棱角的环境。譬如翡翠湖,另一位居住在翡翠湖边诗人陈先发也很早就已经写出过“这些被湖岸困住的湖水”,这是从水和岸的冲突方面来分析的,像横梁和立柱抵住,形成一首诗的建筑形式,结合整首诗的文本进一步迈向了阐释文明中既有的与不断出现的矛盾的可能性;我则写过“湖水诠释陆地的缺陷”,试图从湖水与陆地的共存面着手,它们在这首诗中就是一个平面上共同承受着力的钢筋。
遵循这种显然多有疏漏的写作方式,我一直在试图朝着自己认为更开阔、更具有可能性的作品而谨慎到近乎保守的方向前进。好友叶丹曾经就和我提过,我的部分作品“遮去姓名,完全就可以标上十九世纪的日期”。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对自身写作长久以来的忧患,它是不是因为过多思维的束缚,某些时候过于求新,超出了自我认知和语言所能负载的蕴义,某些时候又过于偏倚被灰尘覆满,逐渐被遗忘的诗歌形式,脱离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直到我后来和哑石谈起这个问题。他向我表述,一个诗人的作品最终目的仍是要固执地与这个时代的文明背景对话,尽管文明多数时候是没有任何回声的。诗歌对我而言由此从不断向高处搭建的建筑,更多地转化成为追随着文明轨迹的道路。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只是游离在这个时代文明背景的表层的部分,像水面归属于湖水,它很难在湖水更近一步,拥有进入深层的体验。同样,一层薄薄的水面同样也很难远离它所存在的这个文明背景。哪怕是再刻意地去挣脱,这样的文明背景仍可以在我的写作中留下我或疏离、或靠近,或刻意探索的印记。在合肥生活两年多,我习惯于向来客们介绍,合肥是一座缺乏特色的城市,它似乎什么都具备一些,譬如东南西北的吃食,途经的人群和天气。它的境内只有一座海拔两百多米,相对高度一百多米,勉强可称之为山的小丘陵,一如这个城市本身平淡的城市印象。很难说清合肥影响了我多少,但它的性格,确实在诸多方面成为了我的性格。
在整个文明背景的层次上,今天的文明相较于一百年前,又或者更久之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很难去系统完整总结出来,尤其是当文明每一天都可能要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又或者旧问题的不同形式。新的语言形式,如同格里耶所说,文体变化的根本性目的是为了不断地去适应这个时代的文明背景。而如何去与文明背景对话,怎样解决文明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更多依托于自身对文明背景的整体认知与个体的洞察,具体到我身上,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写作,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在写作中解决。我想在这里我也必须要为自己辩护,我的早期写作是真挚又拙劣的,它们无意识地遵循某种既有的秩序,还原了一个宏观意义上古老的村庄与儿时生态,它们多依赖于一种图像式的语言,当面对我正在经历的生活时显得极为笨拙;我现在的写作则更尝试于分析我自己的问题,进而在某種程度上展现一个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以期能够汇入这个时代众多探索、剖析的声音之中,尽管现在的写作往往难以被看作真诚。
最后还是提一下翡翠湖。去年末我印制了一本很小的册子,题目就是《在湖水边缘》,“湖水边缘”与我或许有着共同性的关系,是整片翡翠湖中最能吸引我的部分,它并不是指河岸,而是翡翠湖旁边一条很小的河,我将之理解为“湖水的边缘就是湖岸,再边缘就是注入它的河流”。大多数诗歌中,我提到的水面都是翡翠湖的水面。但在现实中的情况是,我几乎很少去湖边,它太过普通,只需一下午的观览,就可以在记忆中重构出一片湖水,并根据气候、人群等因素的转换,在思维中像不断叠加的漆器一样,模拟出这片湖水在不同情况下所可能展露出来的语意,并不断朝着更丰富、也更精准的方向递进。
说到底,它不过是一个极为寻常的物象,但有成为一台面向不同景别的摄影机的潜质,一直以来我通过它水面之上不断扩散的波纹,和水面之下可能隐藏的语义,去不断尝试抵达、发掘生活中许多或可记录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