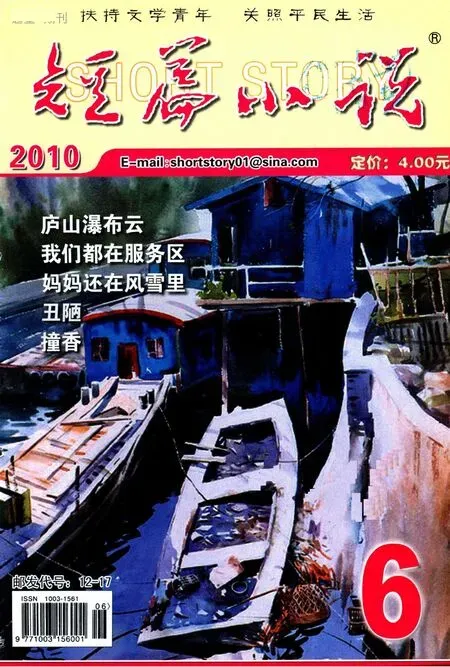飞翔的姿势
◎王明新

他一步步走向井架,一种欲飞的感觉充溢全身。这口井已经完钻,等待搬迁,井场上只留下一个人看井,这时候正躺在高架水罐下的阴凉里睡觉,对他的闯入全然不知。
他叫三孩,17岁的身子还显得有点稚嫩。如果他不是一个贫穷农民的儿子,这时候他已经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听老教授谈古论今了,坐在大学图书馆的某个阅览室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了,在大学校园里每天晚上必有的讲座或沙龙上听各种各样的奇谈妙论了,在大学生周末舞会上脸红心跳地与四妞在舞池里学“步”了。
他们那个村只有他和四妞考上了高中,一个村的男女老少把羡慕和笑脸都给了他们俩。县中学离村几十里路,他与四妞同来同去整整三年。
去学校的时候,要背着书包、煎饼和咸菜,走一段路他就对四妞说,我帮你背吧。四妞就看他一眼,把自己的一袋煎饼和咸菜交给他。又走一段路,四妞说,我背会儿吧,路远没轻债。他就看四妞一眼,把四妞的一袋煎饼和咸菜交还四妞。他看四妞或四妞看他的时候,总是四目相接,就撞出星星点点绚丽的火花。
他背的那些煎饼和咸菜要吃一个星期,四妞不,四妞是村支书的闺女,家里比他家富裕,四妞虽然也背煎饼和咸菜,但少得多,因为她还在学校的食堂买了饭菜票,就经常买食堂的白馍、猪肉炖粉条和豆腐炖白菜吃。
每次吃饭四妞都多买一些,拉他一块吃,他就咬一口煎饼,吃一口白馍,啃一口咸菜,夹一筷子白菜豆腐。四妞便夺下他的煎饼和咸菜,让他专吃白馍和猪肉炖粉条。四妞说,我又不吃肉,这么肥,我怕胖。
他们经常相互鼓励,好好学习,就是头悬梁锥刺股也一定要考上大学。
三孩说我们不能在村里窝一辈子。
四妞说不到20岁就生娃做饭围着锅台转我受不了。
三孩说生命真短啊,我们不能浪费在石头缝子里。
四妞说生命真好啊,我们得好好活,活得灿烂,活得精彩,才能对得起这么好的生命。
在来来去去的长长的山道上,话题多半是对未来的美丽憧憬和浪漫幻想,两个人常常谈论得热血沸腾,面颊赤红。
这时候四妞就提议唱歌,四妞唱《妹妹找哥泪花流》,三孩唱《好一朵茉莉花》,当然他们还唱他们家乡那首人人都会唱的民歌 《沂蒙山小调》,还有一些别的新的歌和旧的歌,歌声便撒满了弯弯曲曲的山道。
他们就真的考上了大学,并且是同一所大学录取的,因为他们报了同样的志愿而且都只报了一个志愿。
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是个黄昏,残阳如血,把一村的树和缭绕的烟雾都染红了。三孩的爹娘正在喂猪,他们从桶里舀一瓢食倒进猪槽,看着两头半大的猪呱嗒呱嗒香甜地吃,脸上浮着淡淡的满足的笑容。
听说三孩被大学录取了,两个人扔下猪食桶,一起跑过来,围着三孩一起转圈圈,满脸皱纹笑得又深又密。
三孩爹说,考中了,考中了,考中了……
三孩的娘说,这孩子,这孩子,这孩子。
三孩的爹手里的卷烟忘了吸,再吸的时候早已灭了火。
当听三孩说一入学光学费就要好几千块钱时,两个老人又一下子呆了。三孩爹就地蹲下去,身子一点点缩小;三孩娘手里的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半天没弯腰去拣。
山里黑得早,一家人没滋没味地吃了晚饭就吹灯上了床。三孩与爹娘睡隔壁,黑暗中,三孩听见爹唉一声娘唉一声,娘唉一声长爹唉一声短,爹唉一声长娘唉一声短,就唉到了天明。三孩听见爹娘起床,他也起了床,走到爹娘跟前说,爹,娘,学我不上了。
爹的眼就湿了,娘就放了声哭。
娘说,不是爹娘不明理,你哥娶你嫂子咱已经拉了一身饥荒,四邻八舍都借过了,再借上哪去借呢?
爹说,不是爹心狠,山里长大的娃还是在石头缝里找饭吃吧。
娘说,娃,这就是命,认命吧。
爹说,人犟犟不过命去。
四妞去上学的时候,全村人都去送,她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三孩没去送,还不到开学日期,油田来村里招收农民轮换工,合同是3年。3年之后怎么办?干好了3年之后还可以续合同,油田的人这样说。
三孩报了名。
吃了晚饭,四妞来找三孩,他们一起来到村外的一个荒土岗子前,荒土岗子一人多高,挡住了村人的眼睛。四妞看看四下里没人,红着脸对三孩说你抱抱我吧。三孩的脸一下子就酱紫了,说我不配。四妞说你瞎说,声音里就带了哭腔,眼泪跟着也流了下来。三孩就扑过去,一把抱住了四妞,把四妞的肩膀哭得湿了一片。他们在那个荒土岗子下面坐了很久,月亮爬上了山头的树梢,一地的虫不知愁地唱。四妞的娘喊四妞回家睡觉了,他们才又一次抱在一起,然后恋恋不舍地分开。
三孩去油田的时候四妞倒是去送他,三孩的眼肿肿的,四妞的眼也肿肿的。
井架40多米高,井架梯子盘绕井架而上,按直线算差不多有100多米。三孩一阶一阶往上攀登,随着躯体与井架顶端距离的接近,他感到了风的抚摸,听到了天空的召唤,那种欲飞的冲动也愈加强烈。
随着他每一步的攀登,井架梯子在脚下摇晃着,身体悬在半空,便有了点飘飘忽忽的感觉,像驾云一般。他不由自主地扇动双臂,立刻腋下生风,跃跃欲飞。
三孩第一次登井架,是一个多月前,那时候这口井刚刚开始安装。
天奇热,下过雨搬迁时又被各种大型车辆辗过的井场如一个烂泥塘,直射的阳光将湿气蒸发上来,使人喘不过气来,还浑身都不舒服。
三孩与师傅检修泥浆泵,那时他一切还都生疏,师傅拆这个卸那个,衣服全湿透了,他想帮师傅的忙却插不上手,急得浑身冒汗。这时他听师傅说,去,你到材料房拿个盘根来。在这之前,三孩听说过“盘根”这个词,却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他又不敢问师傅,只好硬着头皮懵懵懂懂向材料房走。
套在脚上的高筒水靴太大,后脚拔出来,前脚陷下去,一不小心将脚拽出水靴,赤脚踏进烂泥里,脚就和泥分不出来了。他顾不上把脚上的泥擦掉,用手拔出水靴来套在脚上继续向前走。
“处级钻工”正躲在材料房里佯睡偷懒。这小子是油田职工子弟,技校毕业,他爹也不知是个什么干部,反正每到周末就会有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到队上来接他回家过星期天,过完了再把他送回来。
在油田,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配专车,而他一个普通钻工却享受专车待遇,于是大伙都叫他“处级钻工”。镀金的,大家都这样说他。
“处级钻工”在队上自然是特等公民,没谁敢惹,而他又专爱欺负农民轮换工,平时三孩总躲着他走。这时三孩见了他却如见了救星,赔着笑脸恭恭敬敬叫了一声师傅,问他什么叫做盘根?“处级钻工”漫不经心地朝一个铁家伙指了指。
后来三孩才知道这个铁家伙根本不是盘根,而是缸套,盘根只有手镯那么大,是橡胶做的,而缸套却有百八十斤。当时,三孩却对他万分感谢。
三孩扛着百八十斤重的缸套,是如何跋涉过那几十米长的泥泞的可想而知,可当他“嗨”一声将缸套从肩上掀下来,重重地落在师傅面前时,师傅却凶狠地瞪了他一眼,并一把将三孩推了个屁股墩,师傅自己去拿盘根了。
然后便一个人拆了装装了拆,再不理三孩。三孩知道让“处级钻工”涮了,他坐在泥地上,委屈、愤恨、惭愧,种种感情纠集在心里,把个胸腔胀得要爆炸一样。泪水几次涌上来,又硬是让他憋了回去。“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话三孩不会说,但“男人的泪是金豆子,不能轻易让它滚出来”,三孩早就听说过。
这话他是听四妞说的。上高三的时候,新学年开学,他两手空空忐忑不安地往学校走。路上四妞问他,你的学费凑齐了吗?一句话把他问哭了。眼看就要开学,爹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捆了猪送进食品收购站,谁知猪太小不够分量,人家不收,爹说了多少好话也不顶用。四妞说,男人的泪是金豆子,不能轻易让它滚出来。说着从自己身上掏出一把碎票子给了三孩,说这是我平时攒的,本打算零花的。三孩数数,正好够交学费……
终于休息了,许多人躲在高架水罐下的那片唯一的一点阴凉里,躺了个横七竖八,一片狼籍,疲乏和那身被油泥涂抹成黑灰色的衣服使他们像极了一具具僵尸。三孩心情抑郁,独自向井架顶上攀去。当他登上井架顶端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原来以为高不可测的天空离他竟这样近,原来以为飘忽不定的云这时似乎伸手可触。他纵目望去,茫茫大野,无边无际,世界竟这样大呀!他顿时忘却了种种烦恼,只觉得心旷神怡,激动不已。这时候,他看到一只鸟,一只像飞机那样大的鸟,那鸟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
三孩想,这鸟怎么就没个伴呢,与自己一样孤独无助,就可怜起那只鸟来。那鸟好像不想让三孩可怜,伸展双翼自由自在在蓝天下盘旋,它时高时低,时而抖动翅膀闪电般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时而双翅纹丝不动悠然如一片停在半空的树叶。仿佛它就是这浩瀚天空的主宰,或者说它是这茫茫宇宙的宠儿,天马行空,任由来去。看着看着,三孩激动了,我要做一只鸟!三孩在心里默默地喊道。这个奇异的想法使他兴奋,使他狂热,使他忘乎所以。他伸展双臂如鸟的翅膀,然后上下扇动着做飞翔状。他立刻觉得两腋生风,风力把他高高托起,他就真的如一只鸟一样翱翔于蓝天之下了。
飞呀,飞呀,他要飞越荒野,飞出油田,飞向那所远方城市的大学,飞到四妞身旁……不,不,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飞翔,像鸟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因为他知道自己配不上四妞。
飞翔的感觉使他热泪盈眶,终于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像憋久了的水突然打开了闸门,狂奔而出,一泄千里。他一边哭一边扇动双臂,继续着自己的“飞翔”。
终于,鸟飞走了,三孩颓然垂下双臂。
我要做一只鸟!三孩站在井架上对天发誓。
自此以后,三孩就经常到井架顶上来,有时做飞的种种动作,有时做飞的种种幻想,每次他都激动得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只有此刻,他满心的阴霾才会一扫而光。“我要做一只鸟”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不可遏止。
三孩登上井架顶端的时候,那只大鸟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三孩想它可能是回窝里睡觉了,或者去别的地方觅食了,最大的可能是去恋爱了。但更多的时候那只大鸟都在,三孩就闭上眼睛与它一起飞,他要与那只大鸟比一比,看谁飞得高,看谁飞得快,看谁一动不动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看谁一动不动在空中盘旋得久。秋天过去了,冬天要来了,夜里躺在床上三孩经常听到大雁的叫声,三孩知道大雁去南方越冬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三孩果然看到了大雁,它们排着队,一边飞一边前呼后应,大概是相互照应着不要掉队吧。这天休息的时候,三孩又登到井架顶上,一队大雁飞过来,就从三孩身边掠过,三孩能清晰地看见它们身上的羽毛和它们一张一合的嘴,还能听到它们扇动翅膀时发出的有力的响声。三孩注意到大雁飞的时候,翅膀是不停扇动的,它们不会像那只大鸟那样一动不动停留在空中或一动不动在空中盘旋。三孩觉得那只大鸟飞翔的时候姿势更加优美。但三孩知道大雁要赶路,要赶很远很远的路,所以它们不能像那只大鸟那样停在空中或在空中盘旋。
队上来了电影队,班长说,三孩你去看井吧。其实不该三孩看井,昨天三孩刚看过井,但三孩是农民轮换工,就只好放弃看电影去看井。8个小时一个人很难熬,三孩想打个盹,打盹时间过得快,可蚊子太多,咬得三孩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接班的来了,三孩无精打采地走回宿舍。宿舍里一只灯亮着,所有的人都睡得死了一般。三孩看见自己床上的褥子滑到了地上,洁白的粗布床单上印着一只只黑黑的鞋印,留在床上的部分落满了烟灰。一堆玩旧的扑克,零乱地散落在自己床上。
三孩心里一阵阵地疼。这套铺盖是三孩来油田时,娘连夜做起来的。布是娘一根经一根纬织起来的,棉花是爹、娘用汗水一滴一滴浇灌出来的。三孩轻轻拍打着床单和褥子上的烟灰和尘土,灰尘入进布里,变成了一片黑。这一片,那一片,看得三孩心里头又酸又胀。这么多床铺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自己床上打扑克呢?因为自己是新来的?还是因为自己是农民轮换工?更大的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想到这里,三孩一脚将跟前一只空脸盆踢飞,脸盆飞出去后撞在别的脸盆上,又撞在一只水桶上,发出一连串叮叮咚咚的刺耳声响。收拾好床铺关了灯,在黑暗中躺下来,满眼的泪水无声地滑了出来。
夜里,三孩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真的可以自由自在飞翔了。他伸展双臂如鸟的羽翼,双腿并起如掌握方向的鸟尾。在梦中他身轻如燕,在气流的托举下直冲蓝天白云。
他一边飞翔一边伸手摸了摸天,天是凉的,像一块打磨光滑了的石头;他又摸了摸云,云是湿的,像被露水打湿的刚刚摘下来的棉花。他就在蓝天白云间穿梭飞翔。他身边有大的鸟和小的鸟,他觉得自己同它们一样灵动敏捷。
他向下俯视,下面是一片广阔的荒野,有的地方光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有的地方芳草萋萋一片碧绿,一条小河从荒野上蜿蜒流过,明亮的河水闪闪发光。他还看到一座井架,它是那样小,小得就像一颗羊拉的黑屎蛋,井架下的人小得就当然看不清了。他觉得是那样舒畅,那样惬意,那样无拘无束,他飞呀飞呀飞呀……
三孩醒来的时候,一片刺眼的阳光从板房的窗子上照进来,在床上照出一个碗口大的光斑,光斑里静静地躺着一封信,如一只洁白的鸽子。
洁白的信封上,有用他熟悉的字体写着的他的地址和名字,下面落款是机器印的,他曾向往的那所大学的名称一片艳红。他激动得心跳都停止了,用颤抖的手将信封拆开,果然是四妞写来的。
当三孩决定不去大学报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的缘分已经尽了,虽然那个晚上他们曾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曾吻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他知道那是他们各自赠给对方的最后的礼物。没想到四妞还会给他来信。四妞一定是从家里打听到自己的地址的,因为三孩从没告诉过四妞自己的地址。
四妞先问他的工作情况怎么样,说他们一起高中毕业,他已经能自食其力了,而自己还要靠父母养活,对他十分钦佩和羡慕等,然后开始介绍她的大学和她的大学生活。
四妞说,自我迈进大学校门第一步,到处都使我感到新奇和兴奋,而我入学后的所有日子,都是在这种新奇和兴奋中度过的。
走进大学校门,四妞写道:先看到的是一个带音乐喷泉的圆形花园,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我一个也叫不上名字来,后来才听同学们说有鸡冠、月季、芍药、紫丁香和白丁香,大约有几十种,我一下子记不了那么多名称。最使人感到新奇的还是那个音乐喷泉,只要音乐一放,几十支喷头就会喷出水来,它们随着音乐的变化,水流时高时低,时急时缓,变化无穷,变幻莫测。
校园绿树成荫,高楼林立。我上课的那座教学楼六层高,教室里真是宽敞明亮极了。学校有一座其大无比的图书馆楼,光阅览室就有几十个,书库里的书比咱们县棉花加工厂里一垛垛的棉花还要多。学校还有澡堂,老师和学生是分开的,我每个星期都可以洗上一次澡,你知道我们那个县,整个县城只有一个澡堂,每次过年我都去洗一次澡,澡堂子里的人像下饺子,水稠得像面条汤。哎呀呀!四妞这样写道。读到这里三孩能想象到四妞写这封信的时候,那种惊叹、自豪和调皮的样子。
大学生活比我们上高中时丰富多了,我们除了上课、去图书馆,还可以看电影、参加体育活动,学校每个周末的晚上都有舞会呢,真有趣,可是现在我还没学会跳舞,不过我一定能学会的……
信的结尾写道: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同学们有点瞧不起我,这使我常常感到孤独,如果你能与我一起来上学就好了,真可惜。不过我不会给咱山里人丢脸,我会好好学习,让那些瞧不起我的同学看看咱们山里人并不比谁差。
四妞的信如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三孩尚未愈合的伤口上一刀刀划下去,一刀比一刀狠,一刀比一刀划得更深,直划得三孩伤口遍体,鲜血淋淋。
四妞,四妞!三孩在心里高声喊着,一声比一声凄厉,如杜鹃啼血。四妞,你等我,三孩继续喊,我来了,我要与你一起上学,我要与你一起跳舞,我不让你与别人跳舞,我不让你孤独!
三孩如一只受伤的狼冲出宿舍,一步步走向静静的井场,走向高高的井架,他要做一次真正的飞翔,就像他看到的那只如飞机一样大的鸟那样,就像在梦中那样。这是一次真实的飞翔,他要飞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然就枉为一个17岁的男子汉。三孩走得急迫而从容,他一边走一边将那封信扯得稀碎,随手扬在广袤的荒野上,让那些纸屑雪花一样随风飘去。
三孩越来越接近井架顶端了,高空强劲的风鼓动着他薄如蝉翼的旧衫,他觉得真如翅膀一样了。他抬头望去,空中没有一只鸟,连一片云也没有,头上是一片瓦蓝纯净的天空,脚下是一片茫茫无际的荒野。
这时,他突然看到草丛中有一只野兔,那野兔在草丛中跳来跳去,不时用两只后腿站立起来,向他翘望着。三孩向那只野兔招招手,心里说,它大概是自己飞翔的唯一观众了。
三孩登上井架的顶端,他回忆着梦中的飞翔姿势,一边回忆一边伸展双臂做复习性练习。这时候三孩突然犹豫起来:是像那只大鸟那样飞翔?还是像大雁那样飞翔?那只大鸟飞翔的姿势当然更加优美,但大雁一刻不停地扇动翅膀肯定飞得更快,飞得更远。那只大鸟之所以在空中盘旋不肯离去是因为它恋着自己的巢,大雁之所以义无反顾是因为它们冬天的家在远方。
三孩既想让自己飞翔的姿势优美,又希望像大雁那样飞得更快更远。纠结了一会儿,三孩决定以那只大鸟的姿势,以大雁对远方的渴望去飞翔。他希望以最优美、最潇洒的姿势出现在四妞面前,如果四妞能看到他的话。这样决定了之后,三孩闭上眼睛,便如一只鸟从井架上一跃而下。
在那一刻,世界上的一切都静止了,三孩如自由落体,从空中飘飘而下。
梦中的景象立刻重现在眼前:下面一片广阔的荒野,有的地方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有的地方芳草萋萋一片碧绿,一条小河从荒原上蜿蜒穿过,明亮的河水闪闪发光。一座井架是那样小,小得就像一颗羊拉的黑屎蛋。他感到自己是那样舒畅,那样惬意,那样无拘无束,他飞呀飞呀飞呀……
三孩忽然想唱歌,还唱那首《好一朵茉莉花》吧,三孩就放了声唱,三孩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像今天唱得这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