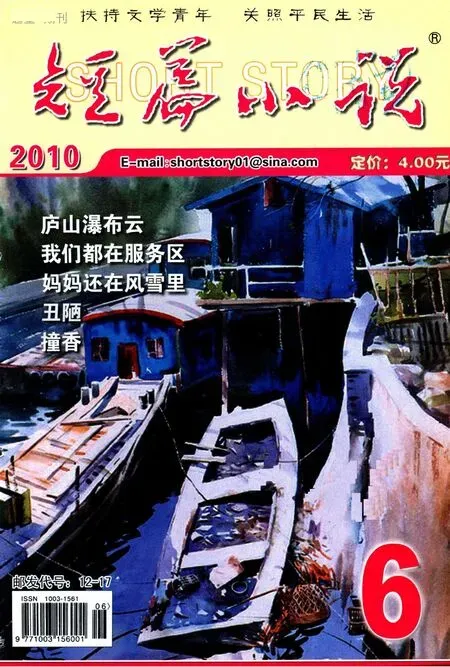琴姑姑
◎刘 红

一
我冬生舅舅走到我四姥姥跟前,说,娘,你去跟我莲姐(冬生舅舅嘴里的莲姐是我母亲)说,让她把她那个叔伯小姑子介绍给我吧。四姥姥此时正坐在门前石阶上,腿上搭着一个盛麦子的簸箕,她正低头捡里面的小石子。四姥姥停住手里的动作,把住簸箕两帮子,抬眼瞅着冬生舅舅。冬生舅舅修长的身影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帅气。他瘦削的脸颊上凸现出分明的棱角,一双深邃的大眼睛透出明澈的光芒。四姥姥看着俊逸的儿子,心里想,要说儿子的眼光还真不错,并且,整个杨树拐村恐怕也就只有儿子能配得上琴了。
四姥姥轻叹一声,说,儿啊,明摆着的事,不可能啊,你就不想想,她有三个兄弟呢,就凭她家土改时分得的地主家的几间房,孤儿寡母的,又没啥家底,她能不为其中的一个兄弟换媳妇吗?极有可能得为老大换,老大眼看着已经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
冬生舅舅说,娘,你怎么这么说呢?她是一个人啊,又不是一个物件,或者猪狗鸡猫的,能随便跟人交换。
四姥姥两手把着簸箕两帮子扇了两下,一层麦皮碎屑随着簸箕的颠动,纷纷舞着跳出簸箕沿儿,还没落地就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四姥姥停下来,说,咱们村里,你看看,哪家的闺女逃脱得了?村子依山又缺水,种地累死个人,哪个姑娘愿意嫁过来?村里但凡有儿子的,哪个不得拿闺女来换?
全子姐姐就没有给全子换,人家可是自己找的婆家。说这话时,冬生舅舅的眼里跳动着一簇亮晶晶的光点子。
你不想想,全子是谁?乡干部的外甥,吃商品粮的长期工人!村里有几个全子?
冬生舅舅扭身去西厢房里推刚买的崭新晶亮的飞鸽牌自行车,走到门口,又扭回头来,对着我四姥姥喊,娘,不管中不中,也让我莲姐去问问吧!
四姥姥扇着手里的簸箕,用“知道了”三个字来把又一个叹息压回去了。
四姥姥怎么不知道?平心而论,冬生舅舅是完全配得上琴姑姑的,冬生舅舅不但长得隆鼻朗目的,俊秀飘逸,而且还接了我四姥爷的班儿,到乡里的供销社上班,成了端上铁饭碗的国家长期工人。勿论冬生舅舅的长相了,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俘获很多村里漂亮姑娘的芳心。
然而,四姥姥就算把脑袋想破,也想不出琴姑姑有不给兄弟换媳妇的理由,但是为了儿子,她还是决定一试,死马权当活马医嘛。
二
母亲走进三奶奶家的南屋时,琴姑姑正坐在窗前的杌子上绣花。她低了头,颀长白皙的脖子微微勾着,呈现出美丽的弧度,像极了在沙滩上漫步觅食的白天鹅,她纤长的手指呈兰花指状,细弱的绣花针在她手里翻飞,圆形的绷子上一对鸳鸯呼之欲出。红嘴橙脚,头着彩色冠羽的鸳,黑嘴灰羽、形体略微小一点的鸯,两两亲密相依。它们身旁是开得正艳的粉红色荷花,青翠欲滴的大叶子,一只黑黄相间的蜻蜓在花瓣间振翅欲飞。碧波一层一层的,正在荡漾的样子。母亲看得呆了,在琴姑姑的绣花绷子上,似乎在这个俗世之外又是一个水上活灵活现的世界。
琴姑姑由于太过专心,竟然没有听见我母亲走进来的声音,直到母亲情不自禁地“呀”出口,琴姑姑才被惊醒似的,身子一抖,扭过头来跟母亲打招呼。琴姑姑笑着问,嫂子有事?顺手拉过一把椅子请母亲坐。大人们都说我琴姑姑就是这样的人,不说话不笑,不叫人不说话(称呼长辈们婶子、大娘、叔叔、大爷),只要琴姑姑的朱唇轻启,那笑必要先跑到嘴角上,嘴角弯起的弧度好看极了,使那张颇具特点的嘴巴又添几分生动。而那从她嘴里蹦出来的一句句婶子大娘伯伯等亲切的称呼,甜豆子似的,脆生生、甜丝丝。那些被叫的婶子大娘叔叔大爷们,一下就陶醉得晕乎乎的,脚踏不着地的感觉。主管我们村的一个大队干部就被琴姑姑叫得晕乎乎了,继而眉开眼笑了,眉开眼笑的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大手一挥,说,人家琴的女红恁好家(方言,特别好的意思),不能让她跟大家平板着(方言,跟大家一样干重活儿)一起下地干活了,得让她专门负责做队里的针线。他脸转向琴姑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下地了,只留在家里做针线就可以了。每天去牲口院看看哪个驴谷撮子破了、开线了,就缝一缝。从那以后琴姑姑就差不多真成小姐坐绣楼了,再也没有踏过地半步,直到生产队解散,土地分配到户,她才重新开始去地里,这是后话。坐了绣楼的琴姑姑原本白皙细腻的肌肤更加光滑雪白了,越发跟我那些黑肤糙皮的姑姑们以及村里的其他姑娘们区别开来了。我别的姑姑们见天价儿丢了耙子拿扫帚,丢了勾担取锄头。茅坑里的大粪被她们一担一担地挑到地里头,那身上时不时就散发出一股大粪的恶臭味儿,哪像我琴姑姑,身上终年散发着夏士莲雪花膏和海鸥牌洗发膏的清香味儿。我有时间就想往我三奶奶家里跑,得空儿就想往我琴姑姑屋里钻。琴姑姑总是笑着呵斥我:花丫头,快出门去跟小伙伴们玩吧,别在这儿淘气!琴姑姑是怕我的小黑手随便在她屋子里一摸,就给摸脏了屋里的物品。琴姑姑的床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一块儿雪白的衬布上,一只黄嘴小鸟儿在一支鲜红的玫瑰上昂头鸣叫。用报纸裱糊过的墙壁白刷刷的,用过期的挂历的背面围成的炕围子,白花花的,在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芒。总之琴姑姑的屋子里特别干净,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我常常赖在她旁边,不愿意走。
平时说话伶牙俐齿、火鞭炮仗一般的母亲此时却扭捏起来,期期艾艾的,我,我,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直到三奶奶走过来,母亲才像遇见救兵一般,立即喊了声三婶子,说三婶子你看,咱们家琴绣得那花儿,跟真的一样,真是巧手啊!三奶奶笑眯眯的,得意与骄傲从脸上那褶子里呼啦啦往外冒,藏也藏不住。嘴上却谦虚着,哪里,也一般般吧。
母亲说,像咱家琴这样的人材、这样灵巧的姑娘非得找个国家人做女婿不可,光国家人还不行,还得有人材,必得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子有个子。母亲眼瞅着三奶奶的脸蛋子忽闪一下就从万里晴空变作阴云朵朵了,再看琴姑姑,那绣花针已然向她的手扎去了,白皙的左手大拇指上隐隐可见殷红的血迹往出洇。母亲已然知道自己的话是冒失的、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因受四姥姥所托,她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母亲咽了一口唾沫,清了清嗓子,说,要我说,咱村里除了冬子能配得上咱家琴,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母亲的话像催化剂,把三奶奶的脸蛋子干脆催得阴云密布了,琴姑姑的左手上已经有好几个针眼子在往外洇血。
三奶奶拿眼觑着琴姑姑,从嗓子眼里吭了一声,吧咂吧咂嘴,说,这个……三奶奶的这个到底没有了下文。最后还是琴姑姑说,嫂子,我还小呢,还不谈这个。还小呢,都二十三了,村里你的同龄姑娘都快出嫁完了。母亲的这些话被三奶奶郁沉森森的眼神镇在了嗓子眼那儿,母亲一用劲儿把他们咕噜一下咽回了肚子里。母亲诺诺着,嗯,也是……
后来听母亲说,像母亲一样受人之托前去琴姑姑家求亲的有无数个,且都是各方面条件优越的,特别是都是吃商品粮的。三奶奶和琴姑姑一起拒绝了方圆数十里很多慕名而来的优秀小伙子。
三
被拒绝的冬生舅舅并没有死心,而是三番五次托母亲给琴姑姑捎去他从供销社给她买的礼物,小到一方时兴的小手帕、一条漂亮的丝巾,大到一块外人需要凭票购买的女式手表。母亲明知道是勉为其难,可是为了不惹下自家的娘家人,还是三番五次地走进了三奶奶家里。
对于这些农村稀缺的物品,毫无疑问,琴姑姑是喜欢的。琴姑姑拿眼扫着这些东西,嘴里却用坚决的语气请母亲拿回去。母亲每次都硬给她留下了,琴姑姑又往我家里送了几次,也就烦了,不再送了。
冬生舅舅在计划送琴姑姑手表时决定要亲自送给琴姑姑,并亲自给她戴上,他想象着琴姑姑那雪白的手腕子上若戴上那块漂亮的女式手表该是多么相宜的事啊!
冬生舅舅再次求我母亲做了传话筒子,约琴姑姑晚上在村东头大槐树下见。
正是槐花飘香的季节,一股子一股子浓郁的槐花香味儿直钻人的鼻子,香味儿太浓烈了,琴姑姑不觉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
冬生舅舅与琴姑姑的面谈场面、所谈内容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琴姑姑收下了冬生舅舅赠她的女式手表,因为在琴姑姑与林子姑父定亲之前她一直戴在手腕上的。她抬臂甩腕之间,那手表一晃一晃的,闪着灼人眼目的耀眼光芒。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琴姑姑坚决地拒绝了冬生舅舅的求婚。
冬生舅舅第二天就病了。
一个八尺男儿居然病得起不了床,蒙着被子在床上几天不露头。四姥姥来求母亲,说莲儿呀,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冬子吧,自从见过你那好小姑子琴后,已经躺在床上五天不起来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你就该去给你兄弟奔丧了!
四姥姥说这些话时,咬牙切齿,显出狠狠的质地,而她的眼睛却红红的,明明灭灭的泪珠子在阳光下折射出多彩的颜色,她不停地用一个手帕子擦抹着。
母亲站在冬生舅舅床前,说,冬子,你何苦呢?凭咱的条件,啥样儿的姑娘找不着,为什么偏偏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些话说出去,母亲明显感觉到它们的苍白无力。
被子在那儿抖呢!被子在那儿觳觫呢!我嚷嚷着,母亲拉着我的手使劲儿甩了两下,意思是让我闭口。明明就是嘛,还不让说,我嘟起嘴嚷嚷着。母亲丢开我的手,说,外边玩去吧,别成天跟个黏胡桃似的,不离胡儿!我边往外跑,边扔出一句:你们大人都是些什么人嘛,不让说话,我偏说,被子在那儿觳觫呢,被子在那儿觳觫呢!
也不知道母亲用了什么法子,冬生舅舅总算从被窝里爬出来了,并且吩咐四姥姥:娘,去,去告诉那些媒人,我要去见他们为我介绍的对象。四姥姥那张被愁云遮了好几天的苦脸子一下子乐开了花儿,她颠动着那双裹过、半路上又放开了的半大不小的脚,屁颠屁颠地逐个去告诉媒人,她家冬子愿意见之前他们为他介绍的姑娘了。
冬生舅舅最后在好几个长相不俗的姑娘里挑中了身形乍一看去跟琴姑姑相似的姑娘爱珍。只是他又为四姥姥出了个难题:结婚摆柜的鞋子,得请琴姑姑亲自做。
四姥姥心里说,你是不是脑子犯糊涂,你说这叫什么事嘛,甭说人家琴不答应了,就是爱珍脸皮子上也不好看不是?人家都是自家新媳妇做摆柜鞋,太笨,做得实在拿不出手的才请人做。而我们杨树拐村往往非琴姑姑莫属。四姥姥只在心里边叫苦,面子上却满口答应了冬生舅舅的不情之请。
四姥姥毫无疑问又来找我母亲,我母亲义无反顾地涎着脸去求琴姑姑。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琴姑姑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冬生舅舅的婚礼空前隆重而热闹,全村的人几乎倾巢而出,大家争前恐后地要看看,这个村里的第一美男子,国家人,家境殷实的小伙子到底娶了什么样的大美女。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婚礼上的重点居然成了柜子里的鞋子与鞋垫。
待我母亲用钥匙打开贴着大红双喜字的柜子,所有盯着柜子的眼睛都直了。
只见柜子里的新鞋子雪白的底面,黑色的鞋帮子一双双在那儿支头竖脑的,舒展、板正。一群女人嘴里发出一大片啧啧声,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待要拿到手里细端详,又怕弄脏了,先去裤子缝那儿擦一下手再拿鞋子。只见千层底子上,一排排针脚绵密、匀称,留的花型多样,且美观好看。偏、正莲花、蝙蝠、树板根、小葫芦、套搭子……都是难度比较大,一般妇女不大会留的。
鞋帮子的边沿统统用白布包了,留出的白道子宽窄均匀,看不出针脚,让人怀疑是一体的。人们惊叹,就算机器也不一定做得这么好吧?人们说,这个新媳妇可不得了,原本以为方圆村子里只有琴能做出这么精致的活儿来,再也想不到冬子居然娶了这么巧的媳妇,这手艺,这巧妙,一点也不逊色琴!
母亲听着大伙儿的议论,也不言语,只微微笑着。坐在屋子里的新娘子听到了耳朵根子里,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的大眼睛倏地就遮上一层灰云,那张因打过胭脂原本就红扑扑的鹅蛋脸瞬间飞上红霞,显得更红了。她低下头摆弄着自己的衣角,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四
三奶奶家的三个儿子像地里见风就长的庄稼秆子,呼啦啦往上蹿。用我奶奶他们的话说,不见元旦儿就长高了,长成人了。这不,老大根子叔已经二十二岁了,琴姑姑也已经二十六岁。这个年龄,甭说在我们杨树拐村算大龄女了,就是放到广大的农村世界里,也已经是,用我奶奶她们的话说,老闺女了。
正当大家带着惋惜的口吻,纷纷猜测像琴姑姑这样的好闺女作为换亲的一个筹码,也不知要遭遇一个怎样差劲儿的男人时——要知道,但凡需要换亲的,男方肯定都多少存在点缺陷,譬如迟钝、木讷,这是最常见的,当然也有跟我三奶奶家状况一样,家在山区,孤儿寡母家境困顿的。却忽然传出了琴姑姑“送数”的消息来。很快大家就知道了,琴姑姑并没有给哪个兄弟换亲,而是自作主张跟自己看上的一个大队干部的儿子订婚了。媒人正是一直赏识琴姑姑的那个干部,他是男方的姨夫。小伙子比琴姑姑小四岁,长相中等,人却机灵,已经被大队推荐当兵且转了志愿兵,听说不日将提干。这个消息如在小村投了一枚炸弹一般,一下把小村炸得沸腾了,说什么样话的都有。
有人说,人家琴到底是刚强的,有骨气的,不像村里那些没有主见、软弱无能的姑娘一样,以葬送自己的幸福为筹码,去为兄弟们换媳妇。
有人就嗤着鼻子反驳说,什么刚强、有骨气,明明是自私自利嘛!就不想想,爹早没了,就一个寡妇老娘,底下三个光棍儿兄弟,房没盖半间,后边的日子咋过呢,就自顾自秃噜一声拣高枝儿飞了。
村里的议论基本是围绕着这个两个观点展开的。
琴姑姑的婚事被村里人当作天大的事颠过来倒过去地议论,褒奖与贬责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每每都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冬生舅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侍候他媳妇的第二个月子,他们的大小子已经三岁了,现在又生了第二个小子。我四姥姥高兴得嘴巴天天合不拢,整天张着一张掉了门牙的嘴巴笑得脸上的褶子像老丝瓜皮。她指挥着冬生舅舅为他媳妇做月子饭,她负责给孩子洗尿布。
冬生舅舅正端着一碗红糖鸡蛋疙瘩汤往屋里给媳妇送,四姥姥冷不丁说了句,知道吗,琴那妮子订婚了,不是换亲!听说是个军……
一声“啪嚓”把四姥姥那尚未出口的官字变作了,怎么了,这是?
冬生舅舅手里的汤碗早就在石头地板上碎成了无数瓣儿,黄灿灿的鸡蛋在青石地板上像一只只正咧着笑的娃娃嘴。
冬生舅舅的眼珠子停滞不动,两只手还在半空扎煞着,作端碗拿筷子状。那傻傻的样子真像一只呆雁。四姥姥看冬生舅舅这样子,一张嘴变作了O型,半晌忘了合拢。
直到媳妇在屋里尖着嗓子嚷嚷着怎么了怎么了,冬生舅舅才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冬生舅舅忽然说我胃疼,就捂着肚子往西厢房那张客床上躺去了。
四姥姥叹着气把一地的零落收拾打扫着,屋里的媳妇听这故事,便知道了怎么回事。等四姥姥再重新去为她做好鸡蛋汤,她也不吃了,光蒙着被子嘤嘤地哭。
五
琴姑姑的未婚夫来三奶奶家了。
奶奶母亲她们去看新客。
三奶奶把本家的一一给他作了介绍,他亲切地喊着大娘婶子和嫂子,大大方方的,一点也不拘谨。他亲手倒了茶,一一捧给大家,嘴里说着大娘喝茶、婶子喝茶。
闲下来就紧挨着琴姑姑坐着,用手轻轻摆弄琴姑姑垂至屁股尖子的发梢,时不时咬一下琴姑姑的耳朵,窃窃私语,琴姑姑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有时也稍稍摆一下头跟他嘀咕一句。他们俩的举动很容易让我想起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亲密的恋人镜头。
三奶奶的脸淡淡的,看不出悲喜,但那时不时的一个走神带出来的阴郁还是被我细心的母亲捕捉到了。母亲说,你看看你三奶奶,褶子里藏着苦呢!
母亲说,你琴姑姑的女婿倒大方得很,喊我们喊得多么亲切!还没结婚,居然喊你三奶奶娘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你琴姑姑亲得,也不嫌脸红,你琴姑姑也是,不但不避讳,还跟他又咬耳朵又碰头的,就差……母亲意识到自己失口了,赶紧改了口,你姑姑们谁敢,羞不死个人!
琴姑姑没有在意村里人对自己的窃窃私语和指指戳戳,照样跟未婚夫手拉手地出双入对,用今天的话说,大秀恩爱。
未婚夫该归队了,琴姑姑去送,在车站两人难舍难分。琴姑姑一直站在车窗外,她未婚夫从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捏着她的一只手。直到车嗤地开走了,两只紧紧拉着的手才被强行分开。
在等待再相见的日子里,琴姑姑为未婚夫做了一双鞋子又一双,纳了一副鞋垫又一副,甚至为他织毛衣、编织围巾、勾手套,明明知道,这些个东西在部队根本用不上,她还是要织,要编,要勾。
六
琴姑姑收到未婚夫的分手信时,正是傍晚,四合的暮色像一张巨大的嘴巴,把琴姑姑一点一点吞噬了。琴姑姑感觉自己浑身软塌塌地掉进了一个深渊里。
信中说,他们俩岁数差得太大,自己长得也没有琴姑姑高,最重要的是,两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琴姑姑心里说,这不是扯淡吗?一个月前的信件还是十多页,明明有说不完的话,却忽然又说没了共同语言,至于其他两条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整个夜里,琴姑姑躺在黑暗里,眼泪流了一轮又一轮。一忽儿觉得都是自己的命,决定认命,一忽儿又不甘心,自己这么大的姑娘了,硬着心肠惹下母亲和弟弟们找了这么个军官,被村里人吵得沸沸扬扬的。
在床上煎了一夜鱿鱼的琴姑姑,天不亮就起来去敲媒人家的门。
琴姑姑喊了一声姨夫,就抽抽搭搭哭起来了。那眼泪啪嗒啪嗒的,珠子般不停地滚落。刚刚起床的媒人,肩披着一件外衣,那双惺忪的睡眼一下被琴姑姑的哭声惊得瞪圆了。他问,怎么了,这是?琴姑姑不说话,光顾着哭。
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就在琴姑姑跟前踱步子,踱过来踱过去,两只大手不住地搓着,嘴里哎哎的。
等琴姑姑终于哭够了,才说他外甥提出了分手。分手俩字刚出口,琴姑姑又开始抽搭着哭起来,边哭边说,姨夫你可要为我作主呀!
具体这个姨夫媒人是怎么把那个因被自己上司的女儿看上而很快见异思迁的外甥镇住的,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看到的是个圆满的结局:琴姑姑嫁给了军官。琴姑姑的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琴姑姑结婚后,接连为军官丈夫生了俩儿子。生完小儿子后不久就随军了,从那以后就很少见她了。我们只知道她生活在济南,只知道她冬天屋子里有暖气冻不着,夏天有空调热不着,听说人前人后丈夫对她很好。一句话,琴姑姑的生活十分美满幸福。
七
琴姑姑每年一家四口回来省一回亲,看得出,她和她的军官丈夫确实很和谐,军官丈夫在我三奶奶家,还像刚开始一样,口儿甜、活道。
琴姑姑最后一次回来省亲时,我三奶奶已经是儿孙绕膝了。我根子叔最后娶了个有点憨傻的哑巴媳妇,给他生了一男一女俩半傻不傻的孩子,三奶奶得亲自管俩孩子,洗衣做饭,给小的喂饭,用三奶奶的话说,哪儿不到哪儿不中。二叔娶了个比他大好几岁的寡妇,带了个儿子,又生了俩女儿,闲了就朝我三奶奶嚷嚷,说她的心长到胳老肢(方言,腋窝)那儿了,偏得离谱,光管哑巴的孩子,不给自己带孩子。又说,到底不是她亲生的孙子,差了一截呢!三奶奶听见这话,开始时还争辩几句,抹一把眼泪,慢慢地,也就习惯了,管她怎么嚷嚷,三奶奶该抱柴抱柴该做饭做饭,该给俩孩子缝衣服缝衣服,权当没听见。
三叔从四川买回来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做媳妇,小姑娘见天儿价叽叽喳喳地跟三叔在院子里打情骂俏,一点也不知道避讳。听见街门外有叫卖水果、花生等吃食的,拽着三叔就让去买。寡妇见了就拿眼瞅她撇嘴,嘴里轻声嘟哝,不知道害臊!
琴姑姑一家回来,院子里到处是小孩子玩的棍棒疙瘩,石头、泥巴,一大群小鸡咕咕叫着到处是它们的影子,它们毫不避讳地到处拉屎,使得我琴姑姑家从城里来的俩儿子站在那里叫嚷,妈妈,鸡屎,脏!脚不敢往前迈动。
琴姑姑买的小食品被寡妇家的孩子带头一抢而光。给三奶奶、几个弟媳、侄子侄女分别买了衣服。她们争着比划谁的好,寡妇总是觉得自己吃亏,干脆拿起琴姑姑给三奶奶买的白色的褂子,说这个褂子我穿正合适,还是我穿了吧!说着就把她和她孩子的那一份一并收起来,扭着屁股往她住的西厢房去了。琴姑姑的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温和谦逊的表情看不到了,露出微微的愠怒和鄙夷。琴姑姑瞅着丈夫的样子,脸上的表情讪讪的、木着,像笑又像哭。
八
琴姑姑三年没回来省亲了。
原来拍回来电报说是忙,回不来,后来又说得了胃溃疡,不舒服,就不回来了。后来忽然接到她丈夫的电报,说其实她得的是胃癌,之前怕家人担心,她一直不让说,已经去南京做过一次手术了,刚复查了,需要再去南京做第二次手术,问娘家人能不能去一个。根子叔说自己没钱,让二叔去,二叔耸着两道浓眉说,你没钱,我养了三个娃咧,更没钱!三叔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刚买的这个媳妇除了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外,还塌了大窟窿(方言,欠了很多债),我肯定去不了。
三兄弟商量好,不告诉三奶奶,怕她担心,只说孩子上学,姐姐要给他们做饭,回不来。三奶奶红着眼圈说,再走不开,也不能连家也不回吧?
后来,根子叔他们去乡里那部唯一的手摇电话那儿给琴姑姑的丈夫打了个电话,说已经做完手术好长时间了,能不能回老家来疗养一段时间。那边说,我跟你姐商量了不知多少次了,她说死也不回老家了。
最后没有办法,就在琴姑姑去世前一个月,根子叔叔他们三兄弟凑了钱让三叔作代表去了一趟济南。
据三叔回来说,琴姑姑其时已经瘦得一把骨头了,一双大眼睛深深陷在枯了的眼眶里,牙龈鼓突,牙齿瘆白,头上已经掉得没有一根头发了。听三叔的描述,我都在一边打冷战。
一个月后,我们琴姑姑的亲人们接到去给琴姑姑奔丧的通知。大家按琴姑姑的遗愿自始至终瞒着三奶奶。但是好像冥冥之中有感应似的,三奶奶说,不对劲儿,我咋感觉老不对劲儿了,你姐姐是不是有事?我连着好几天梦见她来到我床前说,娘,我走了,我对不住你。
根子叔强装笑脸说姐姐好着呢,是忙,回不来。
三奶奶从根子叔脸上捕捉到了那躲躲闪闪的不幸消息,哇的一声就哭了,我知道了,你们全都瞒着我,一个月前,三儿去济南,现在一大家子又去曲村(曲村是我琴姑姑的婆家),一定是你姐姐已经没了,你们这是去给她奔丧,是不是?
根子叔叔看瞒不住了,干脆对三奶奶讲了实话。三奶奶的两个眼珠子一下就直了,木木地往身后的石条子上顿去,说,还是走了,走了……一只芦花鸡不长眼地咕嘠咕嘠走过来,被我根子叔一脚踢过去,芦花鸡尖着嗓子喳地苦叫着,秃噜噜振翅飞上了土围墙上,歪着小黑脑袋打量着傻傻地自言自语的三奶奶和红着眼睛抹泪的根子叔。
也算蹊跷,三奶奶之前常常为见不着琴姑姑胡乱猜测而动不动哭鼻子抹眼泪的,现在已经确认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她反而不哭了,干着那双混浊的眼,自顾自地在那儿叨咕:还是走了,走了……
九
琴姑姑是火化后被她丈夫用一个黑匣子带回来的。丈夫按老家的规矩给她做了柏木大红棺材,棺材头那儿镶着她健康时的半身照。一头齐耳短发,把她那张瓜子脸衬得俏皮生动,她微笑着用那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瞧着院子里为打发她忙进忙出的亲人们。
他丈夫不时跟一个漂亮的女人商量着什么,一个同样长得漂亮的三四岁的小女孩拽着女人的衣角,不离她身边。
小女孩长得真是漂亮。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像一对宝石般散发着晶莹的光芒,双眼皮,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乍一看,让你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工精心雕刻出来的洋娃娃。
我趁她妈妈离开的当儿,走到她身边,弯下腰赞她漂亮,并问她几岁了,哪儿的?小女孩一点也不眼生,那张红艳艳的小嘴嘟起来,两嘴片儿一翻一覆,清晰地吐出了一串话。说她三岁了,家是济南的,这里是老家,还解释了一句,是爸爸的老家。她的话让我一惊,我本来还想继续往下问些话,被母亲喊着后家该上香了,让我赶紧归队。我用手把小女孩垂下来的头发往后面帮她撩了撩,就赶紧回到后家队伍里去了。就是这撩头发的当儿,让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小女孩脸左侧居然有一个瘊子!要知道琴姑姑的丈夫也同样有一个!而且俩瘊子的部位惊人地相似,只是小女孩的小一点罢了。当我再去打量那个小女孩,不得不悲哀地发现,小女孩居然有诸多与琴姑姑丈夫相似的地方。那脸型,那鼻子,甚至说起话来那口型、那语气都一模一样。
送葬回来的路上,我就跟母亲偷偷说了这事。我说这个小女孩会不会是琴姑姑的丈夫跟那个漂亮女人的孩子?琴姑姑所谓的癌症什么的,会不会俱是谎言?会不会琴姑姑是因为她丈夫出轨且有了婚外女儿被活活气死了?
母亲斥我道,小孩子家,别乱说!
我嘟哝着,谁乱说了,明明就是嘛!
就在我们都去为琴姑姑送葬的当儿,冬生舅舅又在家耍酒疯。他一大早起来,就一个人喝酒,等两瓶二锅头下肚,他又去开第三瓶时,被他媳妇拦住了,说,冬子你不要命了吗?我知道那个琴死了,你心里难过,但也不能往死了喝呀!你不想活,我们娘儿仨还想活呢!你死了,我们靠谁去?说着那泪珠子就往下落,嘀嗒嘀嗒打在她的花布衫上。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就连娶我也是找了个替身,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就是那个死鬼的替身!
冬生舅舅瞪着那双红眼珠子,伸着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吼吼着,你再说一声,再说一声死鬼,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媳妇吓得一跳脚跑一边去了。冬生舅舅身子一软,趔趄着倒下了。
是四姥姥张罗着把冬生舅舅送到乡卫生院的,医生说,喝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了,若送不及时,会没命的。他媳妇嘀咕了一句,那正好,他正好可以去追他那死鬼相好的了!
四姥姥白她一眼,斥道,胡咧咧个啥呢?没个媳妇样子!他媳妇小声嘟哝着,明明就是嘛!
十
杨树拐村一如既往地陷入了平静。
三奶奶还是天天忙着掇登(方言,抚养)二叔的那俩孩子,也帮着寡妇带那几个孩子。院子里照样跑着咕咕叫的鸡,一坨一坨的鸡屎让外来人没地方放脚。
冬生舅舅照样骑着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去乡里的供销社上班。
整个杨树拐村的人依然重复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习惯。
关于琴姑姑,在她死后,大家又议论了一段时间,当然包括那个冬生舅舅,那个漂亮女人和小女孩。
一段时间过后,又有了新的议论话题,关于琴姑姑也就不再提了。
数十年过去了,我们杨树拐村再也没有出过像琴姑姑那样美丽、那样手巧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