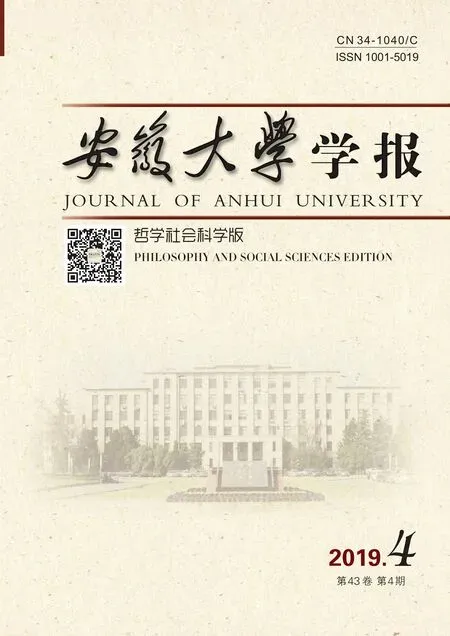一种愤而不悲的苏格拉底主义
——安提斯泰尼哲学新探
于江霞
一、安提斯泰尼其人及其“悲观主义”标签
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 of Athens,约公元前446—公元前365年)是古希腊出色的苏格拉底主义者[注]这里的“苏格拉底主义”(Socratism)主要指受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方法与实践的启发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哲学传统或路线。当然,不同哲学传统或路线之间可能存在“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很多学者将安提斯泰尼视为苏格拉底的正宗传人,而安提斯泰尼的苏格拉底主义也的确影响了色诺芬,更影响了后来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在现代常以昔尼克派创始人的身份而著称。作为苏格拉底最亲密的追随者(Xen.Mem. 3.11.17)[注]本文用DL指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英译本见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 by R. Hic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中译本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用Xen. Mem.指代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英译本见Xenophon, Memorabilia, trans. by E. Marcha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译本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用Xen. Symp.指代色诺芬的《会饮》,英译本见Xenophon, Memorabilia, Oeconomicus. Symposium. Apologia, trans. by E. Marchant and O. Tod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中译本见色诺芬《会饮》,沈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用t.表示S. Prince的Antisthenes of Athe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一书收录的文本。上述引文皆随文夹注。文中的翻译参考了相关的中英译本。,安提斯泰尼尤为捍卫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并被公认为是苏格拉底—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克拉特—芝诺这一思想传承链上的中坚力量。正如拉尔修所言,安提斯泰尼“为第欧根尼的不动心,克拉特的节制和芝诺的坚忍开辟了先河”(DL 6.15)。正如古人曾说苏格拉底本人都感叹柏拉图写了太多他未曾说过的东西(DL 3.35),现代哲学家波普尔则指责柏拉图背叛了苏格拉底,并称安提斯泰尼才是苏格拉底“唯一值得尊敬的继承人”[注]K.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The Spell of Plato,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1945, p. 171.。不管这一评论是否公道,它至少从研究苏格拉底主义的角度暗示了安提斯泰尼哲学的重要价值以及我们继续寻找、辨识和研究其著作的重要意义。
虽然安提斯泰尼极为高产,但他的大部分著作,甚至连残篇都未能保存下来,因此关于其思想的争论非常之多。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安提斯泰尼是否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鉴于他对人性、社会、知识等的激烈批判为古希腊人乃至后人所熟知,很多现代学者认为昔尼克主义者生平所遭受的不幸使他们迁怒于周身世界[注]L. E. Navia, Diogenes of Sinope: The Man in the Tub,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8, pp. 77-78.,创始人安提斯泰尼识人观世的态度尤其充满着夸张、悲观和忧郁的色彩[注]L. E. Navia, The Philosophy of Cynicism: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5, Ref. 258; S. Prince, Antisthenes of Athe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p. 390.。至于具体的文本依据,这些学者往往首先诉诸柏拉图的对话《斐多》。因为这篇对话曾提到这样一类人,他们由于缺少对人性的真正知识而最终沦到厌恶世人、厌恶论证的地步:
他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技艺而高度相信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是完全真实可信、可靠、值得信任的,但是后来却发现他其实是卑鄙、虚伪的。之后他对另外一个人也有同样的经历。……最后在持续的打击后,他变得憎恨每一个人,认为所有人都是不可靠的(《斐多》89d-e)。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悲观主义”标签。最一般意义上的反驳即是突出古今犬儒主义的不同。例如有些人就认为现代犬儒主义者才是消极厌世、玩世不恭,对人的道德能力彻底悲观,并因此在智识和精神上颓惰无为的,而古代昔尼克派则是积极入世,行事谨慎,对人性与教化持乐观态度,并为习俗的改良努力奔走的。这种观点作为一般性认识虽有其合理性,但它对以上诸文本的回击是极不充分的。因为严格地说,古代晚期昔尼克派中确实存在随波逐流(Bion of Borys-thenes)、闭言退隐(Secundus),甚至以死殉世(Peregrinus)之辈[注]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 77, pp. 111-112.。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对安提斯泰尼哲学的日渐重视和深入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安提斯泰尼并非是昔尼克派的建立者,而只是昔尼克派的先驱[注]D. Dudley, A History of Cynicism from Diogenes to the 6th century A.D., Chicago: Ares, 1980, p. 15. F. Sayre, Antisthenes the Socratic,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43, no. 4(1948), pp. 237-244. V. Tsouna-McKiraha, The Socratic Origins of the Cynics and Cyrenaics, The Socratic Movement, ed. by P. Vander Waerd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7-391. W. Kennedy, Antisthenes’ Ajax and Odysseus,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7. 这里的几位学者甚至倾向于认为安提斯泰尼都称不上昔尼克派的先驱。当然多数学者还是承认,安提斯泰尼的学说(还包括某些生活方式),以口头或著作的方式为第欧根尼的实践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Cf. The Cynics: The Cynic Movement in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 eds. by R. B. Branham, M.-O. Goulet-Caz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7.正如西塞罗所言,昔尼克派的来源是安提斯泰尼的学说,后者又以苏格拉底为榜样(《论演说家》3.17)。。进言之,除了具有昔尼克派的某些特质外,他还有其他思想面向和独特之处。例如纳维亚(Luis E. Navia)就认为,智者式的修辞学家、苏格拉底主义者、昔尼克主义者这三种角色可能分别在安提斯泰尼一生的不同阶段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他的思想尤其是后期思想则可能同时带有三者的某些特点[注]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reface, viii, p. 14.。

二、作为苏格拉底主义者的安提斯泰尼与“悲观主义”
作为苏格拉底最亲密、最年长的同伴和追随者,安提斯泰尼在很多方面都与苏格拉底极为相像,因此安提斯泰尼还有“苏格拉底主义者安提斯泰尼”之称(t. 122C)。最重要的是,他也写过一些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可能一度是雅典最杰出的苏格拉底主义者[注]K. Döring, The Students of Socrates, ed. by D. Morri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2.。另一苏格拉底追随者、斯多亚哲学家帕奈提乌(Panaetius)甚至宣称,在所有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中,他只能肯定柏拉图、色诺芬、安提斯泰尼和埃斯基涅的对话是真实的(DL 2.64)。很多现代学者也都坚持认为,安提斯泰尼首先是一个以认识自己、寻求真理和善为严肃使命的苏格拉底主义者[注]S. Prince, Antisthenes of Athens Text,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p. 11. 尽管有学者认为安提斯泰尼比柏拉图更准确地理解了苏格拉底哲学,并更忠诚于老师的学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受限于自己的智识,安提斯泰尼并没有领会更没有担当起苏格拉底的使命。Cf.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 66.,而且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很大程度上即是安提斯泰尼的苏格拉底[注]很多学者都认为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申辩》等著作可能受到安提斯泰尼的影响。Cf. A. Chroust, The Antisthenian Elements in the Two Apologies of Xenophon, Socrates, Man and Myth: The Two Socratic Apologies of Xenophon, 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 1957, pp. 101-163; L. E. Navia, The Philosophy of Cynicism: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Ref. 198, 200, 246, 248, 260, 278, 291.。这一点也可以在古代论者那里找到文本和思想上的支撑。如普鲁塔克(《莱库古传》30.6)等哲学家都称其为“苏格拉底主义者安提斯泰尼”,阿忒纳乌斯(Athenaeus)在提到安提斯泰尼时还说:“这只狗在很多方面都与苏格拉底相似”(《博学者的欢宴》5.216b)。即使是明确将安提斯泰尼视为昔尼克派的创始人,进而引起了诸多误解和疑惑的拉尔修,也认为柏拉图、色诺芬和安提斯泰尼是继承苏格拉底衣钵并因此被称为苏格拉底派的三个最重要的追随者(DL 2.47),并在安提斯泰尼所感兴趣的话题上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苏格拉底式底色:定义(DL 6.3)、 道德(DL 6.5)、德性、幸福和智慧(DL 6.10-6.12)等等。
我们也认为“苏格拉底主义者”是安提斯泰尼最重要的身份,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为了警醒和劝说世人,拨正社会乱象,他本人是以一种极端、“愤世”的态度实践并发展了苏格拉底身上的某些气质、品性以及生活样式,如物质上的贫乏、不动心、节欲和自足等。在他那里,苏格拉底对人们带有温和的讽刺的质问和对语言的辩证态度(既可为“毒药”,也可做“解药”)变成一种对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更为公开的、谩骂式的谴责和对语言、交谈的怀疑、否定。不仅如此,他对政治、宗教的怀疑和批判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形式[注]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p. 77-78, p. 90.。而他的很多著名悖论,都可以说是对苏格拉底问题(即一方面是对定义的探求,另一方面则是关于真正之幸福的主张)所做出的某种极端回应[注]S. Prince, Socrates, Antisthenes, and the Cynics, eds. by S. Ahbel-Rappe, R. Kamtekar, A Companion to Socrat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77.。但问题是,这些极端化倾向是否就代表他的思想是一种悲观主义呢?在我们看来,不管我们是否将苏格拉底视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注]我们显然不能忽略安提丰(Antiphon)这样的评论者,他认为苏格拉底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并因此称其为一个“教授不幸的人”(Xen. Mem. 1.4.3)。,安提斯泰尼所践行的苏格拉底主义都不能与“悲观主义”相挂钩。



作为从苏格拉底到斯多亚派的重要中间人物,安提斯泰尼的德性学说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他的苏格拉底主义。但这一复杂学说依然很难用“悲观”,尤其是“反智”加以描述。拉尔修、色诺芬等记录了安提斯泰尼及其追随者关于德性的一些重要教义。尽管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系统地重构安提斯泰尼的德性思想,但可以结合相关文本而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当然,除了对获得德性的潜能、“苏格拉底式力量”等的肯定外,安提斯泰尼的达观更在于他无畏地身体力行,其德性观念的整体物化之实即是由他自己所塑造的一个活生生的苏格拉底式英雄或贤哲。这种以实践为归宿,真正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践行的伦理学无疑影响了昔尼克学派。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它所蕴含的是一种乐观的教学法,其所强调的“德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尊重人性的、可实践的、有益的。
三、作为昔尼克派先驱的安提斯泰尼与“悲观主义”

首先,关于人性的讨论往往是相对于对动物性和神性的探讨而进行,在这一点上,安提斯泰尼并没有走昔尼克派的通路,即将动物和神作为道德典范而贬低人本身。因此与第欧根尼相比,他其实是将人性置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并对其表现出更强的信心。相较于将动物视为(与人相对立的)“他者”的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主义者在道德上对动物(如狗、老鼠等)地位的抬高(如将这些需少、求少的动物作为人的榜样)无疑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至少在表面上)。安提斯泰尼同大多数昔尼克主义者一样,也认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存在先天的截然对立。但与第欧根尼等人相比,他总体上还是将动物视为某种负面的模型,认为人如果缺少德性或哲学化的过程就会像动物(如驴、牛)一样(t. 54.14, 62, 63, 96, 189A-2)[注]S. Prince, Antisthenes of Athe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p.135.。与之相关的是,他还拒绝把希腊传统意义上的神视为某种高高在上的存在,这从他对女神阿芙洛狄特略带狂妄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另外塞米斯丢斯(Themistius)的演说《论德性》中的一段记述也值得我们注意:
安提斯泰尼说,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告诉赫拉克勒斯(Heracles):“你的努力完全是卑贱的,因为你追求人的事务而忽视照管比它们更重要的事情。在你学会比人事更尊贵的事情之前,你不会是一个具有完全德性的人。如果你学会了这些事情,那么你也将知道人事。但如果你只学习人事,你就会像野兽一样偏离正道”。(t. 96)




四、具有智者背景的安提斯泰尼与“悲观主义”

例如在安提斯泰尼的上述两个演说中,我们并未发现明显的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悲观主义论调。而且,鉴于其曾经的智者教育背景和在语言学上的造诣,他关于快乐等的一些看似极端的言论,很可能都带有修辞上的目的,尤其是当面临来自亚里斯提卜的快乐主义的挑战时。无怪乎我们在其他一些文本中发现,安提斯泰尼其实并不拒绝快乐,而只是主张享乐需要一定的前提或方式(如共同体、德性、苦干、不后悔等)[注]另有一些文本对安提斯泰尼有关快乐的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呈现:如果快乐不引起后悔,那么它就是善(t. 127A-B);“在没有和谐的酒会上和没有德性的财富里是没有快乐的”(t. 125);“我们应该将快乐置于苦干之后,而不是苦干之前”(t. 126)。塞尔(F. Sayre)甚至认为:“我宁愿发疯也不愿意拥有快乐”不是安提斯泰尼所言,这与他的品格不一致,这句话应该是“基督教时期的斯多亚派的一种病态狂热主义的表达”。Cf. 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 87, note 10.我们以为,塞尔或许给安提斯泰尼摘对了帽子,但不一定给斯多亚派戴对了帽子。。对于柏拉图的相论等的态度或许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源于其在哲学上的智识匮乏,而只是他故意为之[注]S. Prince, Antisthenes of Athe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p. 14.。这就提醒我们,应特别注意安提斯泰尼所擅长的情景修辞,乃至古代文本在对其思想进行记述、摘取时所运用的相关修辞手法,以尽可能地展现其思想原貌,并时刻牢记这种语言解读的局限性。


对习俗之见与事物本质之间的区分还影响了安提斯泰尼的神学观和语言观。如果真正的神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多神教的神或人格化的神,那么他很可能不像任何人或任何物,并且甚至是无法言说的、神秘的[注]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 49.。作为可能是最早用寓意解经法阅读荷马的思想者之一[注]L. E. Navia, Antisthenes of Athens: Setting the World Aright, p. 50.,安提斯泰尼越来越感受到语言的界限,感受到“言”与“意”之间的殊异。另一方面,他相信真正的修辞是通过行动显示、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DL 6.11)。所以他说自己从哲学中得到的好处就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能力”(DL 6.6)。这就在承继苏格拉底的“过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逻各斯相一致的生活”的教导的基础上[注]A. Brancacci, The Socratic Profile of Antisthenes’ Ethics, ed. by Ugo Zilioli, From the Socratics to the Socratic Schools: Classical Ethics,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51-52.,将自身的苏格拉底主义推向深处。这些观点和做法与其说是对语言的悲观,不如说是对语言和人的生存现实的一种深刻、明智的把握。
五、结 语
综上,安提斯泰尼并不是一位厌世、厌人、反智的悲观主义者。苏格拉底主义者作为安提斯泰尼最首要、最关键的身份,也是展现他的达观精神的最重要的窗口。其昔尼克色彩和智者的教育背景非但不与之相悖,而且还使得其所创立的苏格拉底主义显得愈加独特(甚至激进),并同样展现了其哲学的乐观元素。如果说《斐多》中的“苏格拉底”确实有所指,并且指的是有昔尼克派背景的人,那么这个对象更像是不在场的昔尼克派的创立者第欧根尼[注]据说有一次,当第欧根尼被问到他是否真的憎恨所有人时,他回答说,他憎恨邪恶之人的堕落,憎恨善良之人在道德堕落面前的沉默(Muntahab Siwan al-hikma, Diogenes 17)。Cf. L. E. Navia, Diogenes of Sinope: The Man in the Tub, p. 27.当然这完全是一个假设,因为第欧根尼是否悲世厌人,是否与柏拉图相识仍然是富有争议、尚需论证的问题。,而非在场的安提斯泰尼(《斐多》59b)。因为安提斯泰尼眼中的人与社会仍然是可治愈的、有希望的。他与柏拉图等人的人性假设和社会态度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他们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如在公开揭示人性事实和社会乱象方面,一个是以几无保留、有所夸张的方式,一个则是以有所选择甚至带有“哄骗”性的方式)示人,进而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教育规划。相较之下,安提斯泰尼对人事、对社会的态度或许有些乖戾或过于敏感,但他的判断却不无道理,他的发奋努力亦让人钦佩。不仅如此,他的傲世自足、勤勉苦干、重德重行等思想所投射出来的精神品性是积极向上的,其所倡导的自由、简约、自治、净心等精神元素则构成了现代人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综合其哲学气质、实践风格与品性特征看,他的苏格拉底主义其实是“愤而不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