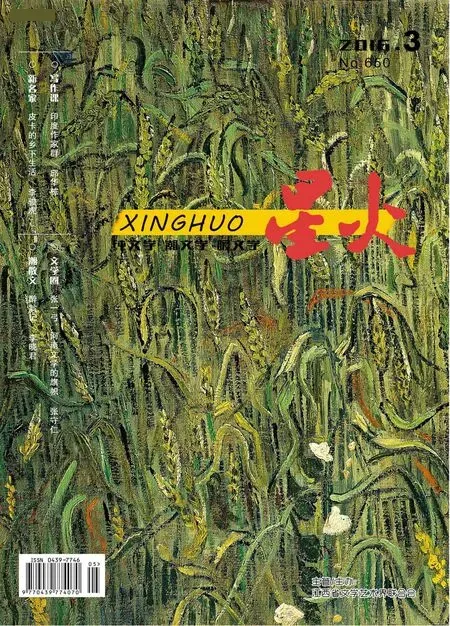我永远感激他们
——《名作家记》序
在首都文学界纷纷庆祝《十月》创刊四十周年、欢度这一文坛节日之际,不禁回想起1977年夏天,我、王世敏、章仲锷三人,在山东济南南郊宾馆商议出版一本大型文学杂志《十月》,以打破封冻的坚冰,吹响文艺的号角,迎接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到来。
王世敏当时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他办事果断,有权调配人力,回京后立即挑选黎汀等人筹备班子,组织稿件,请故宫博物院书法家写刊名。经过一年多策划,《十月》创刊号(当时以书代刊),终于1978年8月问世。这是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个大型刊物,新华社立即发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由于第一期登出了茅盾、臧克家、杨沫、李准的稿子,由我编发了刘心武冲破禁区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由黎汀在“学习与借鉴”栏目里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的一课》等赏析文章,故刊物大受欢迎,各地读者奔走相告。
紧接着佳作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十月》编辑部: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冯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羡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鬈毛》、梁晓声的《雪城》、高行健的《车站》……好稿多得用不完,佳评如潮。当时《十月》刊发的许多中篇小说被转载,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京剧、评剧,导致《十月》发行量节节攀升至六七十万,成为当时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读者来信堆积如小山,只能用一条条麻袋来装。公众场合人们常能听到议论《十月》新发的作品;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常提出要添购《十月》,以满足大学生们急切的阅读需要;湖北一位作家作品获奖,宝贵奖品竟是一本《十月》。《十月》成了文坛的精神高地。全国有百多家杂志,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春天、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两次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共有三十部作品获奖,其中就有十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十月》上,得奖数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专门撰写《致<十月>》一文,表扬“《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于2003年12月初写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说:“《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我经历了《十月》从创办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因而和众多作家有了频繁接触、深入了解的机会。我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无不涉及。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最使他们激动、最难忘、最擅长、最拿手的题材,他们因而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使《十月》在众刊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从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载过去了,“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我和他们打过交道的、给《十月》写过稿的,如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冯牧、陈荒煤、吴伯箫、李准、林斤澜、冯其庸、刘绍棠、骆宾基、张贤亮、张一弓、张天民、张笑天、余易木、章仲锷、史铁生、程乃珊、苇岸、胡冬林、张弦、张玲、秦志钰……先后离世。我时常怀念他们。
回忆往昔,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前辈们的嘉言懿行、为人为文,足资楷模。我牢记着在南方旅途中和汪曾祺共居一室时他对我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如水,波涌推动,前后相连,不可切割。我早年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打印过程中有一幕戏的原稿弄丢了,打字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安慰她,叫她放心,便坐在打字机旁,从那场戏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我所以能背,因为文章内流贯着节奏和韵律。”1992年春天,我和徐迟、王元化、丁宁、江波、涂光群、李天芳等十多位作家聚在深圳西丽湖畔度假,临别时大家排列在“创作之家”门前草坪上合影留念。78岁的徐迟年纪最大,竟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孩童般天真可爱,毫无大作家架子。我钦佩前辈师长们的学养深厚、知识渊博。1961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晚报》不久,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带领副刊部主任顾行和我到京西调查,寻找“燕山夜话”的素材和题目。他站在一幢古建筑废墟上,俯身捡起一块黄琉璃瓦碎片对我和顾行说:“琉璃瓦古称缥瓦,唐宋时代就有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者王子韶都在他们作品中提到过。除琉璃瓦外,封建贵族们还造过铁瓦、铜瓦、银瓦、金瓦。但底层老百姓只能在屋顶上铺上石瓦、竹瓦甚至稻草,有的甚至头无片瓦、足无寸土。可见即使一块瓦片,如对它深入研究,会发现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1991年4月,云南通冯牧任采访团长率领我们到彩云之南采风。参观玉溪北门街3号聂耳故居时,他竟如数家珍般给我们十多位作家当起了导游。他说:“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父亲聂鸿仪开过一间叫“成春堂”的小药铺。聂耳小时候爱听民间音乐,爱拉民族乐器,学谱曲子。后到了上海,1933年,他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根据田汉被捕前,匆忙写在香烟纸盒上的歌词,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我们如今大家唱的国歌。”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诗人骆一禾对《十月》诗歌栏目的创造性贡献。是他首先在《十月》上编发了海子、西川等名诗人的作品。海子铁轨上去世后,他奔赴山海关,料理海子丧事,接待、安抚他的父母,搜集、编定他的遗稿,积劳成疾,于1989年炎夏,以28岁的芳华青春,遽然离开了我们。我尤其感动于史铁生临死前捐献了自己的肝脏、角膜;又捐出脊椎、大脑,供医院研究。面对如此大爱,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才配赞美他那高洁的灵魂。我记起了爱笑的程乃珊在上海她那“蓝屋”“丁香别墅”般的花园洋房里,向我诉说家庭的重要:“人生在世,应该有个温馨的家庭。家好比是人的大后方、根据地。有了美好、和睦的家庭作为宿营地,一个人在外奔波,即使再苦再累,也无后顾之忧。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和谐的家庭,而能全神贯注于事业之中。我甚至认为,‘文革’中那些挨斗、挨揍的名人,因同时遭受家里亲人的斥责、批判,才走上自尽的不归路。”我赞赏京郊昌平的苇岸、吉林长白山的胡冬林,是他们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倡并实践土地伦理学,一生钟情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把它们视作亲人般精心呵护、百般珍惜……
2004年1月,我到芝加哥探望女儿、外孙时,接到文友李陀从安那堡(AnnArBor)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到他执教的密歇根大学一游。域外遇故交,我欣然前往,乘火车在雪原上穿行4小时抵达安那堡。李陀和他教比较文学的夫人刘禾等在车站上迎接我。当晚,寓所外朔风呼啸,我们在屋中围着壁炉,吃着烤白薯,回想设立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北京文学联络站的往事,以及我和陈建功走了许多路寻找到李陀在小西天附近平房里的家,听他朗读刚写出的短篇小说。那晚长谈中,李陀对我说,现代文学资料书一本本出得不少了,建议我写写当代作家的故事,记下他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创作特点。尤需注重时代细节,让当代文学形象化、具体化、鲜活起来,显示它的呼吸、脉搏和体温。把当代文学实况血肉丰满地详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是你和崔道怡、章仲锷等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全过程的老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那时至今又过了14载。直到今年才完稿的这本《名作家记》,实乃履约包括李陀在内的众多文友们对我的嘱托和我自己的承诺。
我所交往的、经历苦难的作家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身怀一腔爱国心。他们关切着可爱祖国母亲的命运,幸福着她的幸福,痛苦着她的痛苦。跟他们接触多了、深交了,我感悟到:所谓爱国,就是爱我们脚下的绿色土地(故有词语“国土”),爱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鹤,爱白鹤飞往的、远方黧黑的山峦,更爱锦绣河山上勤劳、实干的伟大人民。因此,我对那些以民为本、将自己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学园地里辛勤笔耕,且给予我温暖、友情和支持的作家朋友们,永怀炽烈的感激之情。
是为序。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