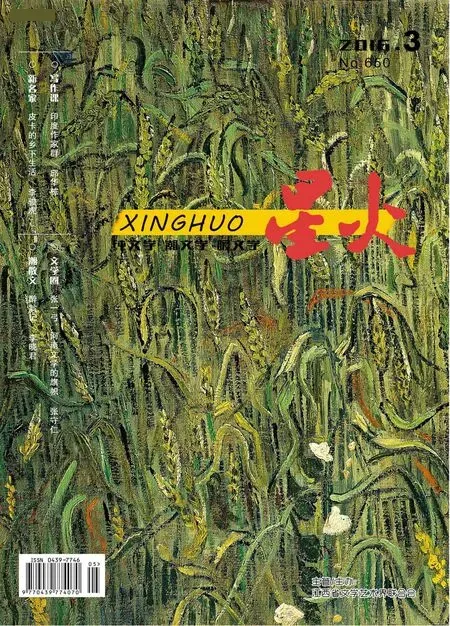去安陆看银杏树
○刘诗伟
1
安陆有银杏,李白居安陆。
每想及此,你的眼前就有一片白羽在金黄中飘逸。
公元725年,李白出蜀地,途荆楚,游历金陵及扬州,两年后来到安陆,落脚寿山。倘若彼时正值秋末冬初,城西白兆山冲坳的银杏黄了,艳阳婉风,绵延的黄叶逶迤成云,亦如摇摇荡荡的金鳞,而李白,必然行走在银杏树下。
树丛里的光芒犹如银线,洒落银斑,碎碎地晃移,晶亮而轻盈,发出沙沙细响,流溢着亲切又陌然的气息。李白像一片白羽,由冲口向山坳深处飘去。冲坡上偶有茅屋,一屋一屋的山民走到屋门口观望:以为那银的光线与光斑是李白的放射,直到李白拐弯消失,一切仍在闪烁,细响,并清晰地袭扰鼻翼。
没错,李白或许的确向来是白色的飘逸。
而且,彼时李白还不是后人描画的那个腆着肚皮的白胖子。年方二十七,未婚,黑发绾在头顶,眉且清目且秀,骨骼方正,满腹诗书,怀儒乐道,英气逼人;如此,穿着唐开元年间束腰的长服,两手反剪在背后行走,当然是很跩的。
所以那一羽白色注定要惊动安陆的金黄。
不久,李白“见招”并恋爱了。女方叫许宗璞,大户人家的千金;招见李白的是女方的祖父,退居安陆的前朝宰相许圉师。许氏宗璞如何美丽贤淑,没有直接描写的文字可考,后世的臆断之据有二。一是家族遗传。以许家的地位,定然代代择良女而婚,一茬一茬地遗传累积,加之锦衣玉食礼乐教化,宗璞姑娘岂能不佳?二是李白的美学。白乃诗人,美为信仰,鄙俗成癖,品位超凡,所以一见钟情,当是遇见了至美;有李白《紫藤》为证:“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至于李、许二人当年的花前月下眉目传情,或者青年李白怎样在恋人面前毛手毛脚,那都是人之常情,各人尽管去想象;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是个急性子,当年便结婚移居白兆山南麓的桃花岩下,次年生女儿平阳,隔年又生儿子伯禽。因为爱情,大约夫妻二人也时常去到白兆山上看景,向着旷野欢笑……
而今,白兆山上有一棵古老银杏,相传是李白与夫人许氏合手栽种的,科考1280多岁,恰好跟李白在安陆的10年对得上。
2
这么说吧,你的想象中规中矩并不奇诡:今人去安陆看银杏,一半是看李白看过的银杏,或者期待看见那个白色李白在山间看银杏咧。
乘车出安陆城,由一条顺溜的柏油路向西北行驶15公里,至白兆山下,从右窗望出,可见山岩上一间小小砖房,那儿便是李白当年的居所。宋代安陆人李道儒诗曰:“唯有桃花岩上月,曾闻李白读书声。”李白自道:“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只是,而今岁隔千年,时序初冬,放眼巡视,周遭空茫,既不见桃花红,也没有银杏黄,不由让人莫名沉诵:“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自然又不必颓伤,毕竟大片的银杏就在比邻白兆山的钱冲,那里是全国首座古银杏树国家森林公园。同车的“知道分子”正在讲述:所谓钱冲,因冲地银杏林广,盛产白果,白果养生,山民积果出售,累钱草贮,遇阴雨天票面生霉,待晴日,家家户户在台坡上晒钱,一阵风来,钱票漫天飞扬,堪比满冲银杏叶舞,故曰钱之冲。闻此,兴致陡涨,也就暂时忘却了李白。
不一会儿,下车投入钱冲。
此刻你的心绪还在山民的台坡上流连,目光已被一株蓬松的亮黄吸引。往深处走,黄色渐聚,眨眼间,便置身于连片银杏的冠盖之下。你身在云中不知云,单是觉得被疏朗空濛的金黄笼罩。你驻足抬头,看一棵银杏,看一片鸭掌形的黄叶,看它是怎样的黄和怎么就如此地黄。你当然无法明白。你也无法形容。你只晓得,那叶片很规整,如鸭掌,亦如美人扇;那黄色不是染上的,是长出来的,带着一种洁爽香气的生长;它的边缘尚有浅绿,他还在向着全面的金黄生长,包括把香气也生长得金黄。阳光从冠顶射下来,经了风,的确如银线和银斑,碎碎的,沙沙的,晶亮且轻盈。但你不是诗人,你被美得有些着急。你甚至也不再是普通的人,只是一片恍惚的感觉。你真的看见李白的影子在银杏树下晃了一下……
景深处,有一棵树龄3000多岁的“银杏王”,长在路边的近坡上;1280年前,想必李白来此观摩过它1720多岁的姿容。而今,此“王”高40余米,身干须四五个成人伸展双臂方可环抱。它的样子不再清秀,很是非凡;面对它,你会想:有没有比“伟岸苍劲”更了不起的词句呢?你当然晓得,它承载着3000多个寒暑易节,那是无数的日月轮换,风霜雨雪,禽啄兽啃,雷公震荡,野火燎扰,及至1939年日寇炸弹的损伤……而这一切李白并未全然见识。它的磅礴身干的下部已经死去一半,另一半在自己的尸骸中生长,可那尸骸并非累赘,却是它生命的陪护与支撑;它粗糙厚实的表皮一半以褐色呈现生命,一半以灰枯表达时光;它有巨大而异形的冠盖,顶部的枝叶仍在奋力向40米之外探望,低处生长的虬枝如蟒身触地跃起,中部更有许多枝条不小心地纠结却又礼貌错让;它长出的枝叶一派繁茂,因了冠盖之大且“冠盖”四季,竟然像地球仪,划分出叶片黄绿不同的区块……他怎么可以一边死去、一边活着?怎么如此不讲道理地生长与存在?
他是神?!
你看见树顶有几只鸟巢,树下挂着一圈祈福的红布条,许多观望者如你一样惊诧而困惑……你也看见了树干的豁口,豁口如室,其间摆一张方桌,桌上铺一方红布,红布上站一尊观音——你禁不住皱起眉头:既然是神,又何必用另一个神来装潢这神呢?
3
于是冒出问题:李白当年定居安陆跟银杏有关吗?
记忆中,李白诗千首,不曾写到银杏;向同行的当地专事李白研究的文友求证,文友不无遗憾地回应:或许李白的佚诗作中写过。你便想:白兆山上的那棵千岁银杏,“相传”由李白夫妇合手栽种,大约只能算作人们弥补遗憾的指认。事实是坚硬的,跟银杏相比,李白显然对安陆的桃花更为有感,不仅择桃花岩而居,而且反复诗咏桃花,比如“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桃李待日开,繁华照当年”“桃李今若为,当窗发光彩”等等。
而且,由李白的桃花诗可以探知李白的人生愿景及轨迹。那首《庭前晚开花》写道:“西王母桃种我家/三千阳春始一花/结实苦迟为人笑/攀折唧唧长咨嗟。”种桃栽李喻义培育和举荐贤能人才。写这首诗之前,李白出安陆入长安,得见诗人兼“天子近臣”贺知章。贺为李白才华风度倾倒,称太白先生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从天上贬谪到人间的神仙,立马推荐给皇上。可是,李白终究只做了一个“翰林供奉”,很不得志。不久,在返回安陆的途中,李白想到天庭中有一种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的桃花,不由寂寂喟叹。
可见,青年李白对仕途不仅念兹在兹,且深感怀才不遇。这也正符合李白的人生独白。说回公元727年,李白初来安陆居寿山时,著《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已然宣示自己“匡君济世”的政治抱负和“功成身退”的人生志趣,而桃花灿烂便是这愿景的写照。当时李白27岁,年纪不小了,除诗才斐然,一定深研过匡济之学,不然何以怀孔明志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求“君人南面”?无奈唐开元年间有科举无网络,而李白偏偏不喜欢科考,想走举荐路线,这就得全靠自己折腾了:有点像而今做咨询的人打广告,以待客户找上门来;或者类似艺人北漂,期望通过坊间周转找到舞台。事实是,李白去金陵及扬州空转了两年才来到安陆。
李白为什么没有直接返回蜀地却转投安陆?是无颜过“江东”吗?而安陆吸引李白的肯定不是银杏,且不说李白此际心不在娱,更何况安陆的银杏那时尚未名扬天下。符合实际的是,安陆有同族兄弟李令问和李幼成在,方便落脚;又能得到孟少府这等闻人钦慕,可以“亲承光辉,恩胜华萼”。此外,是否一开始就觊觎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呢?反正李白自信自带光环,果然很快就被许圉师召见,并与其孙女“闪婚”,做了“倒插门”。或许如此就算是为日后仕进铺路也不失节,但安州(辖安陆)裴长史对此很有看法:你李白既然自称与李唐皇室同宗,怎么可以跟凭借军功起家的许氏后人结婚?再者,你李白如果拿不出李氏“谱牒”,不说你冒认皇亲,也只能视为贱民,而许氏是良家,则“良贱不婚”。瞧瞧,全是混账逻辑。李白因此大为不爽,又是著文又是写诗,狠狠地辩驳和表白了一通。待事情消停,还得自己奔忙。以后,李白四度离开安陆,游历大江南北,直至长安,孜孜以求举荐,可惜均未如愿。
如是,李白便喝酒写诗,简直没工夫瞭望银杏了。
后来李白说他“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这“蹉跎”分明是指仕途无获。作为诗人,他在安陆10年留下诗文150多首(篇),其数量在一生的诗文中占比并不小,且多有脍炙人口的佳作;更为重要的是,这10年蹉跎出了诗仙的主体品格。
从钱冲银杏公园折返,去白兆山上的李白纪念馆,你见到了那个昂首挺腹、白衣飘飘、高举酒杯、意在天际的——谪仙!
4
当晚观赏安陆市“李白故里,银杏之乡”的文艺表演。舞台上,一个穿白服的老年胖子正举着酒杯醉诵《将进酒》,那模样和做派活脱脱是谪仙的翻版。你相信这是李白留给后世的意象。你听着《将进酒》,想起李白另外的诗句:“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可白兆山在李白之前并非名山呢。李白告别安陆时才37岁,依然年轻俊俏,远不是白须白服的大胖子。而安陆10年,他心怀儒念,怎么可能“笑孔丘”呢?他显然不自知:以他的仙风道骨做点“咨询”尚可,若干管理必定稀烂。但仕途蓬转,令他灰心,越发向佛乐道,借饮放怀,这才有了“将进酒”的态度;然即便如此,他也不做“竹林七贤”,照例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离开安陆后的25年,李白的命运大体是安陆10年的重复与叠加,幸好是谪仙,还有诗,一切命运都如酒一样化入身心,化作了诗篇,直至在采石矶向着江中的月亮奔去。李白啊李白!
你忽然觉得舞台上这个李白固然是省略了的李白,固然不曾吟咏安陆银杏,可他是一个真实的李白,他是后世一代接一代人的心理真实——是一个自由旷放的精神形象——一道永恒的风景!
这难道不是他一生未践的咨询的滞后效应吗?
恍然间,舞台上出现了你在钱冲见过的银杏满空的绚丽背景,一群少男少女在银杏树下跳舞。历史在现实中绽放。你的脑子里怎么就跳出了那棵“银杏王”。它比李白早到1720多年,它跟李白无关,它有它的命运。白天,“银杏王”的附近有一排做小买卖的山民,一位看上去年过花甲的妇女在砂锅里炒白果;你走过去,买一袋炒熟的白果,一边剥开了吃,一边很不厚道地做“田野调查”。你问:你们家晒钱吗?她先是一诧,即刻笑道:行市一阵一阵的,现在白果才5块钱一袋咧。你又问:那您还卖白果?她笑着:白果便宜了可它还是白果,有人吃呀。你转头看别处的摊点,几乎所有摊位上都有白果,卖白果的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站或坐,或贩或观,都在银杏树下,他们不是舞台上的舞蹈,但他们是与银杏同框的景致……
那是由质朴生命点亮的生意与灿烂!
至此,你确认了安陆的两道风景:李白与银杏。他们之间是月亮远照大地,是彩虹跨越山河,是花香飘过骏马,没必要臆想他们的日常交际或牵扯,他们就像安陆与黄鹤楼或者月亮与星星的存在——虽然是不相干的并存,但李白写没写银杏诗都是千年诗仙,银杏有没有李白的探望都是万年景色!因此,不用遗憾李白没有为银杏写诗,不用猜测李白是否去过钱冲,甚至不用“相传”李白携夫人在白兆山上栽种了那棵银杏。安陆在中国的时空里写着:
有的人死了,李白还活着;
有的树死了,银杏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