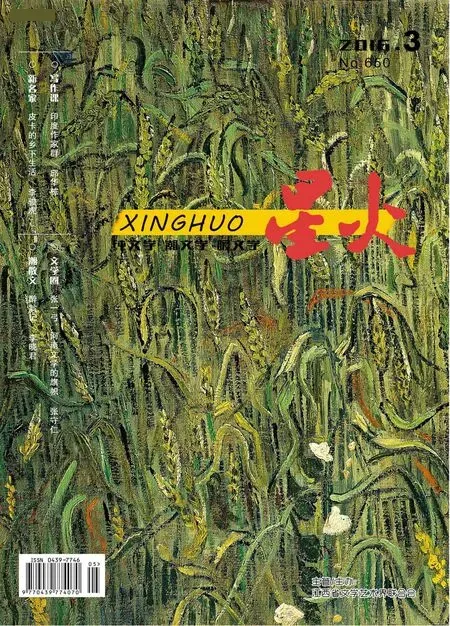三 婶
○南 雪
三婶是个闲不住的女人。
正月的元宵节一过,三婶就忙着扛起锄头挖土准备种菜了。这个时候,离种菜还早着呢!但三婶是个闲不住的女人,正月里窝在家里闲了半个月了,都差点闲出病来了,再不去活动活动筋骨,怕是真要出病呢。其实,不管是辣椒,茄子,黄瓜,丝瓜,苦瓜,豆角,西红柿,此时挖土种植都还嫌早了。不过,三婶等不及了。三婶背了锄头就来到村子后边的菜地开始挖土。这块菜地其实也是已荒掉的没人种的良田。三婶一锄一锄地挖,又把挖起的土块用锄背捣碎,再除去杂草。
三婶一个人在田里干得起劲。这些年,都是三婶一个人种田,一个人种菜。柳村再没有第二个人种田和种菜了。村里年纪跟三婶差不多的女人和男人都喜欢每天在柳村的祠堂里消磨时光,在里面打打扑克,搓搓麻将。她们反对三婶种田,种菜。她们说三婶,你又不是柳村日子过得最紧的,相反,你三婶家日子在柳村富裕得没几家比得上。你还那么起劲地干活干吗呢?你又不愁吃,不愁穿!但三婶习惯了,几十年勤快惯了,懒不下来,停不下来。别人是理解不了的。
三婶不会打扑克,也不会玩麻将,三婶可能是村里唯一一个不会打扑克玩麻将的女人。这也没办法,三婶学过,但老是记不住,年轻时没学会,到老了就更学不会了。但三婶不觉得丢人。这有啥好丢人的呢?
三婶打工回来在家里十年了,十年前她也到温州打过工呢。三婶一边挖土,一边就想起在温州打工的情景。如果不是干洗店的老板经常挑剔她,为难她,她恐怕现在还在那儿打工呢。
当时,三婶在温州信河街找了个干洗的工作,干洗店就她一个员工,有时候老板娘过来帮帮忙。信河街在温州可是一条著名的街道,街上的人家大多在乡下开了厂,都很有钱。这家干洗店生意很好,整条街的人家都拿衣服过来干洗。老板以前是个唱戏的,戏班子散了之后就吃老婆的闲饭了,他老婆就开了这家干洗店。
三婶在这家干洗店做了十几年,刚进去的时候,老板娘还年轻,到后来,老板娘老得不像样子。老板竟然打起了三婶的主意。三婶在这家干洗店包吃包住,睡在一个夹房里,只有七八平米。那天老板娘有事没回来睡觉,老板走进她房间,丢给她一千块钱,要睡她。三婶赶紧把钱丢回给他,叫他出去,再不出去,她就叫人了,老板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睡在隔壁。老板怕三婶真喊叫起来,就悻悻地走了。老板从此恨上她了,总是给她难看的脸色,也总是挑她的毛病。四十五岁那年,三婶提出不干了,回家种田去。老板娘很喜欢三婶的勤快,舍不得三婶走,问她为什么要走,三婶不想让他们夫妻吵架,只说在这里不习惯,在家里种田种习惯了。
开始的时候,柳村还有一些人陪着三婶种田和种菜,但慢慢地,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三婶把土挖好,正月也就过去了。无论是村前的田野,还是村后的田野,三婶成了一个孤独的耕种者和守望者。
二月初,天天艳阳高照。三婶的手又痒了。她想起了山上拇指粗的青青翠翠的小竹子。三婶年轻时几乎天天与这种小竹子打交道,十岁时,就学会了把这种小竹子破成小篾条织成斗笠和扯猪草装猪草的竹篓。
三婶织的斗笠最好看也是质量最好的。织的速度也最快。装猪草的竹篓比较粗糙没多大关系,但斗笠要精细,因为戴在头上,既是人们防雨的工具又是头部的装饰品。
斗笠这种东西已经消失了几十年了。扯猪草的竹篓也消失十几年了,因为,柳村这十来年没人养猪了。但买菜的小竹篮子还是很有市场。不过,三婶这些年也没卖过了。她只是想着这么好的天气,山上的小竹子一定长得很茂盛,很可爱。她的手就隐隐地发痒了。三婶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上山砍些小竹子,织些小竹篮放在家里,并不是卖钱,有哪个女人来串门,看中了可以随时拿走。
三婶从小就喜欢这些小竹子。这些小竹子对三婶来说,确实有一股难以割舍的情感。
三婶小时候家里穷,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所以三婶没念什么书。小学只念了一年,父母就不让她念了,要她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后来都念了高中。
三婶其实不蠢。她心灵手巧得很。那个时候还是搞集体,十岁的三婶每天把织的斗笠和竹篓子交给公家,可以抵七分的工分。男人做一天是十分,女人做一天是八分,三婶的七分相当于一个女劳力了。
三婶十四岁那年,集体解散了,村里把田地山分到了各家各户。三婶织的斗笠和竹篓子也可以自己拉到圩场上卖钱。那时候三婶浑身都是劲儿,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候市场上卖得俏,都是整夜地织。那些年家里的生活开支和两个弟弟的学费都是三婶一双手织斗笠和竹篓子挣来的。
后来,三叔到三婶家相亲。都是农家的苦孩子,两个人都同意了。三婶用自己的双手织来了自己的嫁妆。
斗笠和竹篓陪伴了三婶的少年和青年。她都记不清那时她织了多少个斗笠和多少个竹篓子,怕都有好几万吧。
现在每年三婶唯一还在大量干的活是用芦苇秆织成扫帚。现在芦苇秆织成的扫帚每把在市场上卖到十元,是热销货。
芦苇秆织扫帚容易,坐在家里,三婶一天可以织几十把。就是上山采集芦苇秆十分辛苦,爬山越岭,而且芦苇叶子容易把手割伤。一天能采到十把扫帚的芦苇秆就挺不错了。
芦苇在八月成熟,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三婶坚持每年这个时候天天去采芦苇秆。
这照样招来一些女人的闲话,有骂她是想钱想疯了的,也有骂她太贱了的。但三婶好像没听到这些,她喜欢劳动,喜欢做这些工作,喜欢劳动还有错吗?村子里以前也有好多女人跟着三婶去山上割芦苇秆,但慢慢地跟的人少了,最后只剩下三婶一个人。
去年,三婶是一个人去山上割的芦苇秆,割回来就摆在屋前屋后暴晒。最后,晒干的芦苇在堂屋里堆成一座小山。从芦苇秆上飘下来的芦苇花散满了一地,像是下了一场白白的雪。
不过现在离割芦苇秆的时节还早着呢。还只三月,离稻谷下种也还有一个月呢。三婶刚嫁过来的时候,柳村是种双季稻,早稻和晚稻,那个时候种田特别辛苦,刚刚把早稻收回来,又要把晚稻插下去,俗称“双抢”。也就是抢季节的意思。晚稻种晚了,到了初冬,经历了寒露风,就会颗粒无收。随着村人们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在家种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十年前三婶从温州回来,就发现柳村人只种中稻一季了,都不种早稻和晚稻了。但就是种中稻一季,柳村也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到这些年,除了三婶,再没有第二户人家种田了,就连中稻也没人种了。没划算是他们最大的理由。可是村子里也还有许多五十多岁还能种田的人啊,就是没划算,多少还是有钱赚的。再说了,现在种田也没有以前那样辛苦了,现在有耕田机、收割机,不像三婶刚嫁过来时,一担一担谷子都是踩打谷机死劲地踩出来的,那地也是一头牛不停地吆喝耕出来的。三婶看着村前村后不错的良田荒了实在太可惜,就种了十五亩田,这十年都坚持种了下来。
还是清明刚过,离稻谷下种还早呢!现在三婶只想着山上青翠翠的小竹子。三婶换了粗布旧衣服,穿了上山才穿的解放鞋,拿着柴刀,上了山。山上树木密布,郁郁葱葱,在一些阴暗角落,小竹子如豆芽般地长着,密密麻麻的。几十年没什么人上山打柴了,山都快成了原始森林。蓝天,白云,青山,阴沟里的小溪潺潺,各种鸟在树林间欢快地跳跃鸣唱,唱得三婶的喉咙都痒起来了!
柳村毗邻湖南省,是赣西的边界,所以旧时称柳村是吴头楚尾的地方。三婶不是赣西人,而是湖南那边的人。也就隔一座大山而已。三婶年轻时,村子里办了个花鼓戏剧团,三婶唱过两年旦角,扮相俊美,唱腔甜爽,深受四周乡亲的赞美。后来是因为父母嫌没人干农活挣工分,就不让她去唱了。五十五岁的三婶再没有年轻时唱花鼓戏时那股激情了。但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一点也不减当年!她真的想在这无人的山上唱几段花鼓腔调,可是,时间真的过去太久了,她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的力气也大大不如年轻时候了。一根根拇指大小的青翠竹子,像一个个站直的士兵,笔直得可爱。三婶把它们一根根放倒。然后把竹子的枝桠剔去,削成两米多长一根。再然后把竹子捆成一捆。三婶背着竹子回到了家里。
到了家,三婶就开始破竹子。咔嚓咔嚓破竹子发出来的声音是那样熟悉亲切!三婶似乎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她做闺女的时候。
那时候村子里的姑娘嫁出去,都是自己去山上砍来这样的小竹子,织成斗笠和竹篓子卖钱,置办自己的嫁妆。在所有和三婶年龄差不多的姑娘中,三婶的手艺是最好的。别的姑娘一天织三个斗笠,三婶织五个。如果早起晚睡她就能织七个。织斗笠时,赤脚踩在上面,勾着头,翘着富有青春气息的臀部,一双细嫩的手指穿梭似的在篾条间绕来绕去,一会儿一个斗笠的形状就跳跃着出来了。她们还别出心裁地在斗笠的中间加些好看的图画。
现在,三婶年纪大了,眼睛不如年轻时候,速度已慢了一半了。她不由叹了一口气,唉,老了。她破了一会儿竹篾,对自己的成绩十分不满意。又摇头叹息了几声。
三叔在村子的祠堂里和那些老女人打牌。也就赢输几块钱的样子。那天三叔一天赢了五块钱,就高兴地回家在三婶耳边吹嘘他牌技如何厉害。三叔以前也在温州打工,是一家家私厂的木工主管。今年六十一岁了,早几年就没去打工了。三叔加入了柳村老年人协会。祠堂就是柳村老年人协会中心。
三婶破了一会小竹子,才想起该做午饭了。等会三叔回来又要说她在家里饭都不晓得做。孙子和孙女在儿子那儿读书。儿子在浙江义乌打工,进的是家私厂,工资这些年还可以。
三婶停了破小竹篾,起身去厨房淘米煮饭。想起孙子孙女这会儿在外面也该吃饭了吧。他们的娘在一家工厂做文员,晚上不加班,下午五点就下班,然后在马路上等儿子女儿。学校有校车每天早晚开到小区门口。
三婶脑海里浮现出儿媳妇在马路边等孙子孙女的情景。
三婶对这个儿媳妇是相当满意的。儿媳妇不是本地人,是儿子在外面打工时认识的。但文化水平比儿子高了几截呢!儿子才初中毕业,不过是有一门木工手艺,又吃得苦,能说会道,能把树上的鸟儿说下树来。儿媳妇是大专生呢,不是比儿子高了几截么?
儿媳每年回家过年,一进门就说三婶许多不是的地方,什么三婶不讲卫生,什么三婶头发乱糟糟的,也不喝开水,身上的衣服也不干净,总之,一大堆呢。三婶真是怕了这个儿媳妇呢。儿媳妇回来了,她的头发再也不敢乱糟糟的,也不敢再喝生水,老老实实地烧了开水,衣服也换得勤了。但儿媳妇不在家的日子,她就自由了,又恢复她的习惯。还很为自己鸣不平:喝什么开水?每天还要烧水,多麻烦!自己不是喝生水喝了几十年吗?也没喝出什么病出来!乡下老女人哪有精力花在头发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狐狸精去勾引谁呀?!因此儿媳妇和儿子一家走了,三婶又恢复她的那一套生活习惯。
儿子原先在村子里谈了一个姑娘,那姑娘肚子里也没什么货,成天冷着个脸,半天也不会放出一个屁来。是只闷葫芦。外表也比现在这个儿媳妇差远了。可世上的事情就有那么怪,那姑娘还看不上三婶儿子!儿子带着礼品聘金前去相亲,碰了一鼻子灰。幸好那次相亲没有成功,不然,娶个闷葫芦进来有啥用?
三婶做好饭菜,三叔骑摩托回来了。三叔说:“儿子刚才打电话回来了。”三婶笑着说:“该不是又说我种田的事吧?”
三叔道:“还正是说你种田的事情。儿子说,柳村都没人再种田了,我们家又不是比不上人家,干吗还要种?!儿子觉得他脸上也无光。”
三婶道:“哟嗬,这是什么世道啊,天天去祠堂里玩乐就是荣光了?种田倒还丢人了?!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今年还要种,我身子还吃得消。”
三叔道:“你真是个傻婆娘。何必呢?你不种田,儿子多寄五千块钱回来,还不是一回事。种田又不是不要力气。”
三婶道:“我知道要力气。可现在有耕田机、收割机,轻松多了。那么好的一片田,不忍心看着它们荒掉。”
三叔说不过三婶,只好由着她。三叔吃完饭就又骑着摩托回祠堂打牌去了。
儿子和儿媳妇在今年出门的时候特意交代三婶,叫她不要种田了。村里好多条件比我们家差得远的他们的父母都不种了,你要是种,就是给我们丢脸了。三婶不明白这个道理,在家种田还给儿子媳妇丢脸了?!三婶笑嘻嘻地说:“好啦,今年不种了,今年真不种了。”但三婶心里才不这样想呢。
三叔走后,三婶一个人在屋子里想,我才五十五岁呀,我身子还硬朗,还能劳动,我为啥不要种田了呢?再说了,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又在外面买了车,还要还房贷车贷呢。
吃完中饭,三婶又去村子前面看那片稻田。十五亩上好田,又离村子这么近,荒掉真是可惜。三婶觉得那些已经荒掉的大块田就像一个个弃婴被种田人抛弃在那儿,正孤苦伶仃地在那儿流着眼泪呢!
三婶站在马路上。村子里那些在祠堂玩乐的女人吃完了饭又往祠堂走去。她们看见三婶,问:“你看啥呀?今年还种田呀?!”
三婶说:“看看田。种,今年还种。”三婶看不惯这些女人们,当中有些年纪比她还小,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就学着过去的地主婆那样不种田了,两口子整日在祠堂里玩乐。
那些女人听三婶说今年还种田,就哄地笑成一片,摇头晃脑地走了。“真是有病!这女人!”“她是骨头贱,不劳动就活不了。”“越有钱的人就越贪。”
各种难听的话飘进三婶的耳朵里。
但三婶一点也不难过。第二天,三婶瞒着三叔去街圩上买了十多斤杂交中稻种子。卖肥料的老板开着一车肥料进村子,三婶又瞒着三叔下了一千五百斤复合化肥。
在说三婶种田有病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姬,年纪比三婶小,今年五十来岁,个子也和三婶差不多。王姬两口子早不种田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两口子整日里就在祠堂里乐呵着,一点也不替外面打工的儿子着想。
王姬的儿子在外面谈了一个女朋友,孩子都有了。女方的父母要求也不高,让王姬两口子出个一万块钱,就把女儿嫁过来。可王姬两口子一万块钱也掏不出,向亲戚借,也没亲戚借给她们。有在祠堂玩的工夫,两口子种十来亩田,这五六年过去,一万块钱也早就有了。女方的父母也真是通人情:一万块钱还包括做酒席的钱和嫁妆在里面,人家得垫上好几万呢!
王姬的儿子呢,有了女朋友,又有了孩子,还管家里要钱。可王姬两口子却在祠堂里玩得心安理得。村里像王姬两口子那样的有不少。要是换成三婶,早把事情解决了。
农历三月,下过一阵小雨,山上拇指大小的小竹笋就破土而出了。小竹笋扯回来,剥去壳,伴上腌酸菜,是一道新鲜美味的野菜。但村子里的女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山上有大把的小竹笋。其实不是她们忘记了,是她们已经吃不得这种苦了。扯小竹笋要爬山越岭,又要在荆棘中穿行,十分辛苦。那些可爱的小竹笋往往就生长在荆棘丛里。
三婶没有忘记山上可爱的小竹笋。三婶还能吃这种苦。
三婶换了衣服和鞋,背着竹篓子,翻山越岭,去扯小竹笋。村里的女人听说三婶去扯小竹笋了,就在她家等着她回来,然后抓一把回去尝尝鲜。王姬已经在三婶家等了好多次了,每次抱走的小竹笋都要比别的女人多一倍。
这些女人只有在得了三婶好处的时候才不会说三婶的怪话。但过几天,三婶在她们的眼中,又成了那个不正常,脑子有毛病的女人。
农历四月,大山里的杨梅熟了。这杨梅也知道躲避懒惰的人。它不长在屋前屋后的山上,它偏偏要长到几十里路远的大山里去。
去大山里摘杨梅也是十分辛苦的劳动。天不亮就要起床,晚上就要把第二天中午的饭菜备好。来回四十多里的山路,到了山上也就吃中饭了。吃完饭得赶紧摘,摘满一竹篓子,天就黑了,又得赶着回家,到家也就是晚上八九点了。
早些年,还有一些女人跟着三婶去摘杨梅,但这几年,又只剩下三婶一个人了。
三叔不让三婶去。但三婶不听,不去摘几次杨梅,她就觉得这个夏天过得没意义。三婶是偷偷地背着三叔去的。天还是很黑的时候,三婶就打着手电筒上路了。走了三个多小时,三婶才走到大山里。一棵棵杨梅树挂满了红红的杨梅果。满树的杨梅果都在笑嘻嘻地等着三婶呢。它们像盼亲人一样地盼着三婶已经很久了。这些杨梅树也是很怪,把它们移植到家里,结出的杨梅果酸得不能吃。只有在这大山上,它才是又酸又甜。
这些杨梅果挂在树上如果没人来摘那真是太可惜了。三婶是不忍心让它们挂在树上。挂在树上,它就不叫杨梅果子了,只有把它们摘下来放到祠堂里让人们品尝,它才叫杨梅果。
好多女人边吃三婶摘回来的杨梅果,边说三婶好傻:“你个傻瓜,猪脑子!这几十斤杨梅带到县城去卖,十几块钱一斤呢!”
这些女人就是这样,吃了三婶的杨梅果,还骂三婶是猪脑子。这个世上一切助人为乐的人都是猪脑子。三婶不傻,三婶知道这大山里的杨梅能在县城换回一两百块钱,但三婶不缺这点钱。她就是要放在祠堂里,让大家品尝她的劳动果实。
可这一次,都晚上十点了,三婶还没有回来!这可把三叔急坏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是三婶在大山里出了意外,儿子会把他骂死。三婶娘家的人也不会放过他。
三叔一家一家地问,看是不是有别的女人跟着三婶去大山里了。三叔问遍了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没有。三叔拖着本来就受过伤的腿差点就要哭出来了。三叔以前在温州打工的时候,有一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不小心被一辆迎面而来的三轮车撞了,右腿骨折。好了,但一到阴雨天气,右腿就会疼痛。三叔拖着疲惫的病腿回到家,焦急地等待着。房间里的钟响了十一下,三婶还是没有回来。三叔觉得不能再含糊了,他拿来手机开着手机上的手电,往村主任家走。他只有让村主任给派出所报警了,让他们帮着去大山里找人。
三叔到了村主任家,村主任已经睡了。三叔把村主任叫醒。村主任揉着惺忪的睡眼说:“说吧,你有么子事情?!”
三叔说:“我婆娘丢了!”
村主任笑了,“你这么大的一个男人,怎么会把婆娘弄丢了?!”
三叔道:“她今早就去大山里摘杨梅了,现在还没回家。”
村主任从床上跳了起来“你怎么不早来找我?!”
村主任也感觉事情严重了。三叔说要不要给派出所报警?三叔腿有病,去不了大山里。村主任说他带几个人进大山里去找,明天再报警。
村主任他们在半路碰到了回家的三婶。她全身都被雨水浇透了。原来大山里下了大雨,三婶因为在山洞里躲雨,耽搁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三婶感冒了,发起了烧。但她还是坚持把一竹篓杨梅放到祠堂里。跑得最积极的是王姬,她穿着两寸高的高跟鞋比谁都跑得快!她抓了一大把又一大把放进衣兜里。三婶终于坚持不住了,晕倒在祠堂门口。
布谷鸟鸣叫的时候,已是农历四月。柳村的人们已经对节气没反应了。什么鸟叫也跟他们没关系了。但三婶还对节气有着敏感的反应。最迟到立夏后几天,稻种就要下水了。稻种下水催芽,几天后就要播种了。
田野里还是只有三婶一个人在忙碌着。
十来天后,稻秧苗已出现鹅毛黄了。三婶每天都要去看几次稻秧苗。二十来天后,稻秧苗就已经绿油油一片了。三十天后,稻秧苗就可以插到稻田里去。
到了插秧的时候,三婶四点钟就起床。她扯好几担秧苗的时候,天才亮了。
如果是太阳高照,三婶就头戴草帽,如果是下雨的天气,三婶就穿雨衣。路上的人照样对三婶指指点点,都说,这个女人是要作死呢。三婶才不去管这些话呢。这十五亩田她每年都种了下来。她不在乎别人说她是有病,说她是自讨苦吃。
三婶勾着头,左手握着秧苗,右手飞快地把秧苗插进泥土里。三婶的插秧技术是柳村人公认没人比得上的。又快又好。这也是在娘家做姑娘时练出来的功夫。三婶娘家田多,一个人四五亩,田多你不手快根本就赶不上季节。任何事情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转眼到了农历八月。山上的芦苇成熟了。一根根芦苇秆伸出长长的手臂,似乎都在等三婶把它们请回家呢。芦苇穗子也早就绽开了。三婶的手也开始发痒了。她换好衣服和鞋就上山了。上了山才知道,她不该穿件灰色上衣和灰色裤子,因为灰色衣服太容易吸收热量。三婶没想到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一年的秋天是几十年来从没出现过的炎热。
三婶割了不到十分钟芦苇秆,就感到一阵滞息难受,浑身汗如雨下,心跳急剧加快!这是从来没出现过的情况。很快她就浑身绵软无力。三婶瘫软在地上。在仅有的一点意识里,她知道她不该穿灰色衣服!她是中暑了!地上的湿气慢慢让三婶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三婶再也不敢怠慢,也顾不得羞耻,反正这山野里也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个人类。三婶把上衣脱了,又把背心脱了,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三婶的两个已经没有了弹性的乳房压在草地上。草地的湿气慢慢地穿透进三婶的身子。十几分钟后,三婶的心跳才正常了,那种心悸的感觉才消失了!三婶知道,是大自然救了她。要是没有这片草地,三婶可能再也下不来山了!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三婶有些气馁。她才觉得自己确实是一个有“病”的女人。后来,太热的天,她就再也不敢去山上割芦苇秆了。
三婶请了收割机,把十五亩的稻谷都收割了。一车又一车的稻谷被装进村子,装进三婶的屋子。柳村的女人这个时候才眼红了,才后悔了!不该在祠堂里虚度光阴,看看人家三婶,种了那么多的田,到时候把粮食卖了,大把的红票子又到了腰包里了。她们这个时候对三婶除了羡慕还有些妒忌。
三婶把稻谷晒干,一包一包背进里屋,就等着收粮贩子来收粮了。十五亩田,一百五十包稻谷。算九十元一包,总共也有一万三千五百元。成本算一半,三婶挣了七千多元。
三婶没文化,现在的粮贩子想着各种招儿欺骗顾客,所以卖粮的事情就交给三叔了。
三婶收完了稻谷,又忙着去菜地种菜。下雨天,种不了菜,三婶就在堂屋里扎芦苇扫帚。扎芦苇扫帚不是难事,最难的是最后的收尾。从收尾可以看出一个女人是不是心灵手巧。粗鄙的女人在最后收尾时,就可以看出扫帚收得不像样子。但三婶扎的芦苇扫帚收尾收得非常漂亮,每一根有序地穿插,最后形成一个球状,再用剪刀剪平,球状的扫帚尾就非常大方好看。用起来也舒服。所以三婶扎的芦苇扫帚是很畅销的。
三婶把冬天的菜都种上了。可是很不幸,那天去赶一头在她菜园里吃菜的牛,不慎摔倒跌了一跤,把右腿摔伤了。三婶住进了县人民医院。三叔对三婶说:“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儿子和儿媳妇?”三婶说:“告诉她们干吗?又不是很严重。”
收粮的粮贩子来了,他们知道柳村就三婶种了十五亩稻田。可是三婶和三叔都在县城。这个时候三婶已经出院了,住在儿子买的房子里。父亲打电话给三叔,说收粮的贩子来了,你们卖不卖?
三婶就叫三叔回去卖粮。说她在县城自己能料理自己。
三叔就回来了。
但三叔很惶惑。因为这些粮贩子是很不好对付的。说得难听一点,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你根本就防不胜防。比如,趁卖粮的人不注意,偷着把粮食背走,比如在电子秤上做手脚。口袋里带磁铁是家常便饭。
来收粮的粮贩子一共有五个人,但只有一个是老板,其他都是打工的。有一个是女的,可能是专门联系客户的。收粮老板带来的是电子秤。每次秤两包。每一次都是一百八十斤左右。每秤完一次,老板就在纸上写一行数字。共秤了七十五次。每年都差不多,都是一百五十包的样子。但这一次有些奇怪。每年都是一万三千元多些,但今年却只有一万一千元。很显然粮贩子做了手脚。但三叔就是弄不明白,粮贩子是在哪儿做了手脚。三叔借来了杆秤,和电子秤数量是一样的。说明电子秤是没问题的。可是,收粮贩子是在哪儿做了手脚呢?三叔把老板记数的纸条留了下来。收粮贩子都走了,三叔还在研究。
三叔研究了半天,终于研究出问题在哪儿。纸条上少了十二行数字。七十五行数字只有六十三行。收粮贩子少记了十二行数字。这些钱三叔是要交给三婶的,这是三婶的辛苦钱。可是该怎样跟三婶说呢?钱是要不回来的,收粮贩子早就走了。
三叔还是鼓起勇气,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三婶。三婶如晴天遭了一个霹雳!这是她起早贪黑的辛苦钱,收粮贩子轻松地就骗走了她两千块钱!这些黑心的收粮贩子!三婶难以咽下这口气!收粮贩子是外县人,三婶就是爬也要爬到他们家去。
三婶一瘸一拐地下了楼,她试图跑起来,可是,刚一迈步,整个人就踉跄地摔在地上。滚热的泪水从眼窝汹涌而出,三婶终于放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