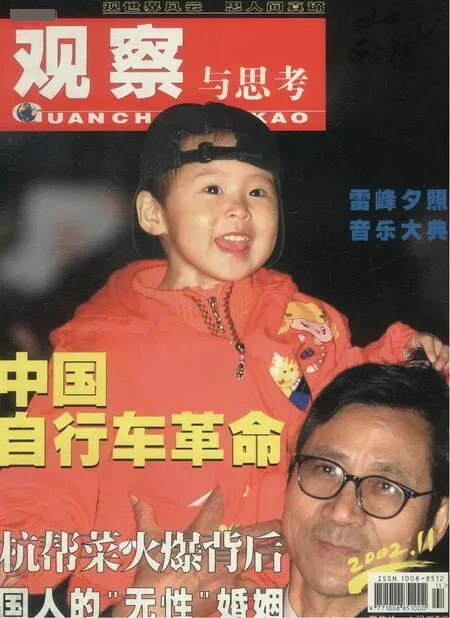清廉:边界的共构及其典型风险*
王 海 明
提 要: 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围绕权力廉洁性,由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共同建构其基本的边界。一方面,清廉是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他律性评价”,具有“他者”属性和“他律”价值。另一方面,清廉也是政治系统“自律性约束”,具有“自我”的属性和“自律”价值。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共构清廉边界,其中,存在着失真整合、过载型塑、自滤固化、过滤失衡等典型风险。
近些年,我们国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进程,呈现出一个较为突出的脉络:强调清廉建设,清廉成为政府行权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词。2017年3月,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条例》,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激浊扬清,扶正祛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作出贡献。①《习近平: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党建网,2017年3月9日。这一要求指明清廉具有政治生态内涵,赋予了清廉新的时代意义,对清廉建设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当前,清廉建设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具有怎样的边界,其边界建构机制如何,建构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典型风险,这若干问题,仍亟需学理解答。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角度对政治生态意义上清廉的边界建构及其典型风险展开探讨,既是对现实需要的一个理论回应,也是阐发、进一步学理建构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的必然。
一、清廉:从政治个体到政治生态
清廉:清,不浊也;廉,廉洁也。它多指居官者清正廉洁有节操,不贪腐、行权正派。②国学大师网上以清廉作为关键词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检索,共有2986个检索结果,清廉一词主要用于形容居官者有节操,不贪腐、行权正派。传统社会,“清廉”一词在很多情况下,用于对居官行权的政治个体进行道德评价。在这一意义上,清廉作为道德评价,体现了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对行权正派居官人士的道德褒奖。这种褒奖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良好政治风气的涵养,社会通过道德评价向政治系统传导了社会系统所倚重的一个重要价值——居官行权的清廉品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治系统对居官者正派行权的整体要求,政治系统希望通过清廉个体的榜样引领作用型塑权力整体的社会形象。通过道德褒奖,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共同建构传统社会权力清廉的榜样,虽然边界模糊,缺乏精度,但还是树立了权力廉洁性的基本方向。
近几年,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清廉”建设,强调要从政治生态的高度推进清廉建设。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①《习近平: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 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新华网,2015年1月13日。。2016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这种风气不纠正、不扭转,对干部队伍杀伤力很大。“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②《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1月12日。2017年3月,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③《人民网评:“一把手”是政治生态“关键的关键”》,人民网,2017年3月9日。党和国家关于清廉的系列论述和论断,推动清廉从道德、个体意义向政治、生态意义发生根本性转化。清廉所涉及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居官行权的政治个体,逐渐扩展为政治生态整体;其次,清廉的特征上,不再局限于仅仅作为道德层面的评价,而具有了更多的刚性内涵,具有强烈的内在约束的规范意义。其三,在机制上,当代社会,清廉已经作为政治生态的核心价值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7页。被置于整个国家、文明的大系统中,其制度建构、运行机制获得强劲的关注和持续的推进。在此期间,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设了监察委员会;相继制订、完善了一系列相关的党纪法规。新时代,清廉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系统主导的个体化的道德褒奖演化为政治系统自律主导、社会系统他律共构的整体性价值。
清正廉洁,从传统社会对居官行权的个体道德褒奖到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核心价值的转变,既是我国当代政治系统对社会变迁的一种理性回应,也是我国当代政治系统自我型塑、自我建构的必然选择。
二、作为“他律”的边界建构及典型风险
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无论是对社会变迁的回应性选择,还是政治系统自我建构的选择,都需要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廓清、建构其基本的边界。在社会系统内,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权力廉洁的感知和评价整体呈现出社会系统所建构的清廉边界,具有“他者”属性和“他律”价值。
清廉具有“他者”性。清廉的边界与其内涵关联,从社会系统来看,清廉是指社会系统对权力廉洁的社会化感知和评价,“清廉”连通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清廉具有“他者”性。社会系统作为权力系统的“他者”,清廉体现的是社会系统对权力的具体感知和评价。这种具体感知和评价,既包括直接来自权力相对方的感受,也包括间接来自权力相对方的经验、知识。“他者”在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中,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具体包括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体,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对权力有着个性化的感受和印象,尤其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联的权力行使印象深刻——包括行权者的态度、行权方式、行权程序和行权结果。清廉内涵具有“他者”属性,因而,其社会系统意义上的边界具有主观性、丰富性、关联性特征。其次,政治系统是一个多层级、多部门的复杂系统,存在着多层级的权力层次,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清廉感知中存在着差序格局①倪星、李珠:《政府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及其解释——基于2015年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因而,清廉的社会系统意义上的边界,将呈现出多层次、差异化的特征。再次,清廉的“他者”性,具有可塑性特征。社会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数字化、网络化、自媒体时代,社会个案中的清廉感受一旦获得社会网络关注后,在传播过程中,大众将原本新奇、少见的事情视为社会中平常的事情,从而改变了公众对社会的了解与认知,甚至会进一步改变公众在生活中的行动与行为。②韦贺舒:《浅析媒体“放大效应”》,《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期。有研究表明,制度、文化和信息控制对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具有影响。③倪星、李珠:《政府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及其解释——基于2015年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这表明,在建构论的视野中,通过制度供给、文化输入和信息控制,社会系统意义上的边界具有可型塑的特征。此外,清廉社会系统意义上的边界具有整体特征。清廉作为社会系统正向评价,体现了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整体性认同,间接反映出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的和谐程度。在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紧张关系中,政治系统很难获得社会系统给出“清廉”的整体评价。
清廉具有“他律”价值。从政治系统视角来看,社会系统建构“清廉”的社会边界,不仅具有“他者”属性,而且具有“他律”价值。“他律”指征社会系统所建构的清廉边界对政治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在具体的作用路径上,通过社会的清廉感知和评价影响政治系统的清廉建设。从“他律”的传统来看,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珍惜名节、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传统,历来都讲“为政以德”④《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1月12日。。社会系统正向的清廉感知和评价作为政治系统的内在追求,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助于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道德。从“他律”的机制来看,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互动性。政治系统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属于公权力,其配置、运行、行使内在的基因决定社会系统清廉感知和评价具有正当性。一旦清廉的“他律”机制日渐式微,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将日渐疏离,权力的腐败风险将潜生暗长。从“他律”的效果来看:政治系统越重视社会系统所建构的清廉边界,越重视社会系统的清廉感知和评价,社会系统清廉感知和评价的“他律”价值就越强,权力运行就越清廉。社会系统的清廉感知和评价正当性越被忽视、被否定,政治系统权力的清廉程度越低,权力面对的风险就越大。
社会系统意义上的清廉,具有社会系统建构的社会边界,其对政治系统权力廉洁的“他律性评价”,具有主观性、丰富性、关联性,呈现出多层次、差异化、可塑性等复合特征。作为一种他律性的社会感知和评价,在清廉的社会边界建构过程中,存在整合与型塑机制。这种机制,既是社会系统内在的规律使然,也是其发挥“他律”作用的必然要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清廉感知和评价的整合与型塑存在着失真整合和过载型塑等风险。
有关失真整合的风险。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清廉感知和评价,无论是作为“他者”的属性还是具有的“他律”价值,其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部分是作为系统的真实而存在,为政治系统权力廉洁性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社会指标。但社会系统整合过程中,可能存在压制型整合,出现“不良社会”。社会力量是以断裂和失衡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出现对立和巨大的裂痕。一方面, 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构成一个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是两者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高度失衡。①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弱势群体的清廉感知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其清廉评价没有话语空间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少数的强势精英则占据、主宰社会系统清廉感知和评价的表达、话语空间,出现整合失真风险。严重的整合失真,使得清廉彻底失去作为“他者”的意义,失去作为“他律”为政治系统权力廉洁性提供社会指标的价值。
有关过载型塑的风险。失真整合风险属于社会系统内部整合风险,而过载型塑风险主要是指外部系统对清廉的社会边界进行社会型塑过程中输入过量的力量和信息,导致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权力廉洁无法形成真实的社会感知和评价,进而无法为政治系统提供有效的“他律”(如社会监督)。以系统理论来考察,有动力和资源基础向社会系统输入力量和信息的主体,主要来自政治系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处在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政治体系中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存在极其强烈的型塑动力。政治力量在型塑权力清廉过程中,从社会系统外部输入型塑力量和型塑信息,对社会系统进行型塑。从逻辑上讲,这一类的型塑存在全覆盖型塑、广覆盖型塑和小覆盖型塑。型塑的覆盖面和深度体现型塑主体与社会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能动与被动的关系,影响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距离。政治系统对社会渗透力和组织力越强,其对社会系统的影响力、控制力也就越强。过载型塑意味着政治体系对社会体系的控制形成了超载压制,对社会系统力量和信息的输入失去了必要的平衡和距离,带来关系失衡、发展失控等恶果。
三、作为“自律”的边界建构及典型风险
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不仅是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权力廉洁的“他律性评价”,具有社会边界;也具有政治系统自我建构的边界,将对权力产生“自律性约束”。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政治系统将建构自我约束的边界,具有“自我”属性和“自律”价值。
清廉具有“自我”属性。从政治系统视角来看,清廉政治意义上的边界来自于政治系统的自我建构。现代社会,政治系统的权力发生过深刻的变革。社会变迁必然引发政治领域的转型调整,新的政治观念、政治规则将逐渐成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政治体系中核心概念“权力”逐渐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政府权力逐渐由主权性转化为公共性,政府权力出现了现代转型:权力的真正功能是创设秩序和稳定,满足公共需求,这是权力强制力产生的根源。①[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0页。随着权力的现代转型的完成,权力廉洁性受到了政治系统内外的关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说过:“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②转引自付启章、蒯正明:《政党形象型塑鉴迪与我党五项要务》,《新疆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自我”意味着权力廉洁成为政治系统整体性的共识。虽然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政治系统有着不同的框架和结构,有着不同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但清廉一旦成为政治系统自我建构的基础元素,就意味着清廉作为政治系统内在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获得了整体性特征。虽然政治系统是一个多层级、多部门的复杂系统,存在着多层级的权力层次,但清廉作为政治系统自我建构,它可以作为政治体系的共同的理想、精神、品质而超越其内在的权力层次,抹平层级、部门之间的不同,作为一个统一适用的整体而出现。政党作为现代化产物,一端连着民众,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③参见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政治系统中的执政党,作为政治系统的领导力量和主导力量,对权力廉洁的“自我建构”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导清廉的规则建构、机制建构、制度建构,主导确立清廉裁判标准、裁判程序和裁判后果。清廉的“自我”性,不仅体现政治系统的整体性、主导性,而且体现了政治系统的自省性。执政党从规则、机制、制度、标准、程序和后果等方面对清廉的政治边界进行型塑,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系统内部统合的整体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他律”价值的一个回应。社会系统纷繁芜杂的清廉感受和评价在经历社会系统内部的整合作用和外部简化之后,以“他律”的方式作用于政治系统,最终,政治系统将以“自省”的方式和形式将“他律”影响纳入到清廉的“自我建构”。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系统对清廉边界的“自我建构”,也是一个自省的过程,体现了政治系统的自省性。
清廉具有“自律”价值。政治系统对清廉边界的“自我建构”完全有别于清廉社会边界的社会建构。在政治系统中,清廉具有整体性、主导性、自省性,它有着具体的载体和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自律”性。政治个体意义的清廉,其道德褒奖色彩浓郁;而政治生态意义的清廉,不仅具有社会系统的“他律”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律”价值。政治系统的清廉,不仅是执政党主导的政治理想、政治情怀、政治品质的自我建构,同时,也是政治纪律的自我建构,约束、统摄整个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鉴于权力的宽泛性、涉他性,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中,政治系统权力腐败、权力自肥、消极用权防不胜防,权力异化现象全覆盖监管存在不少困难,而且监管成本高企,清廉作为政治系统权力廉洁性的自我约束,逻辑上需要一个普适性的、广泛的、深入的强制性,政治系统任何一个层级都不存在例外与特权。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需要一个能够胜任这一政治诉求的形式——如具体体现为党纪党规的自律准则、或者体现为执政党的党章、或者体现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④田米香:《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首要任务》,《宁夏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新时代,加强党的廉洁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廉洁纪律是清廉“自律”性的集中体现,廉洁纪律既可以体现为执政党的廉洁纪律,也可以体现为对整个政治系统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如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就集中强调了廉洁自律,明确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内容;2017年7月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了中共中央巡视监督的重点内容就包括廉洁纪律,廉洁作为执政党的纪律,是中央、地方各级党组成员不得触碰的红线;此外,清廉作为执政党的纪律要求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党章第三十六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六项基本条件,“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是其中的一项基本条件。清廉作为整个政治系统的纪律,其形式可体现为国家具体的法律规则。如201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系统成文的法律规则,强调公权力的清廉约束,为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系统的法律依据和保障。无论是党纪党规党章,还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中的清廉要求或者清廉约束,主要来自政治系统内在的自我约束、来自执政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革新,集中体现了清廉的“自律”性。
清廉“自我建构”,本质是清廉边界的自我建构、自我维系,这一过程中,存在政治系统的自我过滤,这种自我过滤,一方面保证了政治系统的整体性、主导性,同时,也存在自滤固化风险。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一个保守的偏见得以建立起来。它赋予我们以信心。至于那些拒绝融入的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们发现自己故意忽视或者歪曲它们,使它们无法干扰已经建立的假设。我们注意到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感知行为中被事先选定和组织起来的。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某种过滤机制,能够在最初只让我们感知到我们知道如何运用的东西。”①[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9页。政治系统内部存在的自我过滤,导致清廉的“自我建构”存在固步自封的固化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效化解和克服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②《专家解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概念:政治领导力》,人民网,2017年10月30日。为什么执政考验会成为新时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呢?根源在于执政党长期执政,逐渐沉积自我过滤机制,形成固化效应。破解自滤固化风险,需要政治系统强化自省自律,尤其是执政党的自省自律。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具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强调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从严从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③《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1月12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的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变,执政党通过强化自省自律,成功克服了自滤固化风险。
过滤失衡风险。从系统论来看,政治系统型塑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有反作用力。社会系统“他律”作用是否正常发挥,取决于社会系统是否被政治系统恰当过滤。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流动、变迁以及关于权力廉洁的社会需求、诉求等恰当过滤的,社会系统可以较好地发挥“他律”作用,政治系统能有效、及时识别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不和谐风险,并积极地推动有关权力廉洁性方面的各类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流动、变迁以及关于权力廉洁的社会需求、诉求等严重过滤的,社会系统的“他律”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关系容易出现失序,这种风险就不容易被政治系统识别、承认、正视和认真对待,长期以往,政治系统对权力廉洁性的认识将出现认知失真,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的回应出现僵化风险、迟滞风险。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流动、变迁以及关于权力廉洁的社会需求、诉求等过滤不足时,政治系统将面对一个嘈杂的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内部难以整合出具有整体性、主导性和自省性的清廉,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对权力廉洁性的认识,可能出现错位和割裂,无法型塑良性、平衡的秩序关系,出现混乱风险。
总之,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由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共构其基本的边界,其中,既有由政治系统建构的起自律主导作用的边界,又有由社会系统共构的起他律作用的边界。政治生态意义上的清廉,体现了政治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复合关系,呈现出整合与被整合、型塑与被型塑、过滤与被过滤等微妙的平衡,其中,存在着失真整合、过载型塑、自滤固化、过滤失衡等典型风险。这些风险,是建构权力廉洁、推进清廉建设必须正视、着力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