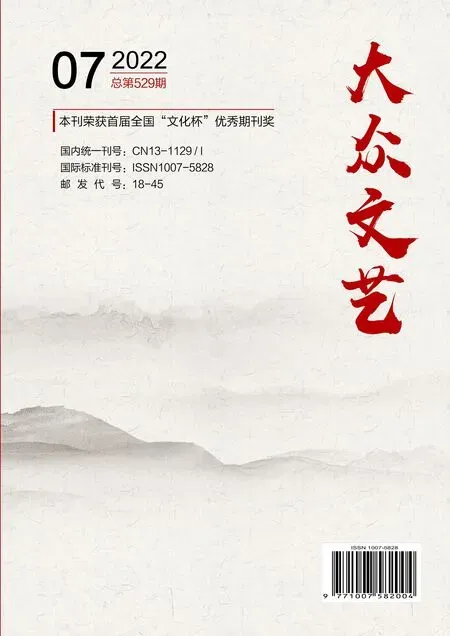从《游民三部曲》看徐童作品的影像意义
赵 铮 (山东艺术学院 250300)
作为近年备受关注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将摄影机对准游民群体,关注被主流社会屏蔽的底层边缘人物,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诉求。他在拍摄时彻底融入被拍摄者的生活,以独特的视角、与摄制对象的顺应共谋关系1,探讨着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徐童的作品“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在国际上屡受嘉奖,同时却也因对被拍摄者职业、信息等的披露,引发了业界对纪录片本体和纪录片原罪的争论。
一、独立创作与底层叙事
纪录片在我国可大致分为两种形态,如《故宫》、《话说长江》的体制内主流作品,又如《流浪北京》、《八廓南街16号》的非体制内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以《流浪北京》(吴文光)为标志,一些非体制内的纪录片创作者追求自由、理想、个性化的创作方式,用摄影机代替眼睛,从精英视角转向大众视角,开始关注人的本身。由此产生的大量非体制内纪录片,也被称独立纪录片。
和许多独立纪录片导演一样,徐童记录的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和生命个体的体验。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苦难都是相似的,但与复杂的社会相比,人的复杂是更有魅力的选题。在完成自己的小说《珍宝岛》后,徐童认为小说、摄影并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于是他坚持带着摄像机,远离城区,走街串巷,通过自己的独立拍摄和剪辑,为大家展示最有代表的生命。算命的厉百程,性工作者妞妞、唐小雁等,这是一些从事着“应该被取缔”职业的人,但他们仗义、讲究缘分,是江湖中人。徐童带着自己强烈的责任感和压迫感,带着对中国现状的焦虑,融入社会底层,拍摄这些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
《老唐头》中的老唐头,尽管已经被退党,还是珍藏着党章,他心中一直有着回到体制内的情结,尽管现实总是让他感到失望,徐童将漫长的历史融入老唐头个体的生命历程,使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漫长的时间,从而达到了对生命的探讨和反思。《算命》中的厉百程身体残疾,却同样照顾着身体残疾的石珍珠,算命场所被查后不得不回到老家,却依然盘算着开春另起炉灶,这种在社会边缘挣扎,但仍旧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值得敬佩。在补充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徐童也通过影像的力量向我们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精神力量,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作品其中。在徐童的作品中,观者经常能真实地感受到激烈变化的社会带给每个人的冲击,而在时代裹挟下,边缘群体的迷惘和失落,坚信和希望,也同样带给观者对生命的反思。
二、人文关怀与游民诉求
伴随着千禧年而来的是一个变革的年代,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而来的是城乡边际的重新划分,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游民群体。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对这个群体做了界定:所谓游民,自古有之,游民的产生和宗法社会有关,一些“宗法人”因战乱和人口激增而失去劳动对象——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游走江湖,成为脱离了宗法网络秩序的人,也就是游民。2徐童的关注点一直在游民身上,他的拍摄对象大多背井离乡,游离余主流社会之外,从事一些不正当职业,也因此他的三部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被合称“游民三部曲”。
为了在夹缝中生存,游民们不得不主动出击,以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寻得一席之地,徐童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是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意识。在《算命》和《老唐头》中,徐童都记录了唐小雁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性。她没有文化,没什么本事,只能选择做一名性工作者,她开洗头房、黑煤矿,废了举报自己的人,这样一个浑身沾满风尘与戾气的女人却努力对自己的生命、家庭负责。《麦收》里的妞妞虽然从事性工作,但依然对嫖客强有着少女怀春的心思;她为父亲筹集医药费,是家人眼里让人骄傲的女儿。在影片《算命》中,厉百程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体残疾而自暴自弃,反而承担起了比自己更弱势的石珍珠的生活,还会称赞石珍珠身上的善良品性。他们虽然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反而挑起了生活的责任。
这就是徐童作品中的主角,他们或许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底色,但能够掌握自己生活的态度。他们行为粗俗、职业难登大雅之堂,他们处在边缘,但坚韧而努力,从来不曾停止从边缘向主流的努力。徐童在作品中努力呈现粗粝的游民世界,生存和归属是游民的诉求,如何生存和归属则是徐童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文关怀。
三、伦理考量与契约关系
徐童的作品备受争议是从《麦收》开始的。《麦收》拍摄了燕郊的性工作者妞妞,视频公映后,因为将片中人的职业、家庭和人际关系毫无掩饰的暴露在公众之下,从而引发了业界关于拍摄者、被拍摄者与观众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针对此片,妞妞对徐童提出删除并禁止大陆播放的要求;片中出现的另一位性工作者阁阁也在网上坚决反对此片的播放;该片在云南、香港、上海等地参展时,均发生了抵制和抗议行动。应被拍摄者要求,徐童呼吁大家不观看、不讨论、不传播该片。
如何解决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伦理问题?西方纪录片界,有时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会在拍摄前签订契约,标明什么是能在影片中出现的,什么事不能出现的。但此种方式在中国实行似乎有些难度,因为中国人更倾向于口头的契约。对此,徐童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走进被拍摄者的生活,以先生活后拍摄的方式,与被拍摄者成为一种平等的合作、朋友关系;拍摄者也将自己的生活展示给被拍摄者,二者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彼此承担着对方的情意和责任。徐童带唐小雁参加影展,将自己的生活展示给唐小雁,让唐小雁理解自己在做什么,纪录片是什么,由此和唐小雁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契约关系。唐小雁随徐童到高校、影展参加活动,到电视台进行专访,不仅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独立电影年度电影展组委会首次颁发的“年度真实人物”奖,还获得了观众的认同和喜爱,这是让徐童和唐小雁始料未及的。最后,引用王小鲁的一句话“我们愿意相信:大多数作品与原型的冲突都将增加对纪录片文化的理解,而不是增加法律的诉讼。”3
徐童将摄影机对准游民,游民的生活无奈又艰辛,但他们用蓬勃的生命去抵抗被边缘化,这种游民精神确实让观者引发了新的思考。徐童所拍摄的游民群体鲜活、真实、可信,他对于游民文化的推广,纪录片宣传方式的创新,纪录片原罪问题的解决等所做出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王冬冬,刘跃.《纪录片拍摄中记录者与被拍摄对象共谋关系分析》.现代传播,2012,05:93-96.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3.王小鲁,《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电影艺术,340期:9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