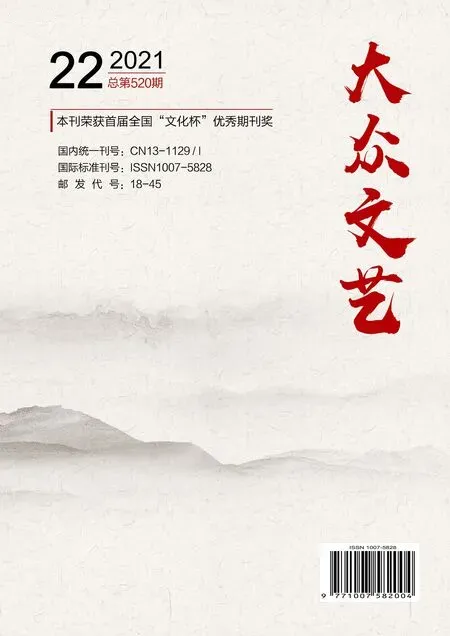解读现代摄影的人文关怀
张 宁 颜莹露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10037)
摄影从一开始简单的留像,到后来演化出诸多风格类型,直至独立地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达形式。一直以来,摄影作品都映射着摄影师从镜头后观察到的世间百态。在创作过程中,当摄影师将镜头聚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代入自己的心态感受,在影像之中思考画面背后的问题,此时,摄影作品本身就被赋予了除了纪实、审美之外更多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人文关怀的注入成就了摄影,升华了摄影。
一、概念的界定
1.现代摄影的定义
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法,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及时捕捉并长期保存外界影像的能力,这个时候的摄影就像是初生的婴儿第一次见到世界,什么都想留在脑海里。摄影正发展成为世界上一种独立的艺术与传递信息的媒介,但要是说摄影从此真正成为艺术,也并非如此简单。早期摄影术停留在把眼睛看到的景象现实的拍出来,当时因为技术还不够,成像的质量也与摄影师们预想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经过塔尔博特、巴耶尔等人的不懈努力,摄影的成本和质量都得到了相当的改善,时间变短,成本变得相对低廉,作品也更加清晰明朗,这使摄影大众化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摄影渐渐从少部分人手中跳出来,变为更多人可以运用的纪实手段。1840年,由于政府只承认达盖尔先生对摄影的贡献,而对巴耶尔冷眼相待,使巴耶尔将自己愤懑不满的情绪倾注在相片中,《扮成溺水者自杀的巴耶尔》应运而生,拍摄者也是被拍摄者,镜头下是自己对自己的悲悯和不平,从此摄影开始有了情绪表达,人文关怀首次出现在了摄影作品中。
2.人文关怀在现代摄影中的含义
把人文关怀注入自己的作品,其实作品本身也就被赋予了摄影师本人的价值取向,我们不只是用相机拍照,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爱过的人,彼时,摄影更像是在摄影师的心上装了个话筒,镜头是摄影师饱含热泪的眼眸。麦基在《可怕的错觉》“你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只看一个人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你只会得到偏颇的结论。这使得很多关系以悲剧收尾。现代摄影师吴家林被誉为“走上国际影坛的摄影大师”,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是对被拍摄者的尊重,镜头前的人和镜头后的人人平等且独立。吴家林老师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他把目光投在生活在山林乡村中百姓的生活中,若说是在表现村民的淳朴民风,似乎太过刻意,似乎他只是局外人,而事实上,吴家林老师是将自己真正当作一个村民在其中生活,他是摄影师,却也是个记录者、体验者、热爱者,他的作品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村民的淳朴自然的美好,还有的是他的醇厚浓郁的热爱和闲适恬静的乡情,经过了长期的对被拍摄者的观察和了解,才使得被拍摄的人保留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和自由,得到的作品才不是失“真”的本质。摄影的创作是似是而非,不是直白的纪实,是超现实的创作,是精神层面的创作,但是要真正将人文关怀产生在摄影中,就需要摄影师和他镜头中影像的一场恋爱,需要慢慢了解,平等对待对方,绝不是任何一方的思想强加给对方。
二、人文关怀在现代摄影中的体现
1.人文关怀体现的错位
悖论的地方是,带着着要注入人文关怀去拍摄,本身就不可避免的代入了拍摄者本人的思想倾向。想要做到对被拍摄者产生真正的人文关怀,就应当减淡自身的表达欲,减少目的性。一个反例就是1936年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流浪的母亲》,兰格拍摄过后表示她当时被这位街头流浪的母亲深深吸引,然而她在拍摄完成后转身离开,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兰格一反此前对这位母亲作出的只研究不发表的承诺,广为传播后使其成为代表作品,可是对这位经受着美国经济大萧条摧残的、被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包围的母亲,摄影师没有给予她任何关怀。可以看到的是,摄影者只把被拍摄者当作一一个足以代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符号,是她经营画面而谋求名利的作品。最后她的作品也只会是一个困难时代的缩影的符号,背后只有让人心寒的贫瘠含义,虽然引起了政府对人民的关注,而被拍摄者的生活无人关心,因为拍摄者本来关注的重点仅是在事件本身,而不是人。
2.人文关怀在现代摄影中的真正体现
世界著名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出自摄影师凯文·卡特,由于过度饥饿而瘦到皮包骨头、几乎脱了人相的女孩被饥肠辘辘的秃鹫当作猎物,在一旁静静等待女孩的死亡,这一幕被凯文·卡特定格,拍摄结束后他将秃鹫赶走,注视着女孩蹒跚离开,呆坐在树下放生痛哭--这个女孩让他想到了他的女儿。他记录下这个画面并发表,因而引起了世界对苏丹饥荒和内乱的关注。但问题是,其实女孩的身旁不远就是领取救济粮的母亲,她并非孤立无援,而凯文·卡特却由于并未显示这一点而备受媒体抨击,由于媒体的错误引导,使得公众舆论猛烈攻击摄影师本人,而此后由于经济窘迫和好友离世的自责让凯文·卡特在车中自杀,似乎使公众更加曲解其中含义,更相信他有愧于《饥饿的苏丹》中的女孩。事实上,凯文·卡特已经运用摄影的功效表达了对女孩的人文关怀,不带渲染和曲解地表现出了女孩的绝望处境,而摄影者本身也并非站在制高点上,并非以一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的姿态去截取画面,而是激起了摄影者作为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运用摄影为女孩和女孩的国家谋求一条生路。万幸的就是,这部作品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作者得到了九四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也由于他的作品,世界各地的政府将目光聚焦在苏丹内战和饥荒上,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同样的,在2012年,克雷格·F·沃克以《欢迎回家,斯考特》一组摄影作品也赢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奖项,他的作品聚焦于退役老兵斯考特身上,聚焦于一个患有战后创伤后遗症的老兵。前后共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和斯考特一起生活,以此深入了解并跟踪拍摄,最后得到这一幅作品。能够设想到的是,跟踪拍摄一个罹患战后创伤后遗症的老兵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任何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脆弱不堪的一面暴露在镜头面前。摄影师需要不断和被摄影者交涉沟通,以朋友、家人的身份论处,不使用任何更适合传播、精心营造的画面,而选用极为客观的角度和平直的手法,着重客观,表达出被拍摄者现实的内心世界。由图片可以看出斯考特由于后遗症而带来的家庭关系问题、内心的空虚、战争噩梦的侵袭、身体的痛楚,更多的还是备受折磨的斯考特带着未来生活的憧憬而作出的努力。这样的摄影作品本身就像是被拍摄者的一个传声筒,而非被摄者的虚构塑造。
三、结语
摄影师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切入画面的视角,在对不同的时间空间进行截取切片时的心态也都会反映在画面当中。可以说,摄影也就是高度提炼的影像通过视觉传达进人们心里,从而引起联想和共鸣,是现实的真相,如何判读终在个人。偏颇难以避免,但不论偏颇如何,而现代摄影中去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恰恰就是需要摄影师实现平等意义上的关怀。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摄影师,与镜头前的人平等共生,互相尊重,尽量减少非理性因素对画面的影响,如此,摄影师作品的表达就可以被看作是被摄影者心相的表达。才是让摄影为艺术服务,为人性保护,去赋予人成为人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