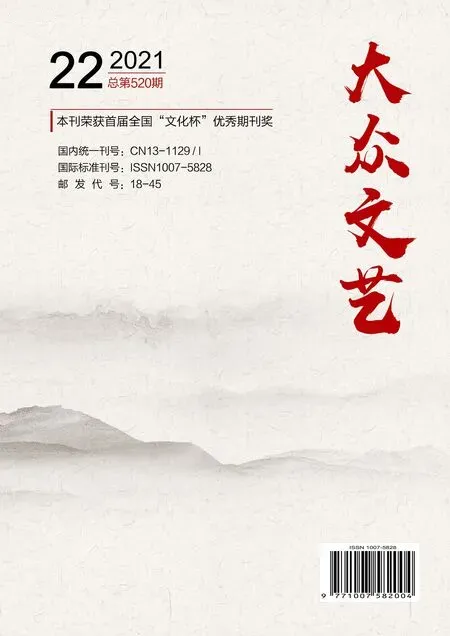论红色叙事与展陈艺术的互文性
程慧福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716000)
法国著名思想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她所著的《符号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并认为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及其所指的语义、符号和表意之间的关系集合,它们构成一种相互参照、无限延伸的网络结构。罗兰·巴特则将“跨学科的”和“多主体性”概念引入从而拓展了文本界定,并认为互文是文本及其主体(作家、读者)之间信息流动的空间本质,即不同形式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红色叙事与展陈艺术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当代的历史博物展览之中,尤其以红色文化、事件及人物纪念的展示设计更充分展现二者的互文性关系。红色叙事是基于事实之上再现了鲜活的历史场景和有温度的生命细节,它是带有鲜明“红色”符号与精神内质的历史叙事。红色叙事注重历史文本的讲述方式,通过文字让读者感受其情节变化、时间推动,从而形成连续的叙事体验。而展陈艺术则以展示表现为主,通过交互媒介的信息输入和受众的多维度参与完成,是一种空间化的叙事形式。因此,本文将从空间、时间、认知三个方向探讨红色叙事与展陈艺术之间的互文关系,以期对叙事展览的内容建构和“红色”主题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红色叙事与空间媒介的多维度观照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的大背景下确立的一门学科,它从一开始就展示出对其文本结构和叙事媒介的热情,连罗兰·巴特也认为,除了文学作品外,很多材料都可以作为叙事对象,如绘画、电影、音乐、雕塑甚至建筑。而所有包含叙事性的媒介都具有时空的二重性,即使早期的学者认为由文字写成的诗是连续性的,是时间性的艺术,也无法像绘画那样同时呈现若干个物象;而红色叙事作为一种叙事媒介已成范式,这不仅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和文本结构的独特性,更是关于时间的审美修辞。文学叙事必须遵循某种特定时间逻辑,文字这一线性媒介自然削弱了其空间形态,而作品只有赋予情节以时空,才能让读者漫游其中,结合主体叙事与个体经验进行合理的推论。
面对视觉化、直觉性的空间故事讲述方式,文学叙写的空间体是对时间性媒介的“出位之思”,它更像是模糊化了的虚构空间,其尺度和形态因人而异且难以界定。而叙事展览则是道具、场景按一定的剧本编织的实体空间,这与文学小说、电影以及戏剧等营造的叙事空间大有不同。
无论是给人以想象的文字化叙事空间,还是直观的荧幕影像叙事,都是通过牺牲观者一定的“自由”,在预定的情节编排中获取的精神愉悦,这与置身于空间之中的叙事体验有着本质区别。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正是一个见证文字与空间美妙邂逅的案例。这是一座与小说同步落成几近相同的空间,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呈现,对小说的空间想象与真实的物象一一对照,那泛黄的老照片,停摆的钟表,新古典的装饰纹样,无不让人熟悉而感怀。读者对博物馆的形象认知由此逐渐清晰,是一种记忆联想向知觉感受不断推进的完型过程。
“红色”主题的叙事性设计以真实的空间形态演绎过去的革命历史与家国记忆,而观者的认知客观角度将不再置身媒介之外,而是主动的介入叙事内部,通过动眼观察与自身移动来完成叙事的话语时间。若将空间叙事的话语时间与红色记忆的故事时间加以复合参照,便能更好地实现文本内容的空间转译。
二、展陈空间的叙事逻辑及时间设置
(一)红色叙事的“时间”形式
红色叙事是文学语境下的“红色”语词或者“革命”叙事,它不但涉及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经验和民族抗争的遗产问题,也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观照,尤其是在维护政治生态、重塑精神文明方面意义重大。红色叙事曾是近代中国文坛史上的主流叙事媒介之一,而至今日也仅留下了代表空洞的正统表义,简化平面的单一范式叙事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还原历史的本真。红色文学以情节讲述故事,塑造丰碑人物的个性,是一种反映特定时空记忆的历史“叙事”,而这种历史的叙述不同于用“事实”说话的历史逻辑,它必然加入作者的情感元素而更艺术化,让故事更有魅力。
红色叙事将史实、人物及事件等话语元素编排于时间轴上营造无限追忆空间,承载往事与集体记忆。在意识形态和叙事结构的趋同性作用下,红色叙事亦呈现出“时间”形式的独特性,依据《新中国文学史》分类其时间形式包括“类史诗叙事”,“类传奇叙事”,“类成长叙事”,“类抒情叙事”四类,而本文通过介绍前三类“时间”形式规律并探讨与之对应的空间叙事展览的特征。
“类史诗叙事”的作品以宏大场景还原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从国家集体的叙事角度把握历史脉络,再现民族记忆,作品风格具有壮阔美、正义美、雄壮美的美学特质。纵观此类文学作品,以“断裂”的时间形式截取某一历史片段,让读者在既定的故事线和时间轴中达到记忆的回溯和信息的传达。国内许多大型纪念馆正是依据“时间”断裂来安排空间秩序,如延安革命纪念馆,多个空间的连续转场记录不同阶段的党与国家、人民奋斗抗争的宏大史诗。
“类传奇叙事”类似于我国古典章回小说,通过夸张的人物描写与戏剧化情节来表现鲜活的主人翁形象及其传奇经历,而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打破恒常的时间线而介入奇遇、挑战、冒险、危机、化解等连续的叙事环节。尽管这种“超时空”为历史学家所摒弃,但它“历险记式”时间模式更适合趣味性叙事的开展。在正统化的革命叙事模式下适度的空间演绎和情态更迭是青年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通过一场探奇历险的互动体验更能加深对往昔战斗的残酷、生活的艰苦的体会。
“类成长叙事”将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相统一,深入刻画人物性格、思想变化以至身份的蜕变,以个人的身体实践折射出了大时代的历史变迁。这类叙事方式呈现出故事的清晰时间脉络,且主体认识在此波折中渐进上升。“丹尼尔的故事”展览是美国大屠杀博物馆的一个面向儿童的线性展陈空间,通过讲述小男孩丹尼尔在1933年到1945年间生活,从个人的视角展现出了犹太人遭受的残酷迫害。出于适龄化的考虑,对暴力的场景做了艺术处理和适度留白,反而给人以深刻印象与遐想空间。
(二)空间叙事的“时间”策略
叙事展览的空间因主题而“量身定做”,通常采用文学中的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的方式完成整个的展示线路,因叙事空间是直观的物理空间,其展陈艺术涵盖实物、图片、文字甚至场景等。故此,除了明确的观览流线外,更要靠内容连续、色彩指向、灯光照明等要素综合构成,而这一过程既是对时间轴的塑造,同时也是将时间轴空间形态化的过程。我们在上文已探讨了红色叙事的时间形式,那么与之对应的红色主题叙事展陈在空间编排的情节设置上便有一定互文关系,提出符合其时间逻辑的空间叙事策略。
叙事展览强调“共时性”的逻辑时间,通过空间的形态与组织、边界的模糊化处理强化观者的在场型体验,同时行动的并存或交替产生不同深度的感知。连续均质的空间阵列可以实现“类史诗叙事”的宏大场景的壮美与气概,如《又见平遥》中千里救人好汉离别之景,锣鼓响,杯盏碎,山呼海啸般的震撼场面令人动容。空间插叙与旁白手法穿插进观者的自主行为实践中,如上海曾举办的“红色一公里行”,通过游客的绿色出行,在其沿线布置醒目的历史记忆符号,文化的信息传播不仅易于接受,同时也增添了其趣味性。
三、叙事性展示设计的空间认知特点
观众在叙事性展示空间中享有高度的“自由”,往往一个空间叙事是在观者站立与行走交替中完成的,也就是说,无论策展人或设计师提前设置怎样的环节,在此过程中观众会根据个人喜好而选择性的接收信息。尽管参观者的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经验不同,但就共同的国家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构成,仍然可以通过象征性符号、语言和器物唤起大家的思想共鸣和文化认同。
空间叙事由连续变化的时空建构直觉性的真实的物理场所,在这个“场”中以复合的空间媒介形态为观者提供立体的视听环境,既有古物、遗存等本体的叙事,也需要其他的辅助视觉系统(场景、模型、雕塑)来完善这一历史性的跨时空对话。
较之红色叙事的情节“创作”,叙事展览中对时间的删减较多,这种展览的省略既有对空间秩序合理化编排的实际需要,也有其展示序列断离、历史证据不足以及历史争议尚存等原因。因此,展示叙事性设计需要设计师在尊重宏观的叙事史实的基础上,把握观者在动态中的感知与体验图式,通过空间情节的方法处理,将物、景、人融合于历史的碎片空间之中进而完善个人不同的叙事性解读。
四、结语
红色主题的叙事空间内涵广泛,除了以纪念为目的的新建设施,那些事件发生的原初地更令人着迷。尽管往昔的情景离我们远去,但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了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每一处细节事实上都在提示和加深人们对那段记忆的深度认知。通过从空间媒介、时间设置和观众认知三个角度探讨红色叙事与展陈艺术的互文性,对革命旧址原生景观的更新和纪念地展览的内涵式构建开辟了新的途径,未来发展呈现出新的方向。
叙事介入展陈设计中,赋予空间以情节化,将文学叙事的“静态”陈述转向了空间的“动态”演绎,真正让红色记忆和历史的文本鲜活起来。而叙事也不再像“故事”那样单向性的“要我看”,而是充分提升观者的自主性,通过“我要看”的兴趣实现叙事的完型。红色主题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教育观,而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共同的中国梦,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将展陈空间的艺术性与历史的革命性相融合,让年青人在其中体会到更深、更有趣的文化熏陶,同时开拓了历史叙事的传统表义方式。叙事性设计研究其内容的创新性与情节的生动性表达,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可行的空间逻辑和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