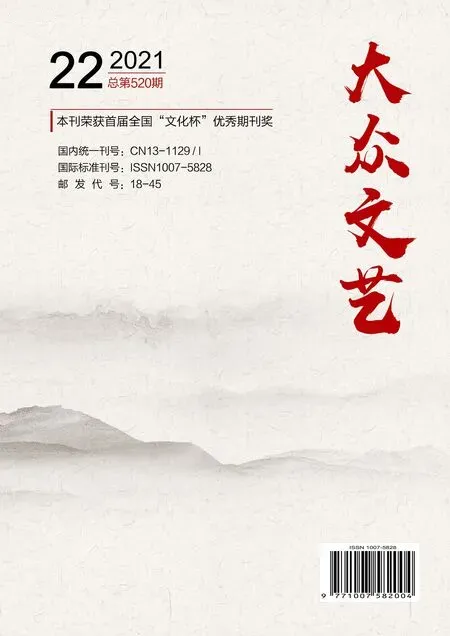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二十年后》的身体空间叙事
曹小雪 (江汉大学 430056)
一、引言
《二十年后》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两个美国青年——鲍勃和吉米·威尔斯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当鲍勃要到西部去创业时,他们相约二十年后在纽约大乔勃拉地饭馆相会。然而在西部闯荡了二十年并且正受芝加哥警方缉捕的鲍勃赶到纽约来践约时,在纽约已当了巡警的吉米以出人意料的手段逮捕了鲍勃。这篇小说短小精悍,情节安排合理,结果却出乎意料却又符合逻辑,凸显了欧·亨利一贯的写作风格。
纵观全文,作者的身体空间叙事对主题的呈现至关重要,它们甚至是理解耐人寻味的结果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二十年后》的身体空间叙事
鲍勃和吉米的差异在二十年前两人在各自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开始展现。鲍勃选择到西部去淘金、发大财;而吉米则选择在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纽约奋斗。他们各自的主体意识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所行走的空间,而空间的特色又塑造了他们各自的身份,影响了各自的命运。
1.西部空间里的“滑头鲍勃”
鲍勃的选择展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淘金热”、“镀金年代”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他的身体留下了一部分美国西部空间的烙印。
据《美国通史》记载,美国西部矿业开发时期较短,它出现于1860年左右,接着是持续30年之久的繁荣兴盛,到1890年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也随之而结束。《二十年后》一文中鲍勃去西部闯荡也就在这一时期。在西部地区,一旦发现金矿,大批的探矿者、冒险家和投机商纷纷涌入这两个地区,采掘价值巨大的金子。西部资源富庶,人少地多,因而能为开拓者提供较多改善自己处境和致富的机会。在西部,阶级界限不像东部老区那样明显、固定地划分,而是比较容易突破。因此,开拓者极有可能因为开发许多未被利用的资源而致富,而同时又很容易在一个尚未定型的社会秩序中获得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因此,小农场主靠肥沃的土地的丰产便很快地富裕起来,投机者由于出售他在城镇的一些地块而获得一笔巨额收入,运气好的矿工拿起铁锹干一阵便发现丰富的矿藏,从而发了横财。总之,一个人只要在有利时机的情况下致力于发财致富,他就有可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可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生于纽约市井的鲍勃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去西部冒险,他渴望通过快速的方式来积攒人生的第一桶金以及快速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获得身份的重塑。
其实在鲍勃做出选择之际,读者就可以隐约看出,鲍勃有着想要放手一搏的急功近利和冒险的精神。同时潜伏在他身上的纽约市井之气又赋予了他圆滑、聪明的特性。
在矿业城镇,社会治安糟糕,经常有匪帮和歹徒进行骚扰和抢劫。争吵搏斗、私刑拷打以致枪击厮杀的事件层出不穷。(丁则民 128-129)西部世界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之所。“这个地方盛产金、银、铜、铁、水银、大理石、花岗岩、白垩、石膏、盗贼、杀人犯、亡命徒、女人、儿童、律师、基督徒、印度人、中国人、西班牙人、赌徒、骗子、恶棍、诗人、传教士,以及傻瓜笨蛋、胆小懦夫。这里花草不生,看不到一丝赏心悦目的青绿颜色,连鸟儿飞越这里也要随身携带干粮。”(马克吐温,原序9)在这里,发财与挥霍,追求与冒险,野心与欲望,强力与巧智,希望、奋斗、钻营、落空、潦倒、幻灭……在万头攒动的黄金梦幻中,人人都上演着各自的悲喜剧。
鲍勃在西部具体经历过哪些悲喜剧,读者仅从欧·亨利精炼的言语描述中很难详查。但是鲍勃在和“吉米”碰头时,重塑身份后的喜悦之情在作者“不经意”的细节描写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了可供追溯并想象的文字。欧·亨利在文中描述的鲍勃精明的眼神、额头上的刀疤、手指头上硕大刺眼的钻戒、嵌满钻石的怀表,以及他给所谓的“吉米”讲述的这些年在西部的打拼经历,鲍勃身上所承载的空间特征让他的性格渐次丰满:一个本性纯良、可塑性极强的纽约青年,在黄金梦的驱使下,来到西部淘金。趋利避害的求生本能、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让他在尔虞我诈、工于算计、以暴制暴的环境中变得心狠手辣、戾气十足,精明狡诈。在江湖上,他获得了一个“滑头鲍勃”的称号,警察也奈何不了他。
他的形象颇似马克吐温在西部小说《苦行记》中所描绘的亡命徒斯莱德:“斯莱德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双手和灵魂上都沾满了冒犯过他的人的鲜血。他是个对任何伤害他、冒犯他、侮辱他或怠慢他的行为进行疯狂报复的人……他是大陆上的一个高贵而精明的公务员,一个土匪中的土匪,又是土匪的克星,他是山区蛮荒地带最嗜血、最危险、最有价值的公民。”(马克吐温 47)鲍勃唯有像斯莱德一样,才能在西部粗砺的环境中生存、打拼并快速的发财致富。
这就是西部空间暴掠血腥的一面在鲍勃身上的体现。然而鲍勃的记忆空间中仍然保留有和吉米的约定。因此,当20年之约来临之际,他记忆中的吉米的形象仍然可爱,“最善良、最可爱”等词汇与其说是鲍勃用来形容吉米的,不如说是用来传达他心中封存已久的那片人性的善良与温暖。因此,鲍勃这个人物内心复杂,善恶交杂。在他身上,既有西部空间的特征,也有市井阶层的特性,有性格狡猾多变、暴力的一面,也有面对友情时温柔善良的一面,因此,鲍勃的人物个性空间呈现出复杂纠缠的多面性。
2.纽约空间里的“无脸男”
和鲍勃相比,吉米的形象相对单纯。吉米从一开始就选择留在他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纽约。二十年的时间让纽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十年前,吉米选择了留在纽约。据《纽约史》记载,“纽约和布鲁克林加起来在1830年总计有22万人口,1860年达到100万,1890年为250万。纽约成为一个大都市,这里的一切都变样了”(弗郎索瓦 107)来自各国移民的加入,让纽约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因为彼时的纽约看上去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出生贫寒并不是成功的障碍。对于努力争取的人来说,纽约是一个能够伸手触摸到经济成功与社会地位提升的地方。即便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平等,但人们普遍将社会阶层可能的上升通道与纽约这个环境紧密相联。
1922年刘易斯·芒福德写道,“不想继续无知野蛮下去的人们应该成为都市人。这表示他们必须来到纽约,或参照纽约的流行行为准则。”(弗郎索瓦 236)因此,吉米选择留在纽约,他认为世上唯有纽约最好,诚如惠特曼所吟唱的那样,“啊!有什么能比我眼中桅杆环绕的曼哈顿更为壮丽、更加美妙?”19世纪的纽约空前发展,普通大众的劳动、资本、还有华尔街和珍珠街上人数微不足道的这部分人群所具备的创造和实干精神使“人们把纽约看作了大西洋上追商逐利的威尼斯”。(弗郎索瓦 封页)纽约的城市的活动、丰盛、气味、景致,使纽约人和游客迷失,使之徘徊在羡慕、憧憬与欣赏的情绪中。因此,欧亨利在其短篇小说《决斗》中写道,“纽约城里住了400万神秘的陌生人,他们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为着不同目的来到这里——亨利·哈德逊、艺术学校、假钞、鹳、缝纫女工一年一度的集会、宾夕法尼亚铁道公司、对金钱的热爱、戏剧、低廉的游览费用、大脑、各类小广告、结实的赶路用的鞋、野心、货运火车——这一切都参与构建了住在纽约的人群”,他们参与到和城市的持续“对决”之中,“好让它评判这些人到底是将要变成纽约人,还是维持粗俗的外乡人身份”。这种对决不仅仅是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对决、也不仅仅是城里人和外乡人的观念对抗,还有文明与野蛮、高雅与低俗、快节奏与慢节奏、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富裕与贫穷等各方面的冲突。
与此同时,各色移民给纽约这座城市填满了各种颜色。雅各布·里斯在1890年写道,“如果我们给城市地图填上颜色来区分人们原本的国籍,那么地图上的花纹会比斑马身上还要多,颜色的种类也比彩虹还更缤纷”。(弗郎索瓦 23)纽约的移民运动在1920年左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对于数百万移民来说,纽约是一座充满各种希望和承诺的城市。而这样的城市也充满了各色的冲突。欲望无法满足之后的失落、对金钱以及奢华生活向往而不可得的失意让这个大都市的罪恶在悄然滋长。罪恶需要正义来对抗。而警察恰好就是正义符号的化身。
因此,在《二十年后》的文本描述中,警察“昂首阔步”、“威风凛凛”“把手中的警棍舞出各种花样”的身体在纽约这样的空间中具有了一种威慑性的意义,特别是在暗黑的街道、漆黑的夜晚,警察的身体更具有了独特的空间领地特征。鱼龙混杂的欲望都市,罪恶在悄然滋长。各色移民都想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获得阶层的上升,获得财富的积累,书写属于个体的美国梦。最好的城市就是吉米一开始就选择生根发芽的纽约,所以对于这个城市,吉米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占有感,而警察这一身份更是赋予了他这样守卫和保护这个城市的权力意识和领地意识。因此,在吉米身上,权力意志体现得非常充分。吉米所持有的“警棍”无疑就是权力维护的象征,就像边沁的“圆形监狱”所形成的人的自发的自我监视机制一样,挥动的警棍所散发出的威慑力足以让任何人心生敬畏,更何况是对那些有不良企图的人。因此,吉米的“身体”所具有的一切特征都集中体现了一种权力意志。而在暗黑的街道上,无尽的黑夜似乎又放大了这种权力意志,让“警察”这一角色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沉沉夜色中大放异彩,让人心生迷狂而难以自拔。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类似于宗教意义上的审判悄然发生在吉米和鲍勃身上。吉米是手持正义之警棍的审判者,而鲍勃则成为了被审判的对象。二者之间,关于善恶、关于纯真和世故、各自的欲望之火在此处较量并发出悄无声息的碰撞,最后被消解于无尽的暗黑和凄风苦雨之中,埋葬于纽约过往的历史和被推倒的旧建筑的沙砾之下。
在吉米和鲍勃的对抗中,吉米身体特征展示了非常典型的警察形象,“警察”这一身份在夜色笼罩的街道显得光明而高大。而吉米本人所具有的个性化的面部特征却在衣领高高耸起,遮盖住面部表情的夜色中无法窥视。吉米作为人的个性特征无法展现,在欧亨利的笔下,他就是一个“无脸男”。“无脸男”吉米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由警服、警棍、昂扬的身姿组成的权力符号。而作为可供识别的吉米的“脸”,其特征则消失殆尽。吉米作为人的个性被抹杀,被模式化,而成为一种职能化的符号,他既可以是吉米,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人,他所要执行的就是警察这个身份赋予给他的权利和职责。因此,作为警察的吉米,在面对邪恶时,他必须实施其职能符号所赋予他的权利意志;作为个体的吉米,他在面对旧时的伙伴情谊时,其情感必须掩盖在“无脸”的面具下,注定是孤寂和悲情的。
3.特定场所的记忆空间——街道和五金店
“滑头鲍勃”和“无脸男”吉米在纽约的一个街道相遇。若是在白天,罪恶无处躲藏,一切昭昭然,故事的情节也不会如此的一波三折。欧·亨利不愧是一个老辣的作家。他把二者相遇的场景设置在夜晚下的五金店,也就是二十年前的饭店所在之处。因此,这个“场所”所在的位置如一个容器,收集了两个不同时间段所隐喻的各类事件,二者叠加或者被收集在同一场所,具有了互在其中的空间共时性特征。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曾说,“场所是具有清晰特性的空间”,“场所是存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场所还具有“精神”和“灵魂”。二十年前两人分手时饭店作为彼时在场的建筑物是二者友谊和誓言的象征;二十年之后,在饭店的残垣断壁中崛起的五金店成为了二者命运相交和冲突之地,是二者分歧的象征。如果说“民以食为天”的饭店代表的是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那么基于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相对单纯和充满善意和温情,靠天吃饭,彼此合作,才会共度难关。而饭店被五金店所取代也是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及商业社会的必然,五金店的工具性、实用性、消费性取代了人与人基于土地的淳朴关系。因此,这个场所虽然所处的坐标不变,但基于这个坐标上所发生的物质运动、城市的历史、政治、经济发展以及人的身份和心理活动的改变使二者命运的冲突成为必然。只不过,冲突大小完全取决于作者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欧·亨利不遗余力的将二者的冲突放到了警察与罪犯这两个极端对立的角色中,制造了欧·亨利式的典型结局。
假如二者在白天相遇于某个纽约的街头,那么二者的命运恐怕要改写,小说的艺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但欧亨利独具匠心,他把多重事件叠加后的冲突安排在了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而沉沉的夜色所具备的特征就是让个体的身份被模糊化,原初的生理性特征、社会事件、个体经历所赋予的可供识别的身体特征消失殆尽,于是个体可以在黑暗中毫无拘束的恣意妄为,释放自我,即便遭遇陌生人的眼光,也不用担心身份的暴露。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滑头鲍勃”放松了警惕,面对陌生的“无脸男”警察展示了自己心中隐藏最深的最原初的温情与善意。也正是在这样的夜色的掩护下,“无脸男”吉米通过巧妙的安排,规避尴尬的身份识别,从而完成了职业所赋予他的权力和正义。
三、结语
罗兰·巴特说,“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鲍勃的身体承载了美国“淘金热”的历史和“镀金时代”的特征,从历史的洪流来看,是一种向上的历史,“是身体向历史的进犯”;而吉米的身体,展现的则是作为大都市的纽约警察对权力意志的渴望和实施,表现为被动的权力改造,“是权力向身体的进犯”。(汪民安 15-21)因此,欧亨利通过在鲍勃和吉米身体上通过精心的设计,展现的不仅仅是善恶冲突的二元对立,更多的是在讲述西部空间、纽约空间、权力空间、场所等多重历史空间的中,不同身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