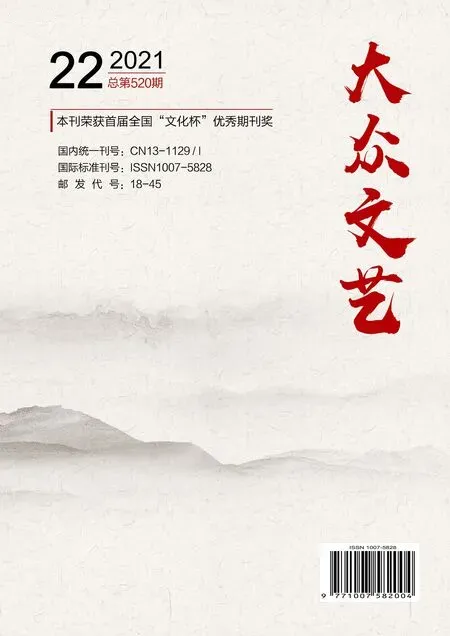论钟嵘《诗品》中嵇康的品第
殷诗诗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710100)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钟嵘的《诗品》是中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这两本理论专著先后成书于齐梁时代,但创作目的和品评标准都不一样。在叙述正始文学的代表时,刘勰明确提到了嵇康和阮籍。原文为“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在论述四言诗的时候,刘勰同样提到了嵇康,“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张衡)得其雅,叔夜含其润。”从刘勰提到嵇康的次数可知,刘勰是很重视嵇康的。可是,稍后于《文心雕龙》成书的《诗品》却明确将阮籍列为上品,把嵇康划入中品,针对这一差别,笔者进行了研究。
一、《诗品》的录诗范围和溯源流的批评方法
笔者认为,刘勰与钟嵘对嵇康的评价,之所以有差异,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待五言诗的态度不同。“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刘勰认为四言诗和五言诗风格不同,各有所长,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适合的诗体进行创作,但是他却强调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可以看出,他还是认可四言诗歌的正统性。《诗品》中针对四言诗和五言诗,钟嵘的看法是:“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对四言诗和五言诗的特点作了说明,与刘勰不同的是钟嵘直指四言诗的缺点“文繁而意少”,之后,更是提出五言诗才是“文辞之要”,强调了五言诗的重要性。在重四言,轻五言成为一种时代风气的情况下,钟嵘独树一帜,首先肯定了五言诗,是一种创举。在《诗品序》中他更是明确提出:“嵘今所录,止乎五言”,明确说明了《诗品》仅限于五言诗。既然《诗品》只收录五言诗,那么,钟嵘对所录诗人品第的划分,也必然依据的是诗人的五言诗成就。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嵇康的创作情况。嵇康,字叔夜,是三国时曹魏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和散文。诗歌现存五十多首。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其中四言诗数量占一半以上且成就也最高。而五言诗仅有《五言赠秀才诗》、《述志诗两首》等12首。从数量上来说,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从艺术性来讲,比之四言,也稍稍逊色。而阮籍作有《咏怀古诗八十二首》,不仅数量上高于嵇康,而且全是五言诗。
钟嵘顺应诗歌发展潮流,提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仅以五言诗的创作成就来评价诗人并划分品第的这种做法却有待商榷。这种做法对嵇康来说,本身就存在不公。因此,嵇康诗歌位列中品,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诗品》借鉴《七略》探溯源流的批评方法,将上品和中品的诗人划分为三大诗派,即《国风》派、《楚辞》派和《小雅》派。首先来看阮籍归属的上品。《诗品》上品共评价了12位诗人。源出《国风》的有《古诗》、曹植、刘桢、陆机、左思和谢灵运等六人。其中,《古诗》和曹植是直接源出《国风》,其他诗人则是间接源出。源出《楚辞》的有李陵、班姬、王粲、张协和潘岳等五人。其中,只有李陵直接源出《楚辞》。只有阮籍一人属于《小雅》一派。共同点是:直接源出三大派的诗人均属于上品。中品所列诗人则没有一个人直接源出三大派。阮籍条有“其源出于《小雅》”。而嵇康条则有“颇似魏文”,关于“颇似魏文”,《吟窗》诸本正作“其源出于魏文”。说明嵇康源出曹丕,曹丕条又有“其源出于李陵”,而李陵才是直接源于《楚辞》。
从渊源上看,阮籍是《小雅》派唯一的继承人,而嵇康只是《楚辞》派第三代的一个诗人,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可见,《诗品》录诗范围——只录五言和溯源流的批评方法均对嵇康的品第有影响。
二、钟嵘品评诗歌的标准:怨、雅、秀、词
钟嵘在《诗品》中明确主张风力与辞采并重。他认为诗歌创作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也就是说,好的诗歌要文质兼备。细读他对上、中、下三品诗人的品评意见,可以看出,在总的评诗原则下,钟嵘还有许多具体的标准。这些标准,大体上可以用怨、雅、气、奇、秀、词六个字加以概括。其中怨、雅、气属于质,奇、秀、词属于文。可以看出,钟嵘是文质兼尚,内容和形式并重的。
1.内容上:重怨与贵雅
《诗品》中,钟嵘写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在这里,钟嵘提到了诗歌抒发情感的两种方式,即:寄诗以亲和托诗以怨。从他引证的事例“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可以看出,对这两种抒情方式钟嵘并不是平等相待的,而是更加重视抒发怨情。“所谓怨,就是内心怨恨和心怀不满的意思。诗人往往由于不幸的道遇,志不能立,道不能行,自身又受到折磨。一腔怨愤,发而为诗,就是“托诗以怨”。”分析嵇康的诗歌明显属于“托诗以怨。”
从诗歌流派看,《国风》和《小雅》均源自《诗经》,共同的特点就是:重“雅”,而《楚辞》一派的特点则是“怨”,这已经是学界共识。嵇康属于《楚辞》一派,那么嵇康自然也重“怨”。
此外,我们还可以具体分析嵇康条,同样可以得出嵇康重“怨”的结论。《诗品》中,钟嵘评价嵇康称:“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即太过严峻急切,揭发质直,显露才能。结合嵇康的生平可知,嵇康在政治上是拥护曹魏,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在司马氏篡夺曹魏集团政权后,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导致他的诗歌带有“过为峻切,讦直露才”的特点。事实上,“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同样是表达怨情的一种方式,钟嵘的评诗标准是重怨的,为什么不满嵇康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怨而不怒的诗教传统的影响。具体到《诗品》中,这种怨而不怒就表现为“雅”。位居上品的班姬也很重视怨情的抒发。在《怨歌行》中,她以团扇自喻,抒发了帝王之爱不长久的感叹。虽有怨情,但是更多的却是一种自伤自怜,并非对帝王的直接攻诘。正如李因笃《音评》中所说“《团扇》之歌,怨而不乱”。可以看出,班姬的诗歌是既“怨”又“雅”。而嵇康的诗歌《述志诗》:“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蛙宅。神龜安所歸。”则明显有“峻切”、“讦直”的特点,而“伤渊雅”,因此,是只有“怨”而没有“雅”。
综合来看,嵇康的诗歌表现了怨情,却“过为峻切”,“讦直露才”,所以有伤“渊雅”。对于“怨”“雅”并重的钟嵘来说,自然不是完美。
2.形式上:爱“秀”与慕“采”
“诗之秀美流丽,主要是指状物之妙,得其风流媚趣,文体华净,诗句自然婉约。秀本指禾穗生花,一切草木之花也称秀。“英华曜树”,就是秀美的表现。臂诸文学,指的是形象鲜明,警句挺拔。”钟嵘认为在建安诗人中,以文秀见称的是王粲,因为他作诗懂得“状物之妙”,诗歌极富形象性。他的《七哀》因真实描绘了董卓之乱后,长安附近的社会图景而被钟嵘视为五言诗的代表作。
钟嵘总结汉魏六朝诗歌创作经验,对兴、比、赋作了新的解释:“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在这三义中,比需要“因物喻志”,赋需要“寓言写物”,可见,比和赋都要通过创造物象来抒情写志。可以看出,钟嵘很重视诗歌的形象性。
《诗品》中,钟嵘称嵇康的诗“讬喻清远,良有鉴裁。”就是对嵇康的诗歌具有“秀”的品格的赞赏。讬喻就是讬物以讽谕。通过创造物像来进行讽喻,从而抒发自己的一腔忧愤,嵇康的这种表达方式既体现了钟嵘“重怨”的标准,又符合他“爱秀”的标准。因此,钟嵘对嵇康托物寓志的写作方式还是很赞赏的。《诗品》中多次提到嵇康的诗,其中《五言赠秀才诗》是钟嵘最称道的。诗歌全文如下: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嵇康以“双鸾”自喻,运用比兴手法,“矫健低徊”(陈柞明《采菽堂古诗选》),道出自己不愿出仕而又欲隐不能的痛苦心情,含蓄婉转,让全诗笼罩了一层慷慨多悲的情绪。
如果说,嵇康的诗在形式方面因为“文秀”而受到钟嵘的认可的话,那么,在丹采方面,钟嵘对嵇康则是否定的。爱慕词采华茂,是钟嵘艺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评价诗作高下的一条很重要的标难。文秀与词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是指形象秀美,一是指词采富丽。钟嵘评诗,既重视文秀,更重视词丽。事实上,钟嵘《诗品》除了定品第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溯源流。《诗品》中,钟嵘虽没有正面评价嵇康诗歌的词采,但通过“颇似魏文”这一总的评价,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东西。钟嵘评价曹丕诗“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对比钟嵘对曹丕和嵇康的评价可以看出,二者基本上没有相似点。那么,“颇似”就只能是语言方面的相像了。在钟嵘看来,曹丕的诗歌语言粗鄙、质朴,如乡间俚语,没能做到“辞采华茂”。那么,可以推知,嵇康的诗歌语言在钟嵘看来,也是质朴,缺乏文采。
总之,钟嵘认为嵇康的诗歌“讬喻清远”,借用生动的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秀美的体现。但与此同时,嵇康的诗歌语言却“鄙质”,不够华丽,因而是缺乏丹采的。
三、小结
综上所言,钟嵘将嵇康的诗歌列为中品有着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原因。客观上,《诗品》录诗以五言为主,对仅有十二首五言诗的嵇康来说,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此外,由《楚辞》派人数众多,而嵇康只是《楚辞》派第三代的其中一个诗人,所以,重要性也会受到削弱。主观上,根据自己的诗歌评价标准,钟嵘认为嵇康的诗歌在内容上重视抒发怨情却不够文雅;在形式上,虽达到了秀美的标准,语言却不够华丽,过于质朴。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钟嵘才将嵇康列为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