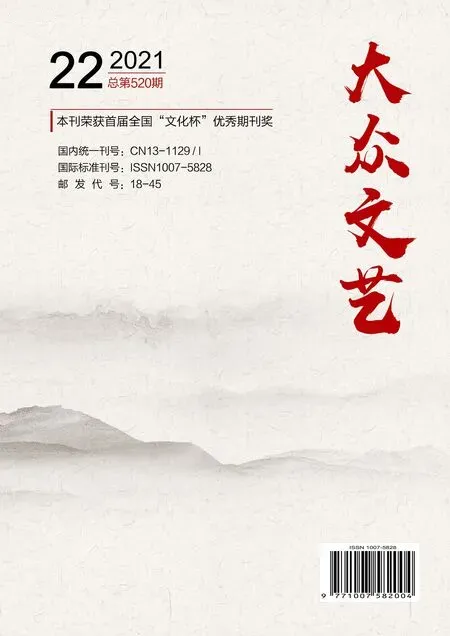从叙事格局看《最后一个匈奴》的叙事特征
刘 莎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710100)
《最后一个匈奴》不像西方小说一样按照一个大致的时间来叙述,而是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征。读者或者批评家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叙事学的影响,对一部作品的评价也往往是站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中观照,这样无形之中会陷入”影响陷阱”,不盲目的使用西方的理论解读一切作品,从文学文本本身出发,发现作品叙述的内在特征成为一种必要。本文试图从叙事格局的角度来阐释《最后一个匈奴》的叙事特征。
一、模拟话本小说的传统叙事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以口述为代表的说话艺术都在文本中显现出叙事者和叙事接收者这两个角色,于是,在文本其实已经丧失了作者的主体身份,而实际上小说本身只有编辑者的身份,但是,编辑并没有权威性,甚至并不能参与故事,只能为读者”讲述”自己知道的故事,讲述者并不参与故事的情节推动。在《最后一个匈奴》中不断的出现“亲爱的读者”“叙述者觉得”“各位”这样的词语,叙述者总是模拟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说话的方式,让读者无时无刻的能感受到叙述者的存在。而在这里小说中出现的“读者”“各位”并不是真正将会阅读的读者,他只是在小说文本中作为一个叙述接收者而存在的人物身份,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性质的人物。也就是说,实际上《最后一个匈奴》中叙述者和叙述接收者的同时存在保证了叙述的顺利进行,而这一叙述格局也恰恰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所形成的一种叙述程式。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叙述者仍然使用传统的叙述模式控制并且指挥叙事行为的发生。
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叙述者与叙述接收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被架构起来,作者创造出来的叙述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呼唤叙述接收主体,与叙述接收者直接交流,完成传达和叙述的职能。小说于是形成了叙述者与叙述接收者的对话。
二、控制叙事进程的叙事者
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叙事者常常跳出来控制叙述进程,充当指挥官,假设叙述接收者的反映来对其叙述进行解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使读者对故事脉络清晰。于一部跨越时间较长的历史小说,其最为重要的就是脉络的清楚。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1p593在小说中,作者经常使用“不提”“容后再叙”这样的语言,我们能够在阅读中勾勒故事的框架。表面上来看,叙事者控制着叙事的进程,实际上,这种叙述方式反而构成了阅读的一种障碍,使文本具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意蕴。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就隐藏在作者所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因而,《最后一个匈奴》中,叙述者也不遗余力的给我们讲述陕北高原的民风、民俗。这对于叙述文学来说算是一个致命伤,因为它的存在会影响叙述的进度,并且会让叙述变得凌乱。而叙述者与叙述接收者的直接对话,直接显在的出现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晰的从民俗中跳脱出来,回到故事情节本身。在第三章,对黑大头家事进行讲述的部分,中间插入了大篇幅的对陕北民间赌博形式的介绍。紧凑的故事情节因为民俗的加入而使得整部小说叙述速度减缓。而作为读者也很容易因为情节的中断导致故事的支离破碎,叙述者这个时候出现,写道:“赌博的各种花样,上面挑出两种,就近详谈,一则……二则……所以这个交代,不算浪费笔墨。”1p59除此以外,还会涉及到小说文本中出现的地名的来源的讲述,在第十七章中,叙述者讲述了肤施城名字的来源,长篇的叙述,让读者进入到神话传奇之中,这个时候,叙述者出场,“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这一年一个初夏的晚上…..”1P312叙述者一把把叙述接收者拉了回来,回到故事之中。这样即使有民俗、传奇故事的插入,中断了叙述,也最终不会使小说本身讲述的事件消解在民俗、传奇故事之中。
三、凌驾于叙事者之上的评判者姿态
《最后一个匈奴》中叙事者往往跳出来说话,叙述者凌驾于文本之上,从自己的角度对叙述的对象加以解释或者评判,这是叙述者展示自己态度的最佳时机,使读者能够最终能够获得对于作者所认定的“正确”理解的叙述序列之中。这是一种叙述者自我意识的展现,作者的声音变得突出和鲜明。
很多现代批评家认为,展示是艺术的,讲述是非艺术的,这是两种对立的叙述方式。布斯不同意这种划分,他指出,早期小说家讲述的一般故事,较之现代小说家肤浅地展示出来的场面,有时看起来却更为逼真;有一些作家评论损害了作品,而有些作品中冗长的评论仍然吸引读者。1如果可怜的杨娥子知道,她将为这一个月,付出一生的代价,或者说这一个月的时间,挥霍了她一生的快乐的话,那么,她将要好好地享受这一个月,使用这一个月。1P271在这里尽可能的展示,让我们不断的对杨鹅子的故事持续发生兴趣。
四、极力彰显的叙事可靠性
真实性一直是中国传统叙述所孜孜不倦所遵循的原则,但凡加入虚构成分的文本都被列入好小说之外。因此,在中国传统叙事过程中无一不会标榜自己对于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极力的伸张自己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这一点,在《最后一个匈奴》中也频频出现,极力的告诉读者自己故事的真实性。
“相信我,亲爱的读者,……我们说的是吴儿堡的事,是襁褓中的杨岸乡,是乳汁尚像山泉一样奔涌的这位年轻母亲。”1P240不断的与读者进行交流。“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愿意在这里,再引用一段斯诺先生珍贵的笔墨。”1P222直接引用历史,展示历史,这算是对社会状况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却引用别人的,并且告诉读者,这可能会有不全面的地方。
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会不断的假设读者对这么离奇的故事的质疑,不断的申诉自己是如何看到的,甚至不息暴露自己的写作技巧,或者是不断的召唤叙述接收者。“我们权且叫他们张三李四吧,谁叫这两个人名突然溜到了叙述者的笔下。”这里充分的展示了叙事的不确定性,叙事者连同名字也是随便胡说的,这里以名字作为能指的内容与所指之间形成了一种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没有消除理解的障碍,反而使毁灭了能指和所指链接的东西:真实性在这里顿时消解。
在传统叙事文学中,叙述者之所以不断的告诉读者,故事是真实性不容置疑的原因在于,中国叙事传统对真实性要求的思维特征所决定的,从内部来看,实际上也反映了小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叙事者与叙事接收者之间的一场战争,叙事者担心自己讲述所产生的传达效果。叙述者这种岌岌可危的地位不得不使得其使用大量的干预来维护叙述者的掌控地位。
这里所说的叙述者可靠,实际上指的是,叙述者所描述的故事不管其是否真实,至少应该从叙事者的角度让叙述接收者认为这是真实的,那么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就必须要对所写的故事做权威表述,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将其虚构的真实当作真正的真实。所以,叙述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明确的告诉读者自己还有不知道的情况,以这样半知的事实,以确保叙述接收者能够信任所写故事的真实性。实际上,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叙述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似,因为,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导致的对于叙述内容真实性的强调。而《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受到传统叙述格局的影响是无形之中的。
五、结语
《最后一个匈奴》叙述者的不断出现,以及对叙述接收者的召唤,更接近的是中国传统叙事的程式,文本中,作者摒弃了只对重大事件进行描述的写作手法,而是会将民俗,包括一些琐碎的平凡生活事件插入,因而,讲述故事的方式不能够再像传统小说一样把每一个故事都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头到尾的展开。作者需要使用一定的技巧,将这些琐碎的细节同时展现给读者,所以,整部小说因为这样的叙事方式而使得事件的因果关系消解在民俗、信天游中。这样无形之中使故事的因果关系变得松散,淡化了故事情节,也带来小说的浪漫主义的特征。
注释:
1.“展示”就是作家客观地将故事展示给读者,如同戏剧在观众面前演出一样,作家不再作品中露面,也不对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流露感情或者发表评论。“讲述”就是作家或者作家的可靠叙述者直接在作品中出面,对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做出判断。它是传统小说使用的主要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