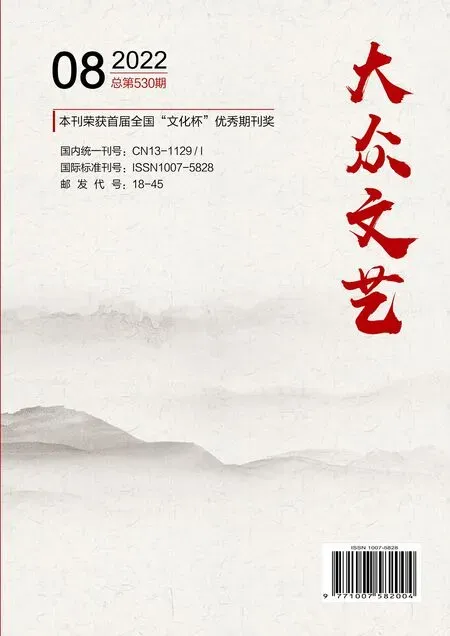从《虞美人·听雨》及其《竹山词》之意境探蒋捷一生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院 210000)
蒋捷,南宋词人,字胜欲,号竹山,宋末四大家之一。咸淳十年中了进士,不久南宋亡,他志不仕新朝,深怀着亡国之恨漂泊于江浙一带,隐居于竹山,度过孤苦的后半生。由于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极少史籍资料记载,只留下九十多首的《竹山词》流传至今,因此我们只能结合他的词作对他作一个大概的了解。在他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听雨》中,通过少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的“听雨”描写,他归纳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心境变化:少年不识愁滋味、壮年漂泊冷清清、晚年归隐寻心安。
一、无忧之境——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蒋捷在南宋灭亡之前,也曾度过一段美好的少年时光。“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亦是他年少时期的写照。与其他文人一样,蒋捷也有过风流韵事,醉倒在石榴裙下,倜傥无限。也“为赋新词”愁过,如《祝英台》次韵:
柳边楼,花下馆,低卷绣帘半。帘外天丝,扰扰似情乱。知他蛾绿纤眉,鹅黄小袖,在何处、闲游闲玩。
最堪叹,筝面一寸尘深,玉柱网斜雁。谱字红蔫,剪烛记同看。几回传语东风,将愁吹去,怎奈向、东风不管。
开头“柳边楼,花下馆”在蒋捷词里常出现的处所,无论是《荆溪》里回忆出现的“花外楼,柳下舟”,亦或是《听雨》里的“歌楼”,都营造了风流少年寻花踏柳的无忧之境地,且是他少年时光的象征。烟柳浮华之地,以及莺歌燕舞、日日笙歌的生活,热闹非凡,多的是闲愁。于是下闕便抒写了思春之愁,与情人的缠绵悱恻,加上蒋捷细腻柔软的心理,抒发了他东风都吹不尽的绵绵情愁;所以少年时期,听的非雨,而是热闹与闲情。
二、孤寂之境——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蒋捷的壮年,充满漂泊羁旅之感。以舟、江以及断雁作为寄托情感的意象,象征了漂泊无定的羁旅生涯。中年时候的雨多了岁月的气息,多了飘零的失落意味。在异乡,在辗转奔忙的路上,在催人悲泣的客舟中,听雨,怅然迷茫。他在这漂泊过程中,也写下了许多反映身世变化的词,如《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绵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漂泊是蒋捷在壮年时的常态,荆溪的雪恰好让他的脚步停滞片刻,江上翱翔的白鸥使蒋捷踌躇,到底是“身留”?还是“心留”?借了白鸥之口问出,营造了苍白孤寂之境。“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面对茫茫江海,自己身如浮萍,发出身寄何处的喟叹。问题只有词人自己能回答,进,无法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退,却无“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旷达。南宋的灭亡、祖传家教的忠君爱国思想以及孤苦飘零的经历使他内心无法安定,而后他又忆起旧游,“依然是,未愁绝”,心事锁眉头。王国维曾在他的《人间词话》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1由此来看,“白鸥问我”这一界面的描写正构建了“我”与“白鸥”二者间的对话,于此境中只“我”与“白鸥”,前者抒情,后者再承情,互相呼应的情感交流,构成清新明朗的意境,同时用拟人手法表现了若有若无的感情线,我于白鸥,白鸥于我,是互相构成空寂飘渺的境界前提,两者让意境自然、和谐,更加浑然天成,不留痕迹。人在愁绪萦绕心头时,一有闲暇,便会思考生命中的困惑,这种灵魂的自我叩问让感情显得更自然真实。
另外,蒋捷另一首词《舟过吴江(一)一片春愁待酒浇》中“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句,尤为后人关注,更多人对其写作手法、用词上做了研究与批评,其实整首词表达的感情亦有值得研究的价值。光阴的流逝与时序变化、植物的季节变迁牵动了在异乡为异客的词人敏感的内心,离家漂泊的生活使他在大把时间中与船、与江河为伴,从他的诗词中也可知道,即使再久,他也无法融入当地的环境,无法安下自己的心,必须以“客”的身份栖居他乡,可见他牵挂家国思想的一种执拗。
三、旷达见浓愁——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听了无数点滴雨,看尽悲欢离合,这个时候他也告别了漂泊,暂时安定。此时,他寄居僧庐,听夜雨寂然而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看似心如止水,波澜不起,可彻夜听雨不眠,便已揭露了作者五味杂陈的心。末句“余香有尽,回味无穷”,构成了审美理想,是直观形象与理性观念的结合。雨为眼前所见,耳边所闻,心中的感悟便是无形的观念性,构成了“美”的理想状态。所以许多人在读到这句的时候与作者感受到的悲哀之情不免油然而生。2
家国灭亡以及孤苦漂泊、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经给蒋捷带来不可思议的心灵创伤,特别是出于人格上选择的不与他人交流的生活方式,让他与其他宋末三大家与众不同。蒋捷出生于家底丰厚的功臣世家,家祖是爱国的忠士,家学的传承奠定了他忠于宋室的思想,他是一个彻底的南宋遗民,当时的南宋三大家也都与新朝有染,而他独独不愿意与之交往,所以宁愿独自飘零,游于吴越一带做个他乡之客。种种现实环境促发了他的隐居思想,同时接触了佛道思想,后来便隐逸于竹山,有词《少年游》:
枫林红透晚烟青。客思满鸥汀。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
春风未了秋风到,老去万缘轻。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
从中看出,即使到了晚年,仍以为“无家”可归,爱竹却无地可以植,以借为名,实则仍盘旋在故国乡思中。末尾“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看似是只能把余生寄托于闲吟咏赋的生活中,实则苍凉无奈,旷达超然、隐忍超脱实是无奈之举。而在《虞美人·听雨》中,“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更多的是无奈无力之感,或许是因为家国无望收复的意难平,或是前半生漂泊无为的生命之思,抑或是看破生命中离离合合的情感经历而进行的无奈之思考,《九歌》中“固人命兮有当,疏离合兮可为?”亦是同样对待人世间离合的无可奈何之叹,深以为这是千古以来都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这里面蕴含的愁情,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辗转柔肠并非直言“愁”。有如温庭筠《更漏子》的末句,“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 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同样是写雨,但从整体来看,温词更着重于眼前景以及眼前情,蒋词则有人生变化起伏之感,多了情感的细腻描写。但两者“任雨滴到天明”有异曲同工之妙,虽不言君与国,但淡语足以道悲情。
四、结语
在《竹山词》中,蒋捷最常抒发是情感是“愁情”,无论是春愁、乡愁、飘零羁旅之愁,都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壮年漂泊他乡为异客,家国心事无尽愁,晚年听雨僧庐下,愁情似淡而更浓。那雨贯穿了蒋捷一生,年月流逝之伤,漂泊辗转之苦,国破家亡之痛,这些疼痛随着岁月散去之后,他听了整夜的雨,回头环视整个人生,以个人身世进行反思,忽然明白生命的意义:悲欢离合总无情。他所体味的生命意义就远比那些闲愁自来、强自为愁的生命意识要更深远,更贴近生存状态。我们透过这首高度概括凝练他这一生的词,终于明白了他“欲语还休”的愁苦。
注释:
1.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02.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