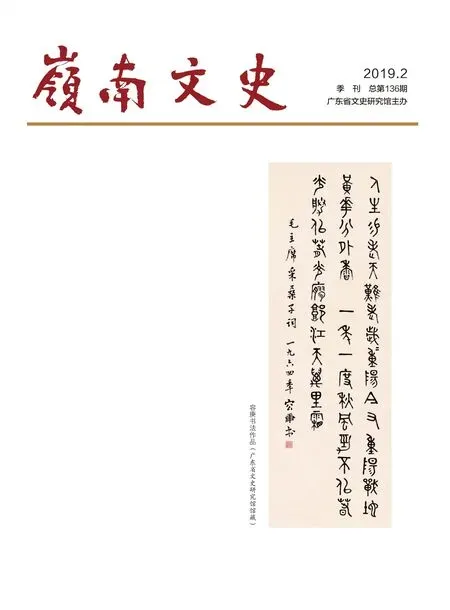法国租借广东藩司署
李颖明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西段北侧一带,1995年、1997年先后发现南越国石构水池及曲流石渠遗址,两次获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备受关注。2003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仔细清理,除发现西汉南越国和南汉国的宫殿遗址外,还有其他历史时期广州地方衙署的多处建筑遗迹。其中清代广东布政司署东侧的附属建筑遗迹保存最好。[1]
南越国宫署遗址附近地区历代建筑多样,遗址区域内的地层堆积较为复杂。其中第二层为近现代和清代晚期文化层,发现有法国领事馆后花园建筑遗址等;第三层为清代文化层,发现有清代广东布政司署东侧附属建筑遗迹等;第四层为明代文化层,发现有明代广东布政司署建筑遗迹。[2]本文结合考古发掘成果、现存历代广州地图、文献及档案等各种资料,重点整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租广东藩司署的过程,以期加深了解当时广东历史。
一、博物馆原是旧衙门
南越国宫署遗址经过十多年的大规模发掘以后,在2009年开始筹建博物馆,至2014年南越王宫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对照现存历代广州地图,如今博物馆的位置在明清“广东布政使司”(今广东财政厅)之东,“城隍庙”(今存)之西,[3]自元末至清代,先后为“理问所”[4]“禺山书院”[5]“关帝庙”[6]“武庙”[7]“容丰仓”[8]等。
广东布政使司始设于明代。明初沿用元制采用“行中书省”制。明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并设布政使一职,掌一省行政事务,国家政令由之宣达府州县,故谓之“承宣”,简称为布政使司。[9]清代布政使司之布政使又称为“藩司”“藩台”或“方伯”,如古代之藩镇而称为“藩司”。清代的布政使为从二品官,与巡抚同。职能与明代相似,掌一省之行政,管理全省财赋的出纳。布政使本为外官首领,“自乾隆以后,督抚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布政使便失去行政上的独立性,而类似今日的民政、财政两厅的厅长了。”[10]而理问所在明清时,是布政使司所属机构,职责为“堪核刑名”,即堪核有司量刑执法是否合于当朝律例。清代只有直隶、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和湖南等省的布政司才设理问所,只设从六品的理问一人,裁去明代设有的副理问、提控案牍等官职。[11]
广州博物馆仲元楼展区碑廊内有两方明代碑记《理问所重修记》《重修理问所记》,均记载明代广东布政司理问所重修事宜。原置广东布政使司署内,后移置该处保存。依碑文[12]及明嘉靖四十年(1561)修《广东通志》[13]内容,可知理问所最初在景和街,洪武二年(1369)由理问崔俨开设。洪武二十六年移至广东布政使司仪门之左。正统十三年(1448)理问李珩重修,弘治三年(1490)理问贺廉再重修。[14]
考古发掘中,发现此处明清两代的建筑遗迹不少。“建筑风格和布局也很相近……建筑平面布局紧凑,每户建筑一般由门房、天井、厅堂、厢房等构成,内部宽敞,厅门贯通,属于宅第式建筑风格。屋外是巷子和道路,有的路面铺石板。房屋的天井和屋外道路下发现有渗水井等排水设施。”[15]在布政使司署东面的建筑可视为其附属建筑。
清代这一带曾一度作为禺山书院、关帝庙、容丰仓等,位置上是在布政使司署东侧建筑群更东面,比较靠近城隍庙。这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体现,在近现代和清代晚期文化层内,发现有法国领事馆后花园和禺山书院等建筑遗迹。而在清代文化层内,则发现有容丰仓和清代广东布政司署东侧抚署建筑遗迹等。[16]这里着重厘清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租广东布政司署的历史渊源。
二、武力胁迫下的租借
1857年(清咸丰七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29日即占领当时广州城的最北也是最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并在此驻扎,广州城失守。次年1月5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及两广总督叶名琛先后被俘,前两人被带往观音山,而叶名琛则被送上英军炮舰,一个月后被送往印度加尔各答。为了管理广州城,联军选择扶持原来的政府,再成立占领委员会严加监督,将当时的广州当局变为傀儡。占领委员会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对英法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冒险试验;对中国而言,这是将近四年屈辱合作的开始。[17]1858年1月9日,广东巡抚柏贵在联军的挟持下,回到抚署复职,但“独住四堂门外,层层守以洋兵,盘诘甚严。”[18]从柏贵开始,继任督抚均被联军严密监控,“逐日派夷官在抚署收呈办事”。[19]因此沦陷期间,英法完全控制了广东的政权,大肆搜刮财富。
广州城的失陷只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端,英法联军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挥军北上,进犯上海、天津乃至北京城。到战争的尾声,咸丰皇帝出逃,北京城破,圆明园被毁。1860年10月24日,中国与英、法分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战事终于缓和下来。1861年(咸丰十一年)2月,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中外谈判密锣紧鼓。
既然和约已成,归还广州城自然提上议事日程,但英法并没有放弃最后获取利益的机会。正是以归还广州城为由,法国强行租借了广东藩司衙门。
《天津和约》附款《中法和约章程补遗六款》中规定,中国赔偿法国军费“约有二百万两之多”,可“分六次,每年一次交清”,而“中国将上款所开银数,或用银两,或用海关会单,一经交清,大法国军兵即时退出粤省,惟以军兵及速退出之便,中国欲将各会单,或先期,或按次,分明年号交出,在领事官署寄存,亦无不可。”[20]按照条约规定,归还粤城当在扣款还清之后,但英法早就希望从中国的战事中抽身。于法国而言,1858年炮轰越南,开始对越战争。此时法国正需要大量兵力投入到越南战场,因此急于从中国撤军。况且对英法而言,在中国大局已定,增开口岸、大量的割地赔款以及各种各样新增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北京城也已允许公使进驻,而一直异常排外的广州城也已畅通无阻。因此驻兵广州已不再是明智之举,英法只急欲从中抽身。
1861年(咸丰十一年)1月16日,法国领事哥士耆往见劳崇光,以先行退出广州城为条件,谋求租借广东布政司署衙门:“称条约内本有扣款清楚,再行退出广东省城之议。今既和好,拟不俟银款扣清,先行撤兵,将粤城让出。惟广东藩司衙门上年经伊国出资修盖房屋,此后欲出资赁与领事官永远居住。”并承诺“如果允行,不惟法国退兵,即英国之兵亦可令其退出。”[21]
租借藩署的要求立刻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反对,[22]一来“藩司为一省长官,而衙署为夷人所据,则官之号令将不行于百姓。官失其势,变乱易兴”。这是面子问题;二来“查广东藩司署,适居粤城之正中,四面与民居铺户毗连,规模极其宏敞”。这是华洋分治民夷相隔思维的延续。但当时主理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则有不同见解:[23]他认为法国之所以急于退兵乃“为省费起见”,这与当时法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情况基本相符;而欲租借城中衙署,则是“恐全行退出后,该省居民不令再行入城,是以豫留地步”。而且法国开出的可令英国一律退兵的条件,也让恭亲王颇为心动。奕訢在主理洋务时,实是“遇事委曲求全,亦只能权利害之轻重”,始终抱持两害取其轻的思维。因此在处理法国租借藩司署问题上,“权其事之轻重,与其使之久据省城,不若使其盘居衙署。”最终同意租借广东布政司署衙门予法国,惟力争在租约上将“永租”改为“暂住”。其租约如下:
为租契事。兹因大法国协办全权事宜参赞大臣哥,面称广州府旧城内从前布政司衙门地基房屋花园,现在法国已经建盖房屋,欲将此地租为法国领事官居住,不作别用,每年中国十二月十五日,由领事官派人将次年租价洋银三百元送交广州查收,一俟法国兵弁退出广州府旧城,领事官即当移入此署居住。如将来和约内扣还之款交清,退出广东省城时,将所租布政司衙门地基房屋花园,一并交还。彼时如中国仍欲将此地租与法国领事官居住之处,任听中国自便。为此立据,按照哥大臣所言及租价,将广州府布政司衙门地基房屋租与大法国领事官居住。俟扣款交清,退还广东时,即照以上各言办理。除将此据作为租契交大法国钦差全权大臣存收外,另行咨照两广总督查照。须至租契者。[24]
事实上,在英法联军控制广州的几年间,藩司衙门已被占据多时。在攻占广州城后,联军于 “观音山上下,该夷已自用经费万金,建造兵房,……其意已为长久计。” 咸丰九年(1859)广西巡抚劳崇光调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7月11日入粤城接印视事,当时“观音山、及将军衙门、藩司衙门均被占住”。[25]当年秋,耆龄调任广东巡抚,发现“英、佛夷酋现踞将军、学政、藩司三衙署及广州府、南海县两学宫,以为办事之所。”[26]可见,藩司衙门的所谓租借,只是将既成的事实加以确认。奕訢不愿因一个既成的事实而阻碍英法退出粤城,与其一贯处理洋务的思维颇为一致。
然而,反对租借的大臣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英国以法国租得广东藩司衙门为借口,也要求租住将军衙门。巴夏礼申辩“两国事同一律,断无法国领事准住城中,英国领事独不准在城居住之理。”[27]当时离约定退兵的日期1861年10月12日只有数十日时间,劳崇光认为当前尤以退兵为重,万一英国要求得不到满足,延迟退兵,则不好交代。劳崇光查得将军衙门“二堂后东边有楼房二间,群房数间,并空园荒地一段。若将二堂后墙门堵塞,另于园内开门出入,与将军办公之处两无干碍。”[28]其实将军衙门早于数年前作为英军办公之所,进城不久英国即“修理将军衙门居住,门楣重新改换鬼样,并油漆铺垫等项,需约七八千银,系向柏贵勒提关税及军需局经费,派员解往。”[29]1858年2月初,联军官员即“搬进将军衙门居住,……将军搬居都统署内。”更“于署外另竖旗杆,欲竖该国旗号。”[30]因此,英国租住将军衙门也不过是承认一个既成事实而已。
清咸丰十一年(1861)10月19日早晨,中国与英法联军举行广州城的交接仪式。10月21日联军正式撤离。广州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广州。英国于将军衙门后建设领事馆。1865年沙面竣工,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迁入沙面。法国则于广东布政司署衙门建设领事馆。从清光绪年间的《粤东省城图》[31]可见,当时布政使司东侧、城隍庙西侧标注“法国领事”字样。法国领事在此处办公多年,“各国领事馆皆驻节沙面,惟法国领事则有一署与藩署为邻,和议既成,照常居住。”[32]而“由于外国领事馆等外事机构需要培养人才充当译员,因而附在领事馆内开设一间以学外文为主的书院,从事培养翻译工作人员。”[33]此即为丕崇书院。[34]直至光绪十六年(1890),法国领事馆才迁入沙面法租界。[35]
据2010年出版的《广州市志》所载,民国17年(1928)3 月,朱兆莘呈奉广东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向法国领事交涉,收回法国领事馆旧址。法国领事呈报法政府同意后,应允将该址无条件交还。9 月24 日,法国驻广州领事丹恕将该址正式交还。朱兆莘与丹恕签立字据,补偿法方建筑费1 万元。9 月27 日,由中方正式接收管理。
三、“两害取其轻”的教训
法国在强租藩司署之前,已在广州成功租借新城内的原两广总督署,作为其建设教堂之用,[36]而英国也已与清政府达成一致,以沙面作为英租界。[37]法国租借藩司署和英国租借将军衙门后堂时,正是以沙面租界未臻完善,需要地方作领事人员临时办公之用为由。事实上,扰攘十多年之久的广州入城问题,早已让英人对广州人民心生畏惧。在建设沙面之时,人工挖了一道宽四十米,长一千二百多米的小涌(即今沙基涌),与陆地相隔,并建东西两桥来往沙面,使沙面成为一个小岛。一方面是考虑到岛内的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有着强烈的严防华民的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租借老城中央的藩司署及将军衙门,更多应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是对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报复性举动,强占衙门以令中国政府荣誉扫地;二是如恭亲王奕訢所想,英法希望能“豫留地步”,以防广州人民在其撤兵后重演反入城斗争的故事。法国长时间内依然以藩司署东侧为其领事馆所在,因此与民众时有摩擦发生。[38]这也正是英国在选择沙面为租界时所极力避免的情况。
对清政府而言,广东藩司署的失落完全是“小事”,但从法国强占的过程中,亦可折射出当时清政府办理外交的一些特点。学者王尔敏在归纳耆英在主理洋务时的一个原则是“不事苛求,务存大体”。[39]以耆英自己的话说就是“体察夷情,揆度时势,熟审乎轻重缓急之间,不得不济以权宜变通之法。”[40]这一办理洋务的原则,从耆英到恭亲王奕訢可谓贯彻始终。就法国盘踞粤城而谋求强租藩司署而言,奕訢“权其事之轻重,与其使之久据省城,不若使其盘居衙署。……惟以藩署与省城相较,似省城为重,藩署为轻,设使不与租住,而省城竟不交还,则省城且不能与之较论,何在藩署?”[41]在权衡之下,当认为省城为重、藩署为轻,因此顺理成章同意租借。
然而,退兵是双方所订条约规定,但租借则为条约所无。这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国欲以归还舟山为要挟连带解决广州进城问题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当时耆英对此严加防范,抱定宗旨“唯有固守成约,责以大信,令其退还舟山。而进城之准行与否,则决之民情。”[42]最终成功将舟山收回而未牵扯到其他问题。当然,舟山自不能与广东省城相比,而时移势易,清同治元年(1862)与道光年间的清政府相较,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恭亲王奕訢同意租借广东藩司署予法国,似是无可奈何之举。纵观清末情势,正是在这种“两害取其轻”的外交原则下,中国的土地、主权逐渐丧失,可说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注释:
[1]《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3期。
[2]南越王宫博物馆编:《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页,2010。
[3]自元末以后的历代广州地图可见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
[4]《广州府境之图》,见《永乐大典》。为目前发现最早的广州地图,《图说城市文脉》,第3页。
[5]《隶省地图》,明朱光熙、庞景撰《南海县志》,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间刊刻。《图说城市文脉》,第9页。
[6]《广州府城郭图》,见清郝玉麟撰《广东通志》,雍正九年(1731)刊印。《图说城市文脉》,第18页。《县治附省全图》,清潘尚亭撰《南海县志》,道光十五年(1835)修。《图说城市文脉》,第21页。
[7]《全城图》,清任果撰《番禺县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印。《图说城市文脉》,第20页。
[8]“容丰仓,在城隍庙西。清同治六年(1867),改建禺山书院,仓迁于学宫前禺山书院旧址。”黄佛颐编撰:《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84页,1994。
[9]俞鹿年编著:《中国官制大辞典》(上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648、750页,1992。
[10]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第214页,2001。
[11]《清史稿》116卷,志九十一,职官三。
[12]见《理问所重修记》碑。
[13]明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修《广东通志》卷二十八“公署”条记载:“承宣布政司……少东为理问所,旧在景和街,洪武二年理问崔俨开设。洪武二十六年改入本司仪门之左,案牍厅、司狱司隶焉。正厅三间、脏罚库三间、公廨三所、吏舍一十八间。”
[14]关于理问所的详考可参阅陈鸿钧《两方明代广东布政司理问所碑记考》。《岭南文史》2009年第3期。
[15]《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第28页。
[16]南越王宫博物馆编:《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页,2010。
[17]关于占领委员会及沦陷时期广州的情况可参见郑爽:《英法联军占领时期的广州(1857-1861)》,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8]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中。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7页,1978。下引简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19]《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英法袭踞粤城传闻异词照钞粤商寄楚信缄呈览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138页。
[20]《中法和约章程补遗六款》,《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583页。
[21][23]《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訢等奏英法退出粤城并法国欲租藩司衙署酌量办理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449页。又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6。
[22]《福建道监察御史许其光奏法国借住广东藩署碍难允准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455页。下引为此折内容。
[24]《抄录为将广州布政司衙门旧地租给法领事居住给法国租契》,《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452页。
[25]《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劳崇光奏入城视事并接见英法官员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93页。
[26]《广东巡抚耆龄奏探闻英军占据粤城地方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314页。
[27]《两广总督劳崇光奏英法约期交还粤城但仍借地居住片》,《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526页。
[2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
[29]《两广总督黄宗汉奏入粤后探访英军占据省城地方情形并预为布置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376页。
[30]《抄录上海粤商接粤东关于英法军搜封军器等情来信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197页。
[31]《粤东省城图》,成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图说城市文脉》,第26页。
[32]《五羊近事》,《申报》1885年9月19日。
[33]《广东省天主教史料选辑第一辑》,第6页,现藏广州圣心大教堂。
[34]《广州省城图》可见,布政司署东侧为丕崇书院。《图说城市文脉》,第30页。据《广东省天主教史料选辑第一辑》记载:“后来法国领事馆迁往沙面,因而丕崇书院也迁至过去成为约瑟路(即今旧部前现市三中的校址),兴建一间颇具规模的学校,命名圣心书院。”
[35]《广州市志》卷十,第796页。
[36]有关租借原两广总督署与石室教堂的兴建,可参阅陈静、郭丽娜《广州第一任主教与石室教堂的兴建》,《暨南学报》2007年第6期。
[37]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3日,中英签署《沙面租约协定》,但沙面的建设工程从1859年已开始。及后英法达成协议,由法人承担沙面五分之一的填筑费用,而英人划出沙面的五分之一独体供法人开辟专管租界。
[38]见上海《申报》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9月19日。
[39]王尔敏:《弱国的外交》。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第59页,2008。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3。
[41]《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訢等奏法租广东藩署事悉心商酌姑允暂租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461页。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