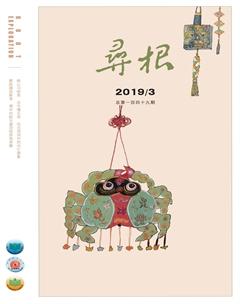被误读的《左传》人物表敬称谓
原德志
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争霸而加强中央集权,原、温并入晋国后,被改为原县和温县。然许多人仍把其县大夫视同世袭领主,将其辖区视为采邑,致使历代学者及姓氏专著把《左传》上原轸、原同、原、温季等县大夫的表敬称谓,误认为真实姓氏,进而臆测。其后人因以为氏,无端给原、温等姓妄加源头。近读山西大学田同旭教授所写《前后原国与两个沁水》,感佩之余,又深憾其重蹈《元和姓纂》等专著之覆辙,误将先轸、赵衰加入原氏先祖之列。本文探讨《左传》人物之表敬简称现象,明晰原、温两县之县大夫和原、温两姓渊源毫无瓜葛。
复杂称谓被简化是古今常见现象
《左传》中确实有将先轸称为原轸、赵同称为原同、至称为温季等例子。但笔者认为:原轸两字,只是其复指性称谓压缩后的表敬简称。前边那个“原”字,是指代“原县大夫”这一职位敬称的。
原轸为原县大夫先轸之简略,原同为原县大夫赵同之简称,温季为温县大夫季之简称,原为原县大夫先之简称。
上述县大夫及其后裔,均未姓原或姓温。但自《元和姓纂》以后,历代专著辗转相抄,皆忽略了晋国的县制并非采邑,错把《左传》人物称谓中复指词组紧缩后的表敬简称,当成了真名实姓,并臆测其子孙亦皆因以为氏。
简称现象古今常见,古人受书写条件的限制,尤其惜墨如金。原轸、原同、原、温季等称谓的组合方式,均属于春秋时盛行的“职务+名字”之类型。“原”“温”等字只代表其职务,后边的“轸”“同”“”“季”,实为其真名先轸、赵同、先、季的简化。
《左传》中由“职务或身份+人名”来组合人物称谓的例子比比皆是。单名前冠以职务的如司马燮、祝佗、师旷等;由“身份+人名”組合的有王子带、王子颓等。
这些由“职务或身份+人名”的人物称谓,在古籍中经常被简略掉其中一些字。例如王子带,便是“周惠王子姬带”的简称。王子带不姓王,这和原轸、原、原同并不姓原,温季并不姓温,属于同一道理。
《左传》人物称谓中的简略是常见现象。“践土之盟”中,晋文公被称作“晋重”,即把“晋重耳”的“耳”字省略了。
更为简略的例子,如“原屏咎之徒也”和“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两例中“原屏”两字相连,但他却又绝非原姓或屏姓中人。前一例的意思是:早在晋楚之战前,晋人荀首就预言:原县大夫赵同和屏县大夫赵括留在军中,那是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啊!后一例的大意是:赵氏蒙难后的幸存者赵武,因为当初原县大夫赵同和屏县大夫赵括被诬谋叛,导致赵家被灭族而怨恨栾氏。这两例中,原县大夫赵同和屏县大夫赵括,被简略成了“原屏”。这两例对本文至关重要的是:“原屏”两字,即只用赵同和赵括两人的表敬简称,来指代赵同和赵括,这和原轸的“原”字,作为对先轸任“原县大夫”之职位的敬称,是同一道理。
按说,虽然赵同、赵括和先玩忽职守,导致晋国在晋楚之战中惨败,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真,但并非存心通敌。只是因为赵家独揽大权,长期积怨众怒,所以当有人借机给赵家罗织谋叛罪名时,栾氏亦表示认同。这便是“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的原因。又因赵同、赵括是赵武爷爷辈的人,赵武理应避讳其名,因而才使用了“原屏”这样的表敬简称。
可见,或为行文的简洁明快,或因特定的礼俗,把复杂人物称谓加以简化,这在古代和今天都是常见现象。《左传》中用“原县大夫先轸和原县大夫赵同”中的“原”字代表“原县大夫”,和“原屏”指代其县大夫,本属同一道理。
历代姓氏专著多属辗转照抄
唐宋以后,许多姓氏专著辗转相抄,把晋县写成采邑,还让其县大夫后人因以为氏。因原、温两县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具有可比性,故本文将其放到一起来讨论。
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是一本贡献很大、知名度很高的书,但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一旦出现失误,其负面影响也就极其深远。宋元明清之姓氏专著以及今人著作仍在以讹传讹,致使许多人真伪莫辨,无所适从。
在许多专著中,诸如“封于先轸,号原轸,其后亦为原姓”“至为温大夫,号温季,因以为氏”“至食采于温,亦号温季,因以为族”之类,均将人物称谓中的表敬简称当成了具体姓氏。这不仅是历史认知上的疏失,从语法角度来说,同时也是对《左传》中表敬称谓的误读。(见姓氏文献中以讹传讹举例表)
春秋中后期的晋县并非采邑
上述姓氏专著中的诸多失误,多因错误理解晋县的性质而起。首先,春秋时人对郡县制这一新生事物就很难扭过弯儿来。纵向看,分封世袭已延续了上千年;横向看,春秋各国的世袭采邑,广泛存在。封建时代,有谁一旦受封,封邑的地名,便和受封者联系到了一起。比如《左传》中,先轸的儿子先且居担任中军主将后曾食采于霍,于是人们便称先且居为霍伯。春秋时代诸如此类的×伯、×叔不胜枚举。按说,县大夫是行政长官,并非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但《左传》中也显示,赵同当了原县大夫后,便有人称赵同为“原叔”了。这说明,县制实行初期,旧的意识和习惯仍然普遍存在,人们仍习惯于用老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
造成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更和某些县大夫的个人品质有关。像赵衰、先轸、狐溱这些开创晋国霸业的功臣,做事认真,行为检点,担任县大夫时,个个奉公守法。但正如古人所说“常胜之难保”,往往传至后代,便每况愈下。先轸的后人先,被任命为原大夫兼“下军左”时,在晋楚之战前夕,楚人便早已料到:“晋之从政者(指阳处父)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晋师必败。”再看温县的县大夫至。他几乎把温县当成了自家私产,竟然狂妄到敢和周天子争起田来。所以,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县制虽名为行政单位,似乎也和分封私邑没有两样。但《左传》又明文记载,自晋文公建温县后,第一任大夫是狐溱,第二任大夫是阳处父,第三任才是至,可见,县大夫由国君委任,已成定局。所以,无论至这个县大夫怎么霸道,他也不敢再动恢复世袭制度的念头。仍以至和天子争田为例,只用晋君一句不要再争了,至便立即收敛。这说明晋国各郡县疆界的变更与否,是由国君决定的。
世袭食邑等于给子孙开创了万代祖产。这样,其子孙才会“因以为氏”以示纪念。因而,弄明白原、温两县的性质,是判断其子孙值不值得“改变姓氏”的关键。
1997年,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发表了《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一文。该文指出:“晋、楚的灭国为县,以及在新领土上所设的县,虽然还不是后世的郡县,但已开始具有地方行政组织的萌芽,即作为国君的直属地,并且县的长官不实行世袭制。”反对此说的杨宽,曾举赵同世袭赵衰的原县大夫职位为例,但周振鹤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赵同并不继赵衰任原大夫”。史载:僖公二十五年赵衰为原大夫,但到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时,先轸就被称为原轸了。先轸死后由谁继任了原县大夫呢?孔颖达引汉代服虔的说法,是将原县一分为二,由先和赵同来分任的。这说明县大夫的任免及辖区的变化,是由国君随时酌情确定的。
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的《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一文,以原、温两县为例,从主官由国家任命,子孙不得世袭,军赋、田赋由国家支配,国家有裁决诉讼最后决策权等方面,说明晋国的县制,虽不能算完善,但“无改于晋县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的政区性质”。也就是说,那些跋扈不法的县大夫,无论他多贪多黑,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并且最后也都没有逃脱国家的制裁。
除了原、温两县,《左传》中还有许多事例,可以支持周振鹤和杜勇的观点。比如,《左传·昭公三年》载:“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杜注:州本属温,温赵氏邑)二宣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杜注:称,晋大夫,始受州。自是,州与温别,至今传三家)晋之别县不唯州,誰获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
综合《左传》文与杜预注可知:其一,州县从温县划分出来后,其县大夫从称到栾豹,已经传了三家。足以证明,当时晋国的县大夫不是世袭的。其二,晋国将大县一分为二的不止州县一例。从未见哪个大县的大夫,敢将被划出去的别县,擅自收回自己管辖范围的。说明县域的大小分合以及县大夫的任命,是由国君主持的。故,这些晋县无疑是属于行政性质的。
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载:“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针对此文,孔颖达正义说:“守邑之长。公邑称大夫,私邑则称宰。此言问其县大夫,问绛县之大夫也。绛非赵武私邑而云则其属者,盖诸是公邑,国卿分掌之而此邑属赵武也。”综合以上可知:其一,在晋国,凡称县大夫的都是公邑。如果原县、温县、绛县果为世袭封邑,那么其主人便只能叫原宰、温宰、绛宰,而不应叫作“原大夫、温大夫”了。其二,慰劳“舆人之城杞者”,这些工役是远到外地去修筑杞城的,足证这是国家行为,绛县的军赋、工役是受国家支配的。其三,赵武了解这个老人后,直接“以役孤老故”将征派他筑城的“舆尉”免职,并任命该老者“为绛县师”。这也正因为绛县是行政县,并非国中之国,作为国卿的赵武,才有权对下属县吏随时任免。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国君委派魏戊等10人分任各县大夫。“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从县域之划定,县大夫之委派,大案要案需上报,再参照上文孔颖达“公邑称大夫,私邑则称宰”来看,在晋国,至少到春秋中后期,县大夫属于行政官性质是没有疑问的。
前述氏、赵氏先后任温县大夫时,氏欲争田被晋君挫败,赵文子欲争州县,又被同僚挫败,诸如此类,无不证明:世袭分封制度,正在无可奈何地让位于郡县制度的事实。
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史家对春秋后期县制的性质认识模糊,影响了《元和姓纂》等编撰者,以致许多人只根据至亦号温季、先轸亦号原轸、赵同亦号原同,便以为氏改姓了温,先轸和赵同改姓了原。影响所及,以讹传讹,居然迷惑人们上千年。
原、温之县大夫均未因以为氏
古代礼仪文化避讳直呼其名,反之则表示鄙视。春秋笔法更讲究微言大义。在孔子笔下,凡写某国有杀其大夫之事,在“杀其大夫”四字前后,如何用字,大有讲究。比如:宋杀其大夫和宋人杀其大夫,前者表示国杀或国讨,后者则表示被人陷害或误杀;在“杀其大夫”四字后,不直书被杀者名字,即表示该大夫是无罪被杀;反之,被直书其名,则表示被杀者是罪有应得。
恰巧,与本文相关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因遭国讨而灭族的。先轸的后代先、赵衰的儿子赵同、晋国三家族的至,他们生前被抬举为原、原同或温季等表敬称谓,一旦恶贯满盈而遭到国讨时,《春秋》在“杀其大夫”四字之后,都无一例外地以直书其名来表示鄙视。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国人把《春秋》尊为《春秋经》,是因为如果《春秋经》上弃用敬称而直书罪犯名字,即意味着是对乱臣贼子验明正身而被杀的历史宣判。——验明正身,当然要用真名实姓。故曰,以孔子之《春秋经》为证,原、温之县大夫与原、温两姓毫无瓜葛。例证来自《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经]宣公十三年……冬,晋杀其大夫先。书名以讨罪。[传]冬,晋人讨之败,归罪于先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之谓乎?晋灭其族,为诛已甚,故曰恶之来也。[疏]注尽灭至来也。正义曰:先之罪,不合灭族。尽灭其族,为诛已甚,亦是晋刑大过,是为大恶。君子既嫌晋刑大过,又尤先自招,故曰恶之来也,己自取之。恶之来也,言大恶之事来先之家。
此时,在孔子和孔颖达笔下,被灭族之罪犯均被直书先,而不再用原这样的表敬称谓了。
[经]成公八年,夏……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传》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义自居,宜其见讨。故从告辞而称名。正义曰:大夫无罪见杀,例不书名。……今虽实不作乱,从告而称其名。言从告者,凡杀大夫,必以其实有罪……鲁史详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书或从或否耳。
此时孔子直书罪臣名字为赵同、赵括。孔颖达进一步强调,大夫无罪被杀,例不书名。凡书名者,必因其实有罪。而为何杜预的引文却仍用“原、屏”这样的敬称呢?因为“原、屏,咎之徒也”一句是15年前荀首评价他两个的预言。那时两人尚在原县和屏县大夫任上,故荀首仍用了“原、屏”这样的表敬称谓。可见原同之原,只是用来代表原大夫这个敬稱的。赵同才是其真实姓名。
[经]成公十有七年……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传]……闰月乙卯,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导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郤氏失民,胥童导乱,宜其为国戮。正义曰:厉公以私欲杀三郤……胥童为栾书、中行偃所杀,乃直是两下相杀,今《经》书二者并为国讨之文,故《传》解之:言民不与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导君为乱,胥童有罪也……故《传》正其二者之罪,解其并为国讨之意。
综合《左传》、杜预注、孔颖达疏,三者解释的重点在于:胥童虽是被仇人所杀,而晋厉公是因受胥童的误导,才下令将氏灭族的。按说胥童因私仇而被杀,不应算作国讨,为何仍以国讨的笔法来写这件事呢?原因是,“胥童导君为乱”,企图独霸朝纲,因而孔子认为他死有余辜。而三家族因久积民愤,即所谓“民不与氏”,故他们的被杀都不能算冤案。
综合以上三例,《春秋》以国讨灭族罪名,将先、赵同、至载入史册,他们的姓氏岂能有假?他们在犯事之前,虽曾被尊为原、原同和温季,但前边那个原和温,只是用来代表他们的官衔。故原、温之县大夫,和原、温两姓源头,毫无瓜葛。
以先氏与赵氏家史为证
先、赵同、至三家被灭族,故绝不存在赵同、至之“后人因以为氏”的问题。
唯独先的幼子先侗,被门客带至他乡而幸存。又因徐俊元等的《贵姓何来》有所谓“原伯后裔先轸”之说,似乎先轸原本就是原伯后裔,故对先氏一族的来龙去脉,仍有澄清之必要。
据四川泸州《先氏联宗族谱》记载:先氏最早源于刘氏。后来因周成王封刘累之后裔于杜,称为杜伯,其后改称杜氏。后因第七代杜伯获罪,杜伯桓之子隰叔逃命至晋国,在晋国为官受封先地,子孙始以先为氏。先姓在《左传》中最早出现的有先丹木、先友。
据《先氏联宗族谱》梳理出的先轸家族:刘氏-杜氏—隰叔—先丹木、先友。先丹木生先轸,先轸生先且居,先且居生先克,先克之子即先。先氏蒙难灭族时,先门客带其幼子先侗远逃四川泸州。今据2014年统计,四川约占先姓总人口的56%,并多集中于泸州。
先氏的来龙去脉如此清楚。除了先轸、先,因分别担任过几年原县大夫被偶尔敬称为原轸、原外,能够在《左传》中查到的有:先友、先丹木、先蔑、先都、先茅、先辛、先仆,包括先轸的第二代先且居,第三代先克,全未与原姓沾边。那么,“其后亦为原氏”,又从何说起呢?
特别是赵同和至,皆因灭族而绝后,但至今许多人却仍根据其生前曾任职于原或温,继续以讹传讹,妄称赵之后人以原为氏,之后人以温为氏。
厘清春秋县制之性质,从历史角度讲关系着中国郡县制度起源问题;从语法角度讲关系着对《左传》中表敬称谓的认知问题;从姓氏渊源角度说,又关系着千家万姓的寻根问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