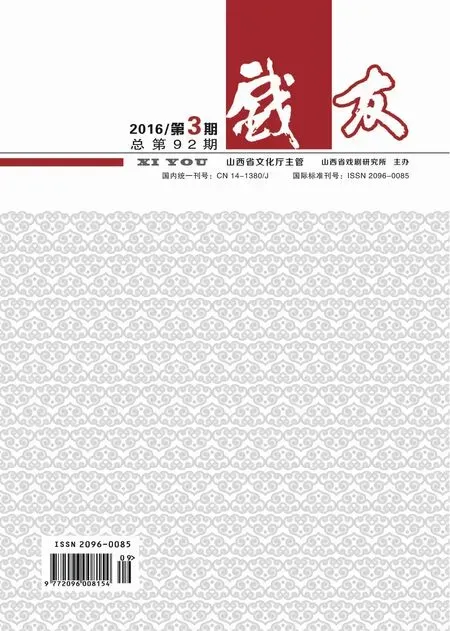秦腔剧作家杨 起和改编本《下河东》
仝朝晖
提起秦腔《下河东》,相信许多西北人不会陌生。特别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三十六哭”唱段,因为其唱词形式和演唱风格的典型性,对于今天秦腔观众来说,《下河东》具有不可代替的精神象征意义。
传统秦腔《下河东》剧目存本,主要有《甘肃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一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二十七集》中收录的《下河东》等,这两个版本都是老艺人的口述本。
甘肃版的曹洪有口述本“后河东”(也即“下河东”)分为十八场。基本剧情:欧阳芳奉旨发兵河东,因与先行官呼延寿廷有仇,假借庆功,将其灌醉,暗约白龙劫营。白龙被呼延寿廷杀败,欧阳芳反向赵匡胤诬陷先行谋反,当面杀死呼延寿廷。呼延金定为兄报仇,被赵匡胤误杀。呼延寿廷托梦妻子,让从岳父处借兵,其子呼延赞得到赵公明点化,治好哑病,传授武艺,呼延赞为父报仇,大破白龙,后见赵匡胤为真龙附体,遂归顺,同奔佘塘关擒获欧阳芳,收杨家将。陕西版“下河东”(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情节与甘肃版大同小异,共十五场。赵匡胤兵下河东,呼延寿廷被欧阳芳诬陷造反而遇害,其妹报仇在阵前被赵匡胤误杀。呼延寿廷阴魂回家托梦,欧阳芳差人到呼延府中抄家,呼延秀英逃出,得骊山老母传艺,呼延赞母子投井,被呼延寿廷神魂相救,为其子去除哑虫,遣黑虎星附呼延赞之体。呼延一家在罗家山借来兵马,河东破白龙,见赵匡胤为真龙附体,遂归顺,同奔佘塘关擒获欧阳芳,收杨家将。
以上陕西版剧本中出现了人们熟知的“三十六哭”唱段,在甘肃版没有这段戏。
现在西北地区秦腔舞台上的《下河东》,大都是源自杨起改编本。关于杨起改编本《下河东》,据《陕西省戏剧志》等文献介绍:《下河东》原来是耀县剧团的老剧目,是四本连台本戏(《火塘寨》《下河东》《呼延赞出世》《龙虎斗》——笔者注)。杨起将四本连台改编成为一本,演出在关中渭北一带风靡。1956年,新风剧社首次赴西安,在五一剧院演出改编本《下河东》,连演数十场,剧团也被誉为“下河东剧团”。为此《西安戏剧》(创刊于1954年)接连发表数篇评论文章。该剧主演陈仁义一举成名,蜚声剧坛,陕西省广播电台还录制了陈仁义演唱的“困营”“赶驾”选段。①
这两段录音就是陕西音像出版社发行的“百名秦腔演员唱腔集”专辑中,陈仁义的“王不该当年离龙巢”唱段,以及现存在陕西省电台的“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唱段。特别是后一段录音,时长30分钟,包括“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猛想起当年投山东”“四十八哭”三部分,是陈仁义33岁留下的唱段录音,堪称精品。但是,1958年出版的杨起改编本《下河东》剧本(东风文艺出版社),就有人们熟知的“哭先行哭得王如醉倒”“王不该当年离龙巢”“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这些唱段,其中却没有“三十六哭”。原因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批判文艺的形式主义,所以书中删除了“三十六哭”,同样命运如山西晋剧界批斗阎逢春,不许他在演出中表演帽翅。
1980年,宜君县剧团高信民以杨起改编本的《下河东》,再次走红西安。1981年,耀县剧团带着《下河东》《三娘教子》两部戏赴西安连演数十场。陕西省电视台录制了陈仁义联袂演出(陈在文革被错判入狱,后落实政策,调至泾阳县剧团工作)的《下河东》全剧录像,长期播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该剧改编者杨起(1923~1971年),字春茂,陕西户县人。幼年就读私塾,后于周至武成中学读书。民国36年(1947)由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毕业,在西安市东羊市小学任教,1949年5月,在咸阳专区文工团任戏剧编辑。1953年,他随耀县宣传部工作组进驻剧团,杨起任新风剧社(耀县剧团前身)团长,1958年6月同时兼任三原六县市协作区戏曲学校校长。作为剧作家,杨起创作或改编过多部戏曲剧目,最著名的就是《下河东》。另外他在剧团任职期间,对后来的秦腔名家陈仁义有知遇之恩。
所谓“三十六哭”也就是剧中赵匡胤“哭先行”的唱段,可以说《下河东》因“三十六哭”而成为经典。在甘陕这段戏一般有两种唱法即“三十六哭”“四十八哭”,陈仁义唱“四十八哭”。
再者,传统戏曲唱词中出现的“三十六”“四十八”“七十二”之类句数,并不是以前被指责的“形式主义”。这些都是所谓“吉数”,具有美好的文化寓意,这和民族审美习惯中的数术信仰有关系。简单来说,象征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吉数”也就是对数字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和神奇色彩。“三十六”之数如何而来?《易经》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三十六数之说,故历代数术家、修炼家将其称为“天罡”之数,乃正气之数。与此类似,而“七十二”其以数说,乃为“地煞”之数。同样,关于“四十八”,《易经》数理认为,乾数二十七是最大的数,无论和震、坎、艮哪一数(二十一)相加,都得到四十八。故此“四十八”亦为吉数,喻示美化丰实之意。这种吉数在传统文化信仰和民俗习惯中屡见不鲜,如梁山“一百单八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泰山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孔子七十二弟子,戏曲界关公舞台亮相工架的“四十八图”等。“三十六”“四十八”“七十二”这种大段排句的唱法最先源于高腔,在明清时期不同戏曲剧种相互融合,乱弹剧目也吸收了高腔的滚唱方式。

秦腔《下河东》(陇县人民剧团演出,黄池河拍摄)
1958年出版杨起改编的《下河东》单行本,共十八场次:登殿、别家、誓师、姑侄助阵、白龙点兵、交锋、屈斩、惊闻凶讯、巡营、传讯、质询、练武、白龙三反、东征、困营、骂贼、赶驾、锄奸。改编本剧情有两处明显改动:其一,去除“封建迷信”内容,删去赵公明传艺,给呼延赞驱除哑虫,让他瞬间从孩童长大成人的情节;其二,去除宿命论思想,原剧本的呼延赞鞭打赵匡胤,发现赵为真龙之体,遂即降服,改为呼延赞兄妹被赵匡胤部将晓之以国家危难、黎民水火的道理,遂被说服。而这样一来,改编后的剧本有个情节漏洞:呼延赞怎么从哑巴孩子,很快变为勇猛超群的成人?所以改编本就安排了赵匡胤被困河东15年,其间呼延赞在罗家山学艺功成。
那么,最初杨起改编此剧时,这一细节的处理是否还借鉴了汉调二黄内容?这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杨起改编《下河东》于1955年前后,有一说其蓝本参照了其弟杨春启(曾任户县木偶剧团团长)的《下河东》唱本。这一时期,长安县的木偶戏班“鸿禧社”(人称“八个娃”戏班)主唱袁克勤在关中享有盛誉,他擅演的秦腔《下河东》《斩李广》《斩黄袍》等戏都来自汉调二黄剧目,而户县境内也有专门的汉调二黄戏班。现存的汉调二黄剧目《下河东》其中就有唱词:“下河东整七载,把孤王的龙须白了”,同样在湘剧、绍剧的《下河东》中也有类似情节。
这里有人也许疑问:一国之君可否会离开国都,一别经年在边关苦守呢?似乎不合“历史”常理。但是,传统秦腔剧目若从故事取材方式论,可以说大多是“传奇剧”,而不是今天所谓的“历史剧”。什么是传奇?这就是明清小说所谓“稗家小史,非奇不传”,所以明清时代人们就把戏曲剧本称为“传奇”。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更是指出戏曲的“非奇不传论”:“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②
传奇剧的显著特点就是强调因果、善恶、人性和解的情节内容,代表了最贴近人心的平民立场,这些我们从秦腔传统戏《三娘教子》《五典坡》等剧目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因此,传奇戏曲的精神内涵和当代的历史剧所表达的唯物论史观,以及其代表阶级立场的功利主义倾向,具有根本的不同。
笔者有时想,杨起《下河东》的情节漏洞完全可以避免。如果改编为父亲出征时,呼延赞外出学艺,等到赵匡胤河东被困,呼延赞闻讯再带兵解围,这样内容不就滴水不漏了?其实这种思路在晋剧《下河东》③的改编中就有体现,秦腔演员陈俊义的《下河东》即是移植了晋剧此本。
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杨起先生可能是为了保留原剧中“哑巴说话”的传奇剧情,退而求其次,改编中加入赵匡胤被困河东15年。当然他在处理这个细节时,也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剧中只有小白龙上场唱了一句“在河东围困15年”,这算是不露声色地藏拙。
但是,如果把这种编剧手法的“虚笔”变成“实写”,那就不甚高明了。陈仁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回到泾阳县剧团工作,当地编剧对杨起版《下河东》做了部分改动,增加了“灵堂”一折戏,把“四十八哭”移到这里唱,而去掉了“困营”一折。所以剧中就多了“珠泪点点洒战袍”,而没有了原来的“王不该当年离龙巢”唱段。在新版“灵堂”一折,反复渲染“十五年度日如年”之类唱词,则显得不妥。甚至于还有一些剧团在下半部戏的小白龙上场时,人物由小生换做须生扮相。这些就是谬解了编剧意图,放大了不该强调的情节过场。
整体来看,杨起改编本《下河东》的戏曲结构更为完整和精炼。可以说该剧能够在舞台常演不衰,杨起的改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下河东》一剧的保留和发扬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说一说,陈仁义原本是业余演员出身,年轻时曾经在泾阳县茶叶工会剧团演出,他再辗转到耀县剧团,因为演出《下河东》成为名冠西北的名角,所以得到雅号“茶叶红”。感恩老师的栽培,后来他每逢到户县一带演出,都要登门拜访看望杨起的家人,这件事传为佳话。杨起先生虽然英年早逝,但后嗣人才济济,其长子就是以画“钟馗”闻名的画家杨旭。
注释:
①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版,第148页。《陕西省戏剧志·铜川市卷》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② (清)李渔《闲情偶寄》,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
③《山西地方戏曲选 第1集》山西省文化局曲剧工作研究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