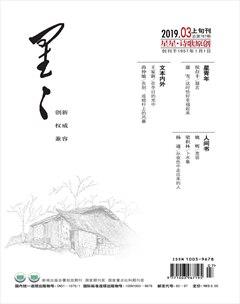从一次旅行开始(随笔)
王家新
去年初秋,有一次让我深感愉悦的行旅。当我乘坐的高铁穿过晨雾迷蒙的华北平原,我读着米沃什的《冻结时期的诗篇》(林洪亮译,上海译文)。这样一位诗人对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睿智洞察、对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和自身存在的确认,都再次使我振奋。他在晚年为其诗集所写的前记也说出了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坚信诗人是被动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的守护神赐予的礼物,或者按你们喜欢的说法,是他的缪斯馈赠的。他应该谦卑恭谨,不要把馈赠当作自己的成就。同时,他的头脑和意志又必须警醒敏锐。……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二者若必择其一,我选择客观的艺术,即便它的意义并非由理论阐释,而是通过个人努力来领会的。
看上去并不新鲜(至少歌德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但对米沃什来说,这却是他通过个人漫长而迂回的道路所达到的真理。重要的是,他重获了某种出自他全部生命的虔敬。而没有这种面对诗歌的虔敬,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是的,馈赠,冰与火的馈赠,尘世与天国的馈赠。这不单单是出自机缘,如果不是一个诗人自身的命运把他推向了这一刻,他也不可能“参与到一部作品的诞生”。
去年末,在南京,一场盛大的跨年诗会结束后的寂寥,我有一种解脱之感,但也不无沉痛,处在新年之始,我甚至感到“在我的耳廓上刮着的/已是万年前的冰风”(《新年第一首》)。正好诗会后有闲,我请诗友带我去高淳探望一位独自生活在湖边的诗人朋友(见《石臼湖边的树——给叶辉》)。冬天的湖岸一派荒凉,“唯见一棵赤裸的歪脖树/细枝峥嵘,屹立于/灰色的风中”,我一去,就被这棵乌桕树吸引住了。我甚至感到它是为我而出现的!回到北京二三周后,当我再次想到那棵树,一首诗也就那样产生了。
可以说这首诗是一个礼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其实我和那位诗人朋友联系并不多,但我们一见面就有一种默契,那是一种各自深知诗人命运而又“惺惺相惜”的默契。所以,这首诗是写与一棵树的“相遇”,但它却由此抵及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更本质层面,否则,它不过是一篇浮光掠影之作。
而在去年9月,在天水,我还写有《访东柯谷杜甫流寓地》一诗,那更是对一种共同命运的认领,其间是一种沉痛感和荒谬感的混合与交织。如同有人所说,那也是我们毕生要呈现的“悲欣交集的功课”。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写作必得深入到我们内心中那些最难言的体验中,而诗歌之为诗歌,总要道出只有它才能言说的东西。
海德格爾有一套关于“语言是说话者”的哲思。据说当年策兰也曾受过影响。但是,他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的。他必然会坚持从自己的根基出发:“真实,这永远不会是语言自身运作达成的,这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其轮廓和走向。”可以说,这也正是一位诗人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必要补充或修正。
真实不会只由语言自身的运作达成,而“礼物”也不是无缘无故被赠予的。米沃什提到了“缪斯馈赠”,阿赫玛托娃的诗中也常写到“缪斯”。真的有这样一种神秘的存在吗?有。像米沃什、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他们的卓越,就在于以他们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肯定了这样的存在。它并不神秘,虽然它也体现了如德里达所说的“语言的幽灵性质”。它无非是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中、在他们全力投入的写作中响起的一个声音,而诗人听从了她的“口授”。
他们发出的,都是非凡的、真实可靠的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是诗的接受者,参与者,而绝不可以“创造者”(曼德尔施塔姆从来不使用这样的概念)自居。他们要做的,就是为之工作和献身,就是时时准备好自己。让我们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