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王献唐碑帖题跋精萃考释
张祖伟
(山东博物馆,山东济南 250014)
王献唐(1896-1960),山东日照人,精目录版本、金石考古等,一生勤于著述,被誉为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历任山东省图书馆(以下简称省图)馆长兼理金石保存所、山东古文管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我馆)筹备处副主任等。主持省图期间,锐意搜集乡邦文献,广罗金石古物,海源阁、陈介祺、许翰、李佐贤、吴式芬、上陶室等故物如江河入海,使省图成为北方图书文物重镇。其最让人钦佩的壮举,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济南沦陷前夕,在韩复榘政府弃之如敝履的困境下,将文物典籍精华转移大后方,并在断薪绝酬的艰辛情况下,客居守护10年,为山东守住一缕文脉。建国后,此批南迁典籍文物及南迁初期限于条件而寄存于孔府的另一批典籍文物安全返济,成为我馆重要珍藏。
先生著述在学者的整理下,已多有出版,如齐鲁书社《王献唐遗书三十种》《山东文献集成》收录43种等。题跋类中的书跋也有《双行精舍书跋集存》两编出版,而碑帖题跋尚未结集出版,成为王献唐研究中的一大遗憾。由于历史渊源关系,我馆是先生校勘手跋碑帖及金石拓本册的重要收藏单位,本文即辑考部分未公开题跋而成。
1 跋清乾嘉间拓三国魏庐江太守范式碑
(1)题签:魏范式碑,双行精舍藏旧拓本。(钤“王”)
(2)此本拓工墨色浓厚古穆,与他拓独异,乃直隶一王姓者所为,数十年前来鲁遍拓济宁曲阜诸碑,价亦持昂。余藏有鲁俊碑拓,墨与此相同,盖出一手也。缺碑阴,俟觅旧本补之。庚申三月灯下王献唐记。(钤“凤生”“王献唐”)
(3)顷敬古斋主人王君来谓此为王鹤群手拓,山西人也。墨中和以鸡卵汁液,过数十年即如此。昨日又获武荣碑亦为王君同时所拓,近时无此艺矣。二十年三月四日校书赘笔,顾黄书寮主人。
(4)迩日体气益弱,思为消遣之计,间取旧碑校之。兴至捉笔又不能自已,既校郑固碑,又取此拓以黄氏小蓬莱阁勾本并景印原本及新拓本对勘。座客来去,时作时辍,略于两日毕事。原石残泐处,黄本与新拓本每模糊难辨者,以此墨寻求点画,多约略可见,亦不详记也。二十年三月九日王献唐校识。(钤“琯”)
范式碑,青龙三年(235)立,宋时残断亡佚,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崔儒聃于济宁龙门坊得残额,方重见天日。十一年后,李东琪又于济宁学宫戟门下获上半截残石。二石现存济宁博物馆。碑主范式,《后汉书·独行传》有载,其墓也于1963年在山东嘉祥发现。
是碑入土前的拓本极罕见,传世者仅北京故宫藏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易于泰安赵相国处访得宋拓本,额完好,碑文存370余字。重出土时,第2行“有士会者”会字捺尚未与石花相连,道光间则已经相连。此拓未连损,乾嘉间拓本。尾钤“姚氏伯印”,为姚元之旧物。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等,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善书工画。扉页又有吴诵清题旧签“魏范巨卿碑旧拓”及29字短跋,述碑之现状及范式传记。吴诵清(1846-1910),字梓林、芷舲、毓庭等,江苏镇江人,官安徽布政使司经历,善篆刻工书擅画,有印谱《似鸿轩印稿》传世。
是拓墨色浓厚古穆,远胜常见之物,且装帧讲究,外加镶边木护板,每页又嵌褐色助条。先生先后手书三跋,1920年首跋赞其墨色,并推测拓手系天津王氏。十一年后,得敬古斋王仁敬见闻,知拓本墨色独特的原因及拓手的正确姓名与籍贯。只是以此拓推论,拓手当是百年前人物。先生所言武荣碑拓亦在馆藏,墨色及装帧方式一如范式碑拓,当拓裱同工。敬古斋王氏,字笙甫,在济经营古籍碑帖店,曾以收得海源阁散出旧物闻名。先生苦心经营公藏时,常从其处充实馆藏,交往日密,感情日笃。不仅为其店铺书匾,先生护送文物南迁时,还将四箱个人藏品代存。其亡故时,先生作诗悼念。“论古王翁故绝伦,手装毡墨尚如新。钟鸣落叶重来日,问到黄炉剩几人。”同年3月,先生又取黄易藏宋拓景印本、小蓬莱阁勾本及新拓本与此拓校勘,并于是拓作详细校勘记39条。如“江字未笔左端,新拓于水旁末画泐连,此与小蓬莱阁勾本同,景本亦连泐。”“命族下字,《隶释》缺,验此拓本似实字,下有为范氏三字,原文或为实为范氏也。黄氏勾本只具外匡,中间笔画全缺,拓本亦泐作一片,此与景本略同,不知前人已有释实字或他字者,不及遍检矣。越日检阅《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黄氏已疑为实字,昨日校此竟交臂失之。”
2 跋清山东金石保存所精拓北魏李璧墓志
李志出土在景州时,拓本用擦墨;在德州时,拓本用蝉翼,均极劣。迨入金石保存所,始有精拓本。此即初入所,姚柳屏监拓精本也。吾友陈雪南后长图书馆,重拓百份,已不如前,此后从未再拓。现在图书馆所出售者,均雪南旧拓之余也。今春三月无意中获得此本,与旧藏张猛龙碑重装并存,使尺幅划一,其字体亦正相近也。碑下罗氏一跋均出柳屏手笔,凡图书馆之题识及金石跋尾其署罗君衔名者类,为柳屏庖代。此碑又有覆本四石,一在济南,一在曲阜,一在德州,一在北平。四本中以北平本最精,锋铓削立几欲乱真。其次为曲阜本,再次为济南本,至德州本虽最劣。然收藏家得之,每误为初出土之未剔者,亦不可不知也。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灯下扶病书。献唐。(钤“王献唐”)
李璧墓志,正光元年(520)刻,石材系打磨旧碑阴面而成。书法雄强挺拔,刀锋犀利可见,在北朝碑志中风格独特。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北景县出土,后被移置德州。宣统元年(1909)山东学政使兼金石保存提调罗正钧购为公藏并刻铭,“宣统元年,津浦铁路修至德州北境,获此石,从土人以银币三百购置金石保存所”。其记述出土地点及时间有误。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济南,公藏有所散佚。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石保存所登报寻找,幸运寻回此石。建国后,经山东古管会调拨我馆。
据跋,1930年3月先生得是拓,断定为初入馆精拓本。3个月后跋其端,述李璧墓志及拓本不广为人知的掌故。如该墓志先后被济南、曲阜、德州、北平四地翻刻,其中北平最精,几可乱真,次为曲阜本,再次为济南本,德州本虽最劣,但常有收藏家误为初出土未剔拓本。又如众所周知的罗正钧题记实际由其幕僚姚鹏图代笔,甚至山东省图书馆内凡署名罗氏的题识及金石跋尾都是如此。再如是碑有景州擦拓、德州蝉翼拓、金石保存所精拓三种早期拓本,前两者远逊后者。先生又补充,金石保存拓本实分两批,一是姚氏监制初拓本,最精美。一是稍晚的陈名豫监制拓本,则逊之。姚鹏图,字柳屏等,号古凤,江苏太仓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知山东邹县等,宣统间为罗正均幕僚,协助筹建省图及金石保存所,《山东创建图书馆记》即由其书丹上石。喜金石,碑版收藏之富,考鉴之精,济垣士林,无出其右。身殁后,藏品多归省图。陈名豫(1883-1966),字雪南,山东滕县人。同盟会会员,历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工商局长等。喜金石,擅书法,关心文化事业,与先生相交。
3 跋明末涿州拓《快雪堂帖》本《闲邪公家传》
(1)题签:闲邪公家传。赵松雪书快雪堂刻精拓本,百汉印斋藏。
(2)快雪堂帖小楷以乐毅论、闲邪公家传二种为最。石在涿州冯氏,时所拓者名涿拓,后入内府拓者名内拓。此则涿拓之最旧者也。后有式古堂收藏印记,为卞永誉故物,后归云南萧绍庭。签题即其手笔,首帧白文长印亦萧氏所钤。济南收藏家在民元前后,以绍庭为第一人。既善鉴别,尤富财力,书商帖贾日奔走其门。自绍庭没后,其书画碑刻亦稍稍散出矣。聊邑邓幼云为悔庐先生裔孙,绍庭之姻戚也。家富藏书,旧椠精抄,率为绍庭所得,此帖则绍庭转赠幼云者。近日,幼云后裔又以藏帖出售。余获得数种,此其一也。忆龆龄学书,先公赐以是帖,日日抚之,期使点画方位与原本无二。至今思之,真拘拙可笑。然二十年来之窗下情事,犹憧憧心目间也。因展阅此本,诸笔及之,时十九年中秋节,王献唐书于顾黄书寮。(钤“献唐题记”“顾黄书寮”)
(3)先后见此帖拓本多矣,无如是册之佳者。旧岁潍邑陈氏藏本散出,亦蝉翼初拓,装潢备极华贵,取较此拓,仍觉当隔一间也。

《快雪堂帖》以王书《乐毅论》、赵书《闲邪公家传》、《兰亭十三跋》最知名,尤胜它帖。其中《闲邪公家传》,墨迹上石,原迹收录于《石渠宝笈初编》,流丽潇洒,姿韵俱佳,公认真迹,今下落不明。而快雪堂最早将之入石,故素受重视。是本卷末摹刻“刘雨若模”,出自《快雪堂帖》。原签题,“闲邪公家传。绍庭题赠,幼芸二棣清玩。”又钤“式古堂书画印”“家在滇南翠海阁”等印。系卞永誉、萧应椿、邓幼芸旧物。先生1930年9月11日从山东书局购得,并10月6日中秋佳节作跋,[1]简略考释此拓递藏关系,并追忆童年习是帖往事。卞永誉,字令之,号仙客,官刑部侍郎。精鉴赏,著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康熙六年(1667)所辑《式古堂法书》由刘雨若镌刻,故此帖可能是刘氏刻帖时的赠品,涿拓本无疑。今与故宫藏《快雪堂帖》校勘,此本第5行“力田”之力字横、第12行“大夫”之大字横,已经出现轻微磨勒,故非初拓本。但笔画完好,属精拓。被先生推为民国初期济南第一收藏家萧应椿(1856-1922),字绍庭,云南昆明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长期客居济南,历任山东劝业道、山东大学堂总监等,民国后从商。“其紫藤花馆所藏书画多系宋元名迹,碑帖亦有精品,书籍明刊本颇多。”[2]其姻亲邓幼芸,出身聊城望族。其族因明朝开国有功而受封,子孙世袭指挥,八世任东昌卫指挥。有清一代,又登科举第,文武兼备,累世为官,更因康熙六十年(1721)状元邓钟岳(号悔庐)而至顶峰。
据跋,先生先后得《快雪堂帖》多部,可考者有二,皆从敬古斋购得,俱称初拓本。一本得于1932年12月17日,[3]一本得于1933年1月4日,蝉翼极精,装潢尤美,为簠斋旧藏。[4]与是拓相比,包括簠斋旧藏在内的“初拓本”都逊一筹。盖当时校勘本稀见,而大家都自矜所藏,率称初拓,簠斋也不例外。据先生购得簠斋藏本时间推断,第二次跋题在1934年。
4 跋清嘉道拓陕刻本天冠山诗帖
(1)题签:天冠山诗。赵松雪书旧拓本,凤笙自署。
(2)赵书《天冠山诗》有二,一为此本,其一迄未上石,只见景印本。说者以此本文跋误以天冠山在冉阳郡,证为赝作,并以松雪此书亦非真迹。近二百余年,几成定谳矣。以吾所见,文跋虽误,安知非一时疏漏,兴酣落笔,偶失稽譣。古人时或有之,不能执此便以文跋为伪。即使果伪,昔贤书画之有伪跋者多矣,亦不能以文跋之伪牵及松雪。今观此书神采飞劲,秀骨怩人,其迈往劲拔之韵,在松雪生平行书除多中锋所写苏诗外,尚未见此佳制,非特景印本不及之也。吾人即书论书,书而果佳,虽伪曷害,又况未必即伪也。余年十一二岁即喜松雪书,先公曾为购得一本,拓墨较次,手自剪装之,珍若球琅,十年以还,不复追摹赵书。偶见赵帖精拓,犹喜好之。友人李万青前时赠余一本,较旧藏为优,后又得此册,椎拓尤精,跋语亦清晰可见,以校近拓,则模糊不可辨识,尚是嘉道旧本也。日前友人高云裳假去临摹,余既谢卸图书馆任务,将离此他去,高君因以见还。饭后无事,灯下展玩一过,见时心情犹宛然在目,日月不居,行近中年,书此感慨系之矣。时十九年八月九日雨窗,王献唐。(钤“献唐书画”)
(3)魏公书多肉胜,而此独稜角峭历,人多疑其不类。余独信之,以其与《张留孙敕》相似故也。
右节录杨耕夫《铁函斋书跋》。余别有考附后,杨说差足忝证。清晨起床迻写于此,时庚午八月十三日。凤笙。(钤“栖禅亭长”)
(4)余前言别本《天冠山题咏》墨迹有景印本二,一在清末,一为近年艺苑真赏社制版,顷以艺苑本与此对勘。彼溢出《寒月岩》《玉簾泉》《五面石》《小隐岩》四首。文辞亦有不同,如《逍遥岭》首岭下可字作足,真字作直;《一线天》首中字作天;《仙足岩》首屋字作宝。此本《灵湫》首题下有标注一行,彼亦无之。细玩写本,虽行笔媚婉而行气不实,无宛转相生之妙,疑是赝笔。诗后有子昂跋云,道士祝丹阳示余《天冠山图》,求赋诗,将刻石山中,为作此廿八首,延祐二年十月廿四日。松雪道人其所叙作诗原委,亦与此异。此云,越四年,装成巨册。索重书,故尔走笔。或是彼为第一次写本,即此本跋中所谓付主院者。此则第二次写本,而书于装成之巨册者。至彼本溢出四首,此本当时未必无之。文跋所云廿四首,殆其所见已为残本矣。向晚孤坐,略疏臆见于此,然仍疑彼本非真,明眼人当能辨之也。十九年八月十九日灯下再记,时蚊声如雷,远处炮火犹震摇窗纸,历历作声,吾握管一小时间,又不知伤死人命几许矣。献唐。


是拓为陕刻24首本,制拓精良,先生断为嘉道间制拓,1930年8月间数次题跋。时值中原大战,战火波及20多个省,从6月至8月,晋军占据济南,省府迁往青岛,省图也受到冲击。先生与全馆同仁不顾个人安危,留馆守书。7月30日,省政府任命赵正印接任馆长,先生所谓“谢卸图书馆”即是指此。但赵氏并未正式履职,8月15日,先生接教育厅复职函,力辞不许。21日,续任馆长。受伪作伪跋的拖累,陕刻本历来多被否定。先生自幼习是帖,并不认同此观点。认为文氏题跋中的开篇不合理之处有可能是其兴酣落笔,一时疏漏导致,未必是伪作。又言,纵使文氏之跋系伪作,也不代表《天冠山诗帖》系伪作。再退一步讲,纵使赵书也系伪作,也不能否定其艺术价值。称其神采飞劲,迈往劲拔之韵,在赵氏生平行书除多中锋所写苏诗外,尚未见此佳制。先生也与艺苑真赏社影印翁氏藏28首本墨迹对勘,也认为此墨本媚婉而行气不实,无宛转相生之妙,是伪作。但又据两本款识,特别是陕刻本“付主持者,越四年,装成巨册,索重书,故尔走笔”提出一种假设:翁氏旧藏28首真本为初写本,而陕刻本为四年后重写本,其最初也为28首,只是后来残损4首。传至作伪跋者,不知其中缘由,狗尾续貂,成一独立版本。
5 跋明末清初拓汉乙瑛碑
(1)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李南涧旧藏本,十九年十二月献唐灯下自题。[5](钤“王献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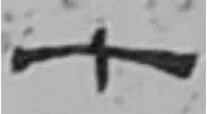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永兴元年(153)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与礼器碑、史晨碑并称孔庙三大名碑,历为书家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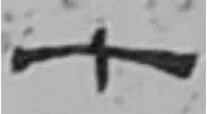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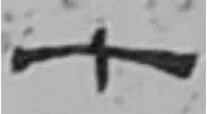
1960年,先生病故,家属遵其遗嘱,将遗稿、书籍、碑帖、金石、书画等私藏分三批捐献给我馆,此在其列。
6 跋明拓汉史晨后碑
此碑每行三十六字,末嵌趺中,在未升碑前,明及清初拓行缺一字。今缺字处皆空格,绵纸浓墨,望而知为明拓也。余见明本孔庙汉碑类如是刘善斋所藏全份整副未剪者尤可喜。往时武进陶兰泉以庙中各碑拓未尽善,字间渍墨瘦损失神,与余约共拓曲阜济宁汉碑法:先洗净,以棉连纸、乾嘉墨,用拓金文法逐行拓条,再付装外,再整张拓之,各加吾二人监拓之印。以耗费昂,豫约者不数人,迁延未果。兰泉逝世,余亦避寇入蜀矣。自顷輖张,旷劫方遒,更无心及此。
大荒道兄嗜金石,亟亟求善拓,傥天假之缘,异日能如兰泉之愿,则一民国拓本可敌乾嘉拓十碑。估所言某字笔画已残已泐者尚有许多处可拓出,昔当验之张猛龙碑矣。戊子四月二十五日献唐济上书。
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169)立,两面刻字,合两碑于一石,记载鲁相史晨等奏祀及实施祭孔之事。阳面刻奏祀之事,俗称史晨前碑;碑阴刻实施祭孔之事,俗称史晨后碑。是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孔庙三大名碑之一,历为书家所重。
是拓仅后碑,为路大荒旧物。路大荒(1895-1972),字笠生,号大荒等,山东淄博人。精于目录版本,自青年时代起即专注乡贤蒲松龄研究,历任省图副馆长、文管会委员等。其自题书签:甲申得于济上并装。1938年因日寇觊觎所藏蒲松龄稿本,路大荒被迫来济,是拓即其客居济南时购得。1948年路大荒嘱居家休养的先生作跋,先生复以花笺两纸。《校碑随笔》载,明季至清初,每行末一字皆未拓,只35字,埋入土中故也。乾隆年间升碑后乃拓全,然末一字皆余半而已,若得到旧拓本36字,则宋元或明初拓本。[7]即明初至清乾隆拓本每行皆35字,直到乾隆年升碑后才有36字。方若“嵌趺升碑说”影响甚大,但误。马子云整理故宫藏拓时,鉴赏过两种秋字禾旁未损明拓本。一本碑阳36字,碑阴35字;一本碑阴36字,碑阳35字。由此知,36字本早就有之,而非直到所谓乾隆升碑后才有。并且碑身、底座皆石质,断无碑身树立后,会在底座中继续下陷的可能。嵌趺升碑,系方氏臆说。之所以会有35、36字差异,当是碑末被泥土淹埋,心细拓手洗去泥土,得36字;粗心者或图省事者,得35字。今以国图藏秋字未损明拓本对勘此本,相差无几,确为明拓。
是拓绵纸浓墨,让先生想起1933年失之交臂的刘献廷藏明拓本。其跋《袁简斋袁香亭合作画册》称,刘氏藏碑帖甚多,仅得明拓孔彪碑,明拓史晨碑、清初精拓乙瑛碑并此册,以价昂未致。[8]这也让先生追忆起1931年陶湘因不满孔庙汉碑全拓历乏善本而相约椎拓的往事。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清末官至道员,民国进入实业界、金融界,任职山东、上海等地。喜收藏、刻书,与先生交好。曾将精刻书籍捐献给省图,《王献唐师友书札》存其13通信件。二人相约椎拓的详情,见于1932年5月及1933年1月陶湘致函,“拟下月天朗气清,亲赴济南,与公洽商,赴馆精拓,并带新旧墨料、精美纸张、良工二人,精拓一次。……倘能仗鼎力拓曲阜、济宁,尤所感盼。”“拓碑之举,议了一年,迄未实践者,拓手未得明白。兹有刘保忠,人既诚实,对于碑帖残完两字颇有研究,特令其趋叩台端,先拓贵馆全份及曲阜(孔林在内)、济宁(嘉祥在内)。此三处如何拓法为宜,并佳纸佳墨均已交之。弟新正月内必趋教一切,还乞先行饬其试办先拓,惟有许多处必须过水洗净浆滞者,统希鼎力维持办到,实文化前途之大幸也。”[9]9月18日,陶湘又致函,欲继续来东拓碑。[10]但从是册题跋看,因耗费过高、陶氏逝世、日军侵略等一系列原因,曲阜之行最终未成,先生引以为憾。时过境迁,先生希望时任职省图的路大荒能有朝一日完成自己与陶湘共同的心愿。
7 跋明拓唐李思训碑
(1)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高南阜跋。甲午春木石盦重装。
(2)老友李伯鹏从故乡来,以此云麾碑残本见赠,乃县中李铭佩旧藏。二十年前展转归伯鹏,中更丧乱,致册首南阜跋残泐,尚忆原文,口述为注于右,两跋在乾隆四年己未,正南阜病臂之岁也。碑文下截漫漶,旧多缺拓,此又散佚不完,重其为乡前辈故物,又有南阜两跋,竭我阮囊,属工重装,庶再续延大千世界之岁月,否则殆矣。李名学瑢,清咸同间收藏甲一郡,详县志人物志。甲午春海曲王献唐篝灯写记。(钤“王献唐”“平乐印庐”)
唐李思训碑,亦称云麾将军碑,开元八年(720)立,李邕行书。书法劲健,凛然有势,为历代书家称道。现存陕西蒲城,残损严重。
拓本第2行“固以为天下”固字、4行“军广子侍中敢”六字、5行“讳孝斌”讳字、6行“群书”损;而第2行“言必典彝”言字、“人之仪”、3行“其惟我彭国公”惟字彭字、14行“谮助”、18行“左屯卫将军”军字均未损。以上为明拓之证。原碑下截漫漶严重,故一般仅拓上半截约900字,但此册弃拓严重,仅上半截400余字,实为憾事。为高凤翰旧物。高凤翰(1683-1749),号南阜等,山东胶州人,嗜砚工诗善画。中年以诸生荐官,知歙县、绩溪县等。乾隆二年(1737)右手突发风痹症,自此改用左手书,风格大变。同年,受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案牵连,获罪去官,侨居扬州五年,与当时画坛革新派扬州画派诸君如郑板桥、金农等相投契,诗词唱和、联袂绘画。乾隆三年(1738)其两次题记,“唐人书当细看其用笔用法所在,勿袭皮毛,始能有得。北海谓学我者拙,知此可与读此帖矣。南阜老农又记,己未左手。”“云麾将军善本极为难得,此本及向时所见高密王绶□本皆近拓中绝少者。乾隆己未,阿坦王君叔和新赋采芹,时余以宦累留滞江南,检囊中仅有此册,遂□题以具贺。四月十一日康山寓舍左手题。南阜。”(钤“高凤翰”)据跋,云麾将军善本难得由来已久。此本为“近拓”中的难得之物,故高氏将之赠予王叔和,作为其考中秀才的贺礼。后辗转归李鸣佩,诸生,工书,得钟王遗法。博购书帖,兼通金石,闭户临摹,不与外事。[11]所藏为道咸间一邑之冠,身后不能世守,百年间荡然无存。
大约1934年,此拓又归同邑李伯鹏。李伯鹏,名巨林等,先生小学同学,好金石,喜收藏,与先生交好,时常于墨蜕互通有无。1954年,将此册转赠先生。因战乱中略有残损,高凤翰跋语损伤“云麾将军善本……此本”7字,先生重新装池,补录缺字并题跋,述此册由来。先生用印多达120余枚,而题跋是册独钤“木石盦”,盖其由来与高凤翰有关。先生旧有高凤翰刻石两种,1950年10月,好友张景栻见其仅有高凤翰刻石而无木刻,将所藏高凤翰木瘿印、木笔筒转赠先生,以成其美。先生欣喜,署所居“木石盦”并治同款印。
初步统计,馆藏王献唐校勘手跋碑帖64种,金石拓本册26余种。拓本册中又有其手辑《金契石友小谱》《寒金冷石文字》等,系汇编多年陆续收集的金石墨蜕零种而成,其中随手考释者不下百余种。据《王献唐金石学编著与题跋一览表》及《双行精舍书跋辑存》两编,[12]此90种金石拓本约占目前已知数量的6成,且题跋数字较多的拓本册几乎全部都在我馆。考虑到其他题跋仅有题写记录,而不知拓本归处,甚至是否亡佚,馆藏此宗文献尤显重要。纵观此批题跋,它们反映了先生对公藏的苦心经营,蒋冯中原大战、抗日战争中舍身守护的大义,严谨辛勤的治学,精准的碑帖鉴定水平,广泛的学术交游及以拓工优劣而非机械地以时代早晚定碑帖优劣的善本观等,是其金石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