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仰底子的毕修勺先生
☉陈思和
有幸结识毕修勺先生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个时候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始研究巴金的著作。一天,有个亲戚患病住院,我去看望,就在病房里高谈阔论,这也是少年轻狂之表现。过后,同病房的一位姓陈的老先生问我亲戚:“刚才听你们在讲巴金什么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毕修勺,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去法国的船票,还有兑换法郎,都是他代办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我可以介绍。”亲戚转告后,我是喜出望外,当下就去拜访了那位陈先生。于是,拿了陈先生的介绍信,我和李辉就登门拜访毕修勺先生了。
毕先生住在长乐路底的一条旧式弄堂里,那时已经快八十高龄了,但是身体非常健朗。因为人的高大,书房就显得窄小,一面墙上挂着吴稚晖、李石曾手书的对联,另一面墙边是小书桌,书桌前面墙上钉了一个布袋,专门存放信件。书桌上摊开着外文书籍。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毕先生是翻译家,以翻译左拉的小说著名。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以前读过的一部译者署名为华素的左拉小说《崩溃》出自毕先生的手笔。
那天的谈话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恍如昨天。说到我们正在研究巴金,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毕先生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与巴金有过交往,他们青年时都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是走的路不同。他是比较靠拢吴稚晖、李石曾一派的无政府主义,参与了创办劳动大学、主编《革命周报》等活动,而巴金则有更加激进的立场,两人的观点有分歧。他回忆了自己与巴金的两次冲突:第一次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时,巴金出于抗议国民党大屠杀的义愤(这场大屠杀是从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弹劾共产党开始的),迁怒于李石曾出钱创办的《革命周报》的主编毕修勺。但是毕先生认为,巴金不完全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巴金骂李石曾的钱是臭的,可是巴金回国以后参与了自由书店的活动,还主编了《自由月刊》,自由书店也是李石曾出的钱,为什么他不嫌臭了呢?这场冲突后来经马宗融从中做调解而平息,两人重归于好。第二次冲突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巴金、吴朗西、朱洗、毕修勺和章靳以五人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其间发生了人事纠纷,巴金与吴朗西分道扬镳,巴金退出文化生活出版社另办平明出版社,而毕修勺和朱洗都站在吴朗西的一边。这场矛盾主要是巴、吴之间发生的,但随着公私合营、政治运动不间断地发生,两人再无机会重新合作。我记得很清楚,毕先生说完他和巴金的恩怨沧桑以后,就说,我不能陪你们去看望巴金,但我可以介绍你们去看看吴朗西,他可是个大好人呵。说着,就拿起司的克(手杖),站起身来,马上就要陪我们去吴朗西先生的家。

著名翻译家毕修勺
毕先生住在长乐路的西头,华山路附近,吴先生住在长乐路的东头,重庆南路附近,中间大约是公交车三站路程。毕先生与我们边走边聊,毫无倦意,司的克挂在他手臂上,也没有当作手杖用。一路上,毕先生讲了他与吴稚晖、李石曾(两个“老头子”)的关系,他追随他们,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怀念。他带着感情地说:“当年我与他们在一起时,就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年纪,我与他们经常在斜桥一带,边走边聊天。”他对吴稚晖特别尊敬,说吴的生活非常朴素,就像一般平民那样,在重庆时,吴的住宅边上就是阴沟,发散着臭味,但他毫无怨言。还说了一件逸事: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有意让吴稚晖接任主席之位。当时夏天,吴稚晖体胖怕热,浑身脱得只剩下围在腰间的一块布,这样出来接见民国要人,说我这个样子去当政府主席,你们不愿意,如果我穿戴得整整齐齐出入办公,我就不得自由,恐怕你们又要忙着公祭了。这样怪话连篇就把主席的职务推辞了。毕先生感叹着说,连政府主席都不要当的人,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我理解毕修勺先生安贫乐居、不求闻达的一生,那就是有着信仰做底子的。他后来被“肃反”、“反右”、“文革”等等政治运动所累,受尽迫害,生死一线,但是他活得坦坦荡荡,胸无芥蒂,就是因为他做人非常有原则有追求。所以,当我再次问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朗声宣布:“我始终信仰无政府主义!”

毕修勺
且不说我们那天见到吴朗西先生和夫人柳静女士的情况,我还是把话题集中在毕先生的印象之上。这以后,我渐渐地与毕先生成了忘年交,经常到他府上去聊天,知道了他埋首于左拉作品的翻译,也知道了他已经译出多种左拉作品的译稿,还不断地在修订旧译,开拓新译。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有一次他指着《巴斯加医生》的译稿说,这是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最后一本,也是最难翻译的一本,里面涉及多种语言。他说,他怕自己年纪大了,来不及译完左拉的全部作品,就挑最难译的这本先译出来。毕先生译稿的旧稿我都看到过,他是托人认真抄写一遍,然后又在抄稿上逐句订正。毕修勺先生的翻译有着鲜明的特色和追求,他尊重原著,采用直译的方法,逐字逐句地对应翻译。这在今天流行的翻译界大约是很不讨好的,所以他的译稿一再被出版社退回来。但是他非常自信,坚信自己翻译的方法是有价值的。曾经有好几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他的翻译著作,只是需要找人润色一下,但毕先生坚决不同意别人随意改动译稿。记得有一次某出版社要出版《人兽》,毕先生要我写一篇导读,我写了以后,他表示满意,并且同意我对译稿做些修辞上的修订,我不懂法语,也只能在语法上稍微顺一顺,但是只改了第一章,毕先生看了以后就收回去了。后来也不见这本译著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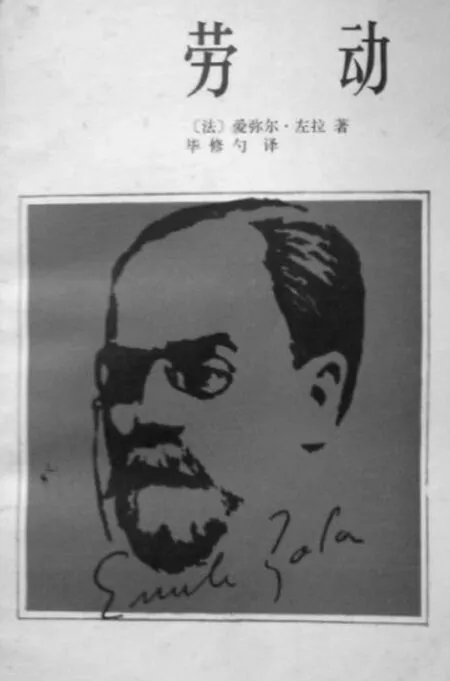
《劳动》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不过,毕先生在晚年毕竟看到了一本旧著的再版。那是左拉的《劳动》,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记得那天毕先生一大早就走到我家,敲了门,亲手送给我新书,还邀请我和吴基民一起在红房子西餐馆吃法国餐。吴基民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文史馆工作,毕先生被聘为文史馆员。吴基民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左拉泪》,表彰毕先生的翻译事迹。我们在红房子餐厅里频频举杯,把《劳动》的出版看做一个好兆头,祝愿以后能够顺利出版毕译左拉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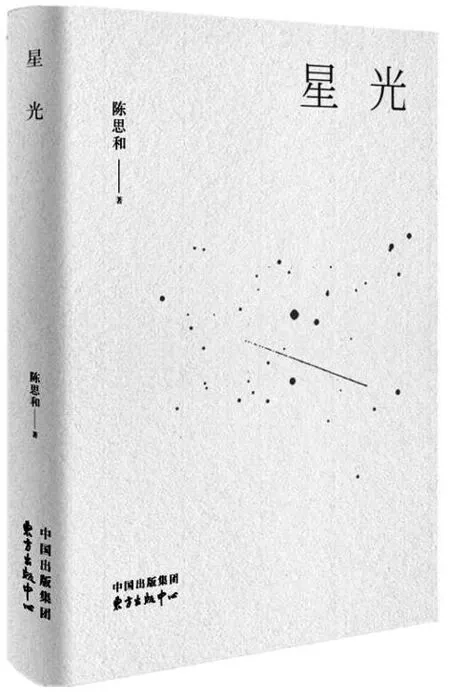
《劳动》体现了左拉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个理想来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三大代表之一傅立叶的思想理论。傅立叶主义还影响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家蒲鲁东,因此也有人把傅立叶理论看做是无政府主义的源头之一。左拉在多部小说里描写过无政府主义者,多数是负面的形象,但《劳动》中描写的社会主义理想却非常有诗意,也最有震撼力。我曾经请教过毕先生,左拉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毕先生说不是的,左拉是傅立叶主义者。我想,左拉作为一个法兰西民族的良心,民主主义的斗士,能够被毕修勺服膺终身,追随终身,他们之间的默契也应该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薪火传承。这样,我们在毕修勺的精神世界里除了找到吴稚晖、李石曾的无政府主义榜样以外,还有就是左拉的欧洲知识分子的战斗传统。
但是,毕先生终究没有等到他的译著全部出版,抱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身后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越来越富裕,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进步,在毕先生哲嗣毕克鲁先生的多年努力下,毕译左拉著作集终于获得了全部出版,真是功德无量!毕先生的其他译著如克鲁泡特金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莫洛亚的《屠格涅夫评传》等也相继出版。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耳边又响起毕先生当年对我和李辉说的话:“我与他们(吴稚晖、李石曾)在一起时,就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年纪……”我和李辉也都过了耳顺之年。在理想主义变得稀有罕见的当今社会,我确实时时生出“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