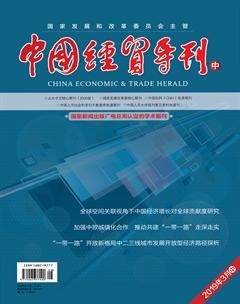新时期东北振兴路径研究
摘 要:信息技术革命削弱了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比较优势正在逐步让位于绝对优势。全球经济的动荡和中国经济发展“三期叠加”,既给东北转型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也为东北振兴提供了少有的机遇。本文以统计数字“挤水分”之后的东北经济状况为研究对象,从观念意识、经济构成和劳动人口三个方面研究东北经济转型的突破路径。
关键词:新东北现象 经济转型 突破路径
自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方针后,东北经济和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伴随着2014年东北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社会舆论方面关于“投资不过山海关”“开门招商,关门打狗”“逃离东北”的命题再次被聚焦,加之“辽宁贿选”“GDP注水”“雪乡宰客”“亚布力事件”等新闻的曝光,东北经济及地区发展广受社会舆论诟病。
学界方面,近些年学者们对于“新东北现象”的研究分析,现有文献中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东北地区保留了较多的计划经济残余,政府体制机制、民众思维观念滞后,营商环境差,市场经济缺乏活力;②东北产业结构、经济机构不合理,国有企业占主导作用,重化工业占比过重,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③东北劳动人口数量下滑明显,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人才流失等现象加剧人口年龄结构的恶化;④改革开放后,基于“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东北经济地位受到冲击;⑤全球经济不景气,原材料需求减少,东北周边国家经济萧条,对外贸易空间有限。
在上述的文献观点基础之上,本文以东北经济内在因素为出发点,从唤醒市场意识、寻求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缓解人口危机三个方面讨论东北转型的突破路径。
一、唤醒市场意识
(一)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现状
“营商环境就是生產力”。营商环境是企业活动中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环境的综合反映,地区内企业数量的变化能够有效反映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状况。在国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后,我国新开办企业出现“井喷”现象,但东北地区企业数量表现却很“平稳”,企业法人数增长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数据再次证明了东北地区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于自由市场竞争既缺乏心理准备,又缺乏一技之长,对市场观念持有恐惧心理与躲避行为。营商环境本质上是政府的管制环境,政府的越位、失位和错位都会对营商环境造成影响。“辽宁贿选”所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和官僚主义,体现了政府官员法律意识的缺失和公职人员道德意识的缺位,加剧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而“雪乡宰客”的行为又体现出民众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出现了偏差。作为市场监管者的政府官员以及作为市场经济核心要素的民众,都体现出一种滞后的思想观念,营商环境的贫瘠与经济形势的走低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二)针对价值观念落后的改善途径
1.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为转变。一是营造法治社会。推进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前提。投资商被坑与个别官员行为有关,游客被坑与当地部分民众有关,这两个维度都体现出了法律意识的缺失。没有法治保障就无法激活市场活力,更谈不上“放管服”改革的深化。东北地区需要严肃法治建设,全面执行依法治国,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二是加强“公共人”意识的建设。政府一些官员把自己定位成为“经济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其公职人员的身份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欲望无法调和。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下,政府预算最大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腐败等行为成为政府或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扩张的具体表现。因此,在严肃法律的同时东北地区需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道德建设,明确其社会责任,唤醒“公共人”意识,实现官员的内在规范。
2.民众意识的疏导和引领。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辉煌和国企下岗潮的冲击,东北民众对于东北的失落具有一种方向的迷失和自我价值的怀疑,对于市场经济有一种本能的排斥。面对这样的形式,地方政府需要全力落实“双创”政策,给予创业者和小微民营企业足够的政策支持。在完善政府自身条件的基础上主动寻求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外资和外贸的市场化运作,激活市场活力,推进市场化进程。
二、产业结构优化
(一)东北地区经济产业状况
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期实行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新环境的发展要求。2003年国家实施的政府主导型东北振兴实践卸掉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包袱,不过与此同时,投资作为东北经济拉动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工业制造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未有所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不高、结构失衡、动力不足、稳定性较弱的劣势并未得到缓解,东北经济对于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进一步加剧。随着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能力持续走低。在2012年投资增长势头出现拐点后,东北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新东北现象”出现。虽然近几年在当地政府轻装上阵“挤水分”之后东北经济有所回暖,但是经济体制与结构矛盾仍旧突出,产能过剩仍然钳制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打破GDP数字迷恋,实现供给侧改革,成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恢复地区竞争力、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的重中之重。
(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路径
1.工业内部优化升级。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供给侧改革,加速落实国有企业“去库存”。鼓励企业以“新亚欧大陆桥”和“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路径,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推进沿线境外工程和境外装备工业园区建设,寻求沿线国家有效市场,尤其面向空间广阔但产业基础薄弱或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资金紧缺的国家,加大经贸往来力度,加速转移过剩产能和低效益产业。
规划开展接续产业与替代产业相结合的混合开发模式,通过上下游接续产业的发展和过度,逐渐将主导产业转移到非资源型替代产业。在接替产业的选择方面,根据王勇、霍经纬、姜晓婧等学者的模型分析,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专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及较大的可能性。
结合制造业的顶层设计,提前为5G商用和物联网时代布局,具体包括:综合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建设重点领域智能工厂;推进智能物流、智能服务项目,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高良品率;通过智能模拟和传感技术,实现柔性化生产等项目。
2.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引导支持工业配套产业的更新和引进,鼓励企业分离外包非核心业务,向管理、研发、营销等价值链高端部门延伸,重点发展以交通运输、仓储、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生产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转型。经济结构方面:①打破国有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遏制以政治权力和国有资本为代表的“渡口经济”,确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双主角地位。②推动“双创”落实,加快众创空间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倒逼国有企业改革,提升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三、缓解人口危机
(一)东北地区的人口困境
虽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随着经济发展,出生率降低、人口流动集聚符合劳动力资源自我调节的规律,但东北地区的劳动人口缺失有其严重性和特殊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众多,在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民众是否遵守生育政策往往与工作机会挂钩,因此当地人口生育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伴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加速,东北地区老年人抚养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的压力较大。②作为商品粮生产基地的东北地广人稀,同时经济结构占主导的重化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人口集聚的影响有限,致使地区就业密度远远低于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③“新东北现象”的出现,加剧了东北劳动人口流出的速度,尤其是高学历人口流失严重,导致人口结构劣化与人力资本损失。根据杨东亮、杨玲等学者的人口模型分析发现,东北高学历流出人口对于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明显强于其他受教育程度人群,且户籍人口迁移对于东北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人口流出,加之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作用,人口流失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形成恶性循环。④东北地区国企比例过大,就业率无法反映大量存在的隐蔽性失业和非充分就业现象,劳动力参与率不能有效反映劳动力的真实利用情况。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政府体制机制改革以及产业技术升级,结构性失业人口将在未来大幅度增加。当地就业形势的恶化,会加剧一般劳动人口的外流,限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转型。综上所述,目前东北地区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严重性远超当前面板数据。
(二)人口问题的突破路径
1.从人口存量和增量两个方向保证劳动人口基数。存量方面,针对老龄化演变,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传统印象,通过制度政策引导,将老年人向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方向迈进,具体包括:①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为有弹性的延长退休年龄、维持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提供心理及生理方面的保障;开发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鼓励有充分技能和知识的老年人二次就业等。②针对就业密度不足,从农业方面入手,通过投资和运用高新农业设备及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释放农村劳动力资源,加大农转非人口的保障力度,推动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为推进东北产业结构优化,拉动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劳动人口的保障。
增量方面,在奖励生育、降低养育子女成本、提高东北的生育率水平的同时,放宽外地人口落户限制,加大人才落户东北的补贴力度,为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供政策便利。
2.从创造和储备两种角度提高人力资本(人均产出增长率)。创造东北本地人才。地方政府在对于教育科研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对教育事业单位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鲶鱼效应”和淘汰机制刺激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和科研工作的投入,提高当地人力资本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提升当地人才的竞争力和劳动力市场活力。
增强东北现有人口对于东北地区的心理认同及偏好,具体包括:①大力支持以大企业高管、连续创业者、科技人员创业者、海外归国创业者为主体的创新型企业,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空间,为经济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性;②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让人力资源在市场的历练中转化为人力资本,激活市场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为服务业企业在细分领域开展“小而美”的新型经营模式提供营商土壤。③针对经济转型期间将会出现的高失业率,做到未雨绸缪。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岗前培训规划工作,引导扶持发展老年产业,将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劣势转化为开展银发经济的先发优势,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改善民众对于东北地区未来发展的心理预期。
参考文献:
[1]武靖州.振兴东北应从优化营商环境做起[J].经济纵横,2017(01):31-35.
[2]王勇,霍经纬,姜晓婧.新常态下辽宁经济转型升级的接替产业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02):91-97.
[3]杨东亮.东北流出流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比较研究[J].人口学刊,2016,38(05):34-44.
[4]周宏春.新時代东北振兴的绿色发展路径探讨[J].经济纵横,2018(09):64-72.
[5]张屹山,张可,辛本禄.化解东北振兴中体制性障碍的路径探究[J].经济纵横,2016(10):45-48.
(董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