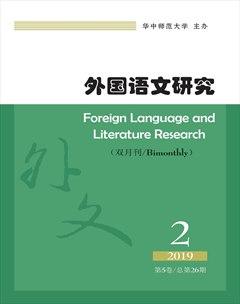世界文学的建构力量:文学资本、语言与翻译
刘岩
内容摘要: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所著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是世纪之交以来难得的学术佳作。本文对此书展开评析,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建构因素进行阐释,以展示文学场域、文学资本、语言、翻译和神圣化资助人在构建此文学空间中的作用,并相应地指出本書的局限之处。
关键词:《文学世界共和国》;文学场域;语言;翻译;神圣化资助人
Abstract: The French critic Pascale Casanova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has been regarded a significant literary masterpiece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aper focuses on factors such as the literary field, the literary capital,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patrons which construct the literary republic to reveal these factors influence.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book will also b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Literary Field; language; translation; patrons
Author: Liu Yan is Ph.D. candidate a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tongjiliu2017@outlook.com
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所著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文学世界有自己的边界地理划分;文学世界的版图是根据其“美学距离”和文学“制造”以及文学“祝圣”来完成的(卡萨诺瓦6)。在文学资本的催生下,文学也出现了等级化现象。作者以乔伊斯、易卜生、福克纳等作家为例,详尽探讨了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阐发对于当下“本土化”和“全球化”文学发展的思考。
该书是卡萨诺瓦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国际文学空间》(1997年)所著,是继歌德阐释世界文学概念后的一部理论巨作。作者对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建构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对构成此文学空间的诸多要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对比,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各民族间文学交流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世界文学的建构力量
1.1 文学场域与文学资本
继歌德首次描述世界文学后,卡萨诺瓦亦认为文学一开始都是在独立、封闭的区域内流行,形成自己的文学资本,而后才通过相互竞争,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世界文学空间。作为布迪厄的学生,卡萨诺瓦也指出文学存在着“资本的场域”。布迪厄认为文学场域是客观存在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李全生 146)。场域是社会成员集中竞争的场所,是策略的实践场,符号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实现之地。社会分化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场域,布迪厄视其为自主化选择的结果,文学场域作为其中的形式,是传统作家与先锋作家的交锋场所,其包含了四种基本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卡萨诺瓦将“文学世界共和国”视作不平等自由的存在物,其内部通过文学等级化、文学语言、文学奖项和文学批评等资本进行不平等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残酷的,遵循着“物竞天择”的法则。不同于布迪厄四种资本的划分,她首先认为语言是文学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语言政治社会学只在语言经济环境中研究语言的使用(以及 ‘相对价值),而不会在纯粹的文学空间中定义他们的语言学——文学资本。我建议将这种语言学-文学资本称为 ‘文学性”(卡萨诺瓦 13)。语言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通过文学遗产的技巧,形成了独立于其他地区特殊的文学资本;资本再通过文本、翻译、文学祝圣和文学弃绝等活动参与竞争,语言成为了文学游戏的密码,只有拿到这些密码,才可以进入到文学大家庭。因此,语言脱离不了政治、民族的范畴,“语言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身份象征——文学遗产和民族心理结构是相互联系的” (34)。借助语言,国家和文学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不间断的对抗和斗争来强调他们之间区别的过程中,欧洲国家才一点点出现;同时,自16世纪开始出现了跨国政治领域的最初形式”(35)。卡萨诺瓦认为文学资本是民族的,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一种依赖,将文学世界中的政治、经济观念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说,文学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活动而产生的。文学空间的获得逐步摆脱了政治对抗而存在,世界文学空间的获得,恰恰是通过每个民族文学的自足化来完成的。作家一方面受到过去文化遗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全球文学等级结构联系在一起,据此卡萨诺瓦对于世界文学空间的建构进行了全新的阐发。
卡萨诺瓦认为文学历史造就了文学等级空间,反之这种结构也促成了文学的历史。最早进入到该空间的文学,则占据了“经典文学”的位置,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文学相互间抗争,文学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使得文学出现了依附的状况;但此结构并不稳定,随着时间和资本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最古老的文学占据了雄厚的资本,更为独立;“文学空间借助美学的、形式的、叙事的、诗歌的——重新诠释了民族和政治的赌注,文学空间在同一运动中也否定了这些赌注”(95)。文学空间竞争对于同一标准的需求催生了“文学格林尼治子午线”。文学子午线作为一个共同的衡量参照,将文学空间组织起来。作者将巴黎看作是现有文学空间的子午线,民族作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所在空间中的位置。远离文学子午线的民族文学被视为弱小的民族文学,在此文学场域中的作家欲进入主流文学,则需要用过翻译、语言竞赛等手段来自我祝圣,获得文学世界的认可。
1.2 语言和翻译的力量
对于文学场域,卡萨诺瓦特别强调“在文学世界里,依附性不是单一呈现的。等级结构不是线性的,它不按照简单的图表集中的、唯一的统治进行描述”(130)。文学的反抗往往是从语言实践开始的。1549年,法国杜贝莱发表《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一文,成为了世界文学空间的发源。法兰西文学对于拉丁语的蚕食,对于法语写作的发扬,使得法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中心。而爱尔兰文学这样的弱小民族文学,语言对其民族文学的觉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叶芝竭力挖掘本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文学,将其作为创作的源泉,同时醉心于爱尔兰神秘主义,以此唤醒民族同胞的自豪感;而以道格拉斯·海德为代表的一批“盖尔语联盟”作家,则大力提倡以爱尔兰盖尔语作为创作语言;此后辛格又将爱尔兰口语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体系中。对于民族语言的坚守,成为了对抗主流文学,彰显其特异性,进入到主流文学世界的砝码。
弱小民族文学进入到世界文学空间,获得认可的另一条途径则是是通过“祝圣”,或是到世界文学之都进行文学创作,或是拥有流散的经历,或是用主流文学语言写作,或是通过翻译等手段实现此目的。“前殖民地作家需要承受三重统治:政治、语言和文学;他们往往处于一种经常的双语环境中……”(297)萧伯纳离开了都柏林,来到巴黎实现自我祝圣。他认为在故国很难找到自己需要的纯文学创作模式,且缺乏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福克纳通过巴黎文学界的译介和评论,逐步走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詹姆斯·乔伊斯虽然关注爱尔兰素材,但却采用了英语来写作,维持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努鲁丁·法拉赫是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索马里作家,但其内心并不愿意接受此现实;在坚持口头文学传统的索马里语和作为文学书写的英语之间,作家被迫选择了后者,因而跻身于世界文学的殿堂。
卡萨诺瓦在该书中一再表明文学性的重要性,即评判哪种语言更具文学性;相互比较下,哪种文学处于边缘化。她将文学分为“统治”和“被统治”两种形式,翻译则充当了两种形式间转换的工具。翻译过程中的种种要素,如翻译者、读者、翻译实践活动、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成为了衡量语言的标准。“将偏离中心作家的远离中心的出路描写成纳入翻译上统称的范畴——采用主流语言、自我翻译、双语作品和对称的双语翻译、创造和推动民族语言和大众语言的发展,创造新的文字样式,两种语言共生现象,都不应该被看作相互孤立和割裂的解决方法集成,而是不确定、艰难和悲剧出路的某种连续”(297)。语言间的翻译转换不是简单的文字活动,而是颠覆文学等级的重要工具。翻译既是译者创造性、叛逆性活动,又与文本、接受语境密切相连。卡萨诺瓦将翻译视作文学活动中作家融入主流文学世界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是各个文学竞争的工具。
然而,语言并非是弱小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唯一途径。作为文学资本的一种形式,采用主流语言写作的确可以使作家较快地融入到文学场域,但语言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被统治语言”下的作家产生了一种焦虑和不安,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自在文学场域内的地位和文学性。“对于所有 ‘远离中心的作家而言,翻译是通往文学世界的主流通道:它是文学上认可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简单的平行转换,不是人们在世界出版界进行的数量上的交易。相反,翻译活动是所有参与者之间全球对抗的关键赌注和武器,是世界文学空间内部斗争的特殊形式”(135)。
打破民族语言的结构和文学性的限制成为了一种动力,“弱小民族”语言的作家均面临着某种形式的翻译问题,被迫做出抉择:是保持本民族语言的独立性;还是接受被翻译的命运,转投某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从而被视为本民族文学的“背叛者”。作家寻求采用主流文学语言,通过自我翻译、双语写作等形式来保持自我的文学性和先锋性,创造新的文学样式。考虑到作家自身的文化身份、成长环境、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翻译这种“祝圣”形式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借助此工具,“被统治语言”可以转化为主流文学语言,从而获得一定的文学资本。弱小民族作家永远面临着要么默默无闻、要么选择“背叛”的困境。民族中最自主的作家往往都是翻译家,以此来积累相应的文学资本。匈牙利诗人达尼罗·金斯将叶赛宁等人的作品进行翻译,介绍到本国;日本作家崛口大学通过翻译将阿波利奈尔等人作品介绍到日本,从而重构了世界文学空间内的美学图谱。但通过翻译,文学资本不断增长,使得这一活动突破了语言转换的作用,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学价值。“翻译、自我翻译、转录,用统治地位的语言进行的直接的写作视作文学化——通过这些活动,一个来自文学贫瘠地区的文本最终可以被合法机构视为真正的文学文本”(157)。
1.3 神圣化资助人的魔力
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所带来的文学资本并不一定能对本民族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见除去语言和翻译,还有其他因素决定着文学资本的重新分配。译者自身拥有一定的文学资本,神圣化的几率则更大;而当译者缺乏此资质时,神圣化资助人中其他要素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因素可以是个人或是机构,前者由权威的译者、知识分子、作家等组成;后者往往是学术团体。前者依靠自身的权威和声望进行翻译,负责翻译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因受到意识形态、审美情趣、商业化等因素影响,资助人会选择主流文化的作家作品加以介绍、推广,从而构成了全新的文学资本。20世纪未来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则恰恰映证了此观点。
未来主义诗歌兴起于20世纪初,其代表诗人痛感象征主义不能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新时代的迅猛进步,开始倡导一种歌颂机器文明,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学运动(袁可嘉 167)。中国学术界对于未来主义诗歌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尤其是其代表作家马雅可夫斯基和阿波利奈尔的作品。译者主要包括余振、戈宝权、飞白、丘琴、萧三等知名译者,译作则发表在《诗歌月刊》、《外国文艺》、《作家杂志》等诸多刊物上,譯文不乏精彩之作,相关全译本和单行本共计20多册。但纵观中国诗歌史,未来主义诗歌却未能掀起波澜,未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20世纪的中国翻译,“信达雅”的标准虽然十分重要,但译文的可信性却非译者的唯一意图所在,而是“借助西方文学的权威性来改变中国,推动一些本国文学自身所不能产生的改变”(王宏志149)。王宏志的观点至少清晰表明了20世纪中国的翻译进程中,译文的“权威性”具有巨大作用;但就未来主义的例子来看,译者和译文的权威性却并未给中国文学带来特有的改变;反之,对于未来主义诗歌形式的理解、我国的意识形态、诗歌的推介、出版等因素则影响到了文学发展的进程,文学活动仍要与各民族具体文学环境相联系,且与政治、经济环境不可分割。
二、《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局限: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
依据“文学格林威治子午线”,卡萨诺瓦将巴黎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大都市,是弱小民族文学“祝圣”之地。现代性使得巴黎具备了先锋性和包容性,代表艺术的高峰。同时,作者将中国文学视为远离文学中心的产物,缺乏必要的文学资本。
中国古典文学,从秦汉以降,直至隋唐,对世界文学的构建,特别是东亚文学圈,如韩国、日本等国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众多的中文,在卡萨诺瓦看来,沦为了长期被忽视的语言。与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则并未获得与其文学性相匹配的地位。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已远离“文学格林威治子午线”,是否具有与主流文学相抗衡的文学价值?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各民族文学交流应遵循何种法则? 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海外文学界,是否要通过翻译等必要的“祝圣”手段?
卡萨诺瓦认为“文学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历史越长,民族文学经典作品影响越广泛,其文学资源就越丰富,能够成为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之一。文学中心凭借雄厚的文学资本和国际声空间望从而掌控了文学经典化的权力,并通过赋予文学作品合法性,生产其象征价值,宣告其文学存在,使其进入世界文学行列”(芮小河 152)。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也拥有悠久的文学发展史,积累了雄厚的文学资源,但与巴黎等世界文学中心相比,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缺乏相应的国际声誉。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成功传播,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文本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非是远离“子午线”的弱小民族语言。文学资本在场域内的流动实际上反映出经济资本的作用。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和中国近代经济和政治的衰落,中文逐渐拉大了与法语、英语等文学语言的距离,导致了被忽视的局面。
歌德认为各民族间文学的差异性是世界文学存在的必然条件,由此表明世界文学空间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之上,“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各民族文化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体,世界文学也不是少数经济强国之文学”(蒋承勇 23)。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世界文学空间的建立仍然要考虑到西方的文化霸权,彰显中国文学的特点,寻找恰当的策略实现中国文学的海外交流。卡萨诺瓦将法语构视为“普世性语言”,是各国文学可利用的重要创作手段,是构成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基础,但却忽略了东西方文学在创作思想、审美标准、诗学体系、文学体裁、文学语言上的差异性,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要考虑到海外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各异需求。本民族所认可的“经典”作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海外学界的认可;相反,一些处于文学场域边缘的作家却能够很快地被海外读者所接受。以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海外传播为例,“五四的女性文学在传统的德才对立模式中滋长生成,又备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洗礼。面对历史的遗留,女性占据身体之德,而无才华之美……对待 ‘女性文学这一称谓的恐慌,时至今日仍困扰残雪、王安忆之类的女作家,惧怕被贴上这一标签后,其作品就被简单地等同于抒情和女气,从而取消了其探索现实的能力”(季进、余夏云 132)。而西方世界对于女性文学的分析则更侧重于从性别、身体解放、政治、欲求等方面来解读,与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模式并不相同。同为现当代女性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则在海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其中一个原因源自于其“流散作家”的身份认同。
卡萨诺瓦强调“文学艺术品的价值再生产包含经典被改成为不同的形式、文类和媒体形式,作家及其作品越来越仰仗文化工业及大众媒体的关注。编辑、出版商、译者、文学奖管理者等实际上承担着神圣化文学作品的职能”(芮小河 154)。此观点表明在数媒时代,商业化的力量也成为了文学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出版商、宣传机构的发表推介、学术机構的评价、各类教材的编写都对异域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神圣化资助人”在文学交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而翻译在各异文学间的交流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依靠翻译这一“祝圣”手段,就要考虑到译者因素,同时还应考虑到各民族的文化差异,灵活采用异化和归化的手段,保持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丹穆若什认为“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并且是那些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丹穆若什 6)。丹穆若什的观点充分表明世界文学空间的建立依赖于文学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再生,而翻译则是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手段。英国汉学家杜博妮曾指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足主要源自翻译决策的失误,即翻译决策人只关注专业读者群,如汉学家、评论家、学者、出版商、编辑等, 而忽略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众读者(Bonnie 22)。根据杜博妮的论断,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成为中国文学现今走向世界文学的重要议题。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一种建构,世界文学空间内的文学流通则需要多元化的翻译,而非局限于一种语言译本或是一种文明。翻译作为文化符号的再编码,必然会有变异的情况发生。两种文明间的碰撞、译者的叛逆性、读者期待视野等因素都会导致变异的发生。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则要充分考虑到此变异,在作家作品、译者、出版机构等选择上不仅要坚持中国文学特色,还要顾及海外学界的接受,如所选择的“祝圣”作家是否具有巨大的文学资本和商业价值、本国译者与汉学家合作翻译、签约海外知名出版社、加大媒体宣传等手段。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在构建文学世界共和国进程中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实现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也赋予了世界文学经典新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打破了原有的地缘限制,促进不同文学间的交流,丰富了文学审美范畴,也使得各国文学得以在保持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的价值关怀(张希琛 65)。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外文学交流中既要注意到文学资本的不平均性,也要看到坚守民族传统的必要性,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实现民族文学间的相互交流,力求达到歌德所设想的平等原则下的世界文学格局。
三、结语
《文学世界共和国》一书突破了歌德所限定的世界文学概念,将世界文学空间视为不平等文学资本相互竞争的文学场域;而进入该场域,则要依靠语言选择、翻译、神圣化资助人等手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世界文学的发展轨迹,同时引发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深入思考,可谓是一部煌煌巨作。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onnie, S. Mcdougall. “Liter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 Chinese Translation Journal 5 (2007): 22-26.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Luo Guoxiang, Chen Xinli and Zhao Ni. Beijing: Peking UP, 2015.]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學》。查明建、宋明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Trans. Zha Mingjian and Song Mingwei. Beijing: Peking UP, 2015.]
季进、余夏云:《世界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Ji, Jin and Yu Xiayu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eijing: Peking UP, 2017.]
蒋承勇:“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文学评论》3(2018):23-31。
[Jiang, Chengyong: “‘World Literature Is not Literary ‘Cosmopolitanism.” Literary Review 3 (2018): 23-31.]
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烟台大学学报》2(2002):146-150。
[Li, Quansheng. “A Brief Analysis of Bourdius Field Theory.”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2 (2002): 146-150.]
芮小河:当代法国社会学派文学经典化理论的演变。《西北大学学报》5(2018):148-156。
[Rui, Xiaoh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rench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to Literary Canonization: From Bourdius ‘Field of Production to Casanovas ‘World Literary Spac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5 (2018): 148-156.]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Wang, Hongzhi.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Tianjin: Nankai UP, 2011.]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Yuan, Kejia. Studies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Modern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Group, 1993.]
张希琛: 从“全球化”到“一带一路”:中国视角下世界文学格局新变化。《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6(2018):61-68。
[Zhang, Xichen: “From ‘Globalization to ‘Belt and Road: New Change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Pattern under Chines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6 (2018): 61-68.]
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