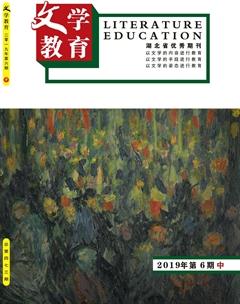艾青1938年的行迹与诗歌创作
内容摘要:大跨度的空间迁徙、原生视野和粗犷北方的冲撞、陌生的人文地理景观,都震撼着艾青心灵,也影响着艾青的诗歌创作。民族苦难覆盖了前期诗歌聚焦自身的忧郁,辽阔的北方拓展了艾青的诗歌视野。本文以艾青北上的时代背景与诗歌创作为基础,探析北上与艾青诗歌、诗风转变间的关系。
关键词:艾青 诗歌创作 初次北上 诗风转变
一.深藏悲哀的苦难“大地”
1938年,应李公仆的邀约,艾青前往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这是艾青第一次跨过长江,涉足风沙覆盖着的北方大地。不同于记忆中的家乡与想象中的北方,满目疮痍的北方大地令艾青震惊,灰蒙蒙的天空,车窗外的山川线条突兀,极其寒冷的气候,就像他唱的,“北方是悲哀的”。伴随着抗战的号角,艾青写下了《卖艺者》《死地》等记录劳动者在黑暗现实中的悲苦与叛乱的诗歌,用诗歌讲述北方的苦难。
大跨度空间迁徙、南方视野和粗犷北方空间的冲撞、陌生的人文地理景观,都冲击着艾青的视觉,震撼着他的心灵。途中的见闻、粗狂豪放的北方大地、战火的摧残都影响了艾青的诗歌创作,表现为诗歌景物叙述的变化。“河流”叙述的变化显现出北上对艾青诗作的影响。1938年之前,艾青印象中的祖国空气水润,物产丰富,带有水乡特有的柔美线条,和风细雨的气候,生活环境温润。穿过被敌机疯狂扫荡过的大地,走过蒙着沙雾的黄土地,艾青到达黄河边,听着黄河的涛声,颠簸在黄河的恶浪中,回忆途中的民族苦难,他写下《风陵渡》表述个人心境。祖国在抗战的风雨中飘摇,艾青历尽万难,前往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传播希望与光明的信念,就像他诗歌写的那样,“古旧的渡船/载着我们的命运/古旧的布帆/突破了风,要把我们/带到彼岸。”尽管侵略者在北方“汹涌着浑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他依旧对民族满怀信心。
大地,艾青诗歌中里的另一常见意象。艾青说,“叫一个生活在这时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①他诗中的忧郁多来自脚下的苦难大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驴子》等诗中都有表现。艾青在北方土地上抒发忧郁,诗歌中描写的荒原、荒漠等粗狂大地,与当时中国的残破现实一致,和他诗的灰色忧郁也相符合。
此时的诗歌乡土中国的特色鲜明,意象就地取材,诗歌与现实的结合更贴切。与早先的忧郁落寞不同,此时的诗歌忧郁源于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但这一阶段的国民忧郁中也带有个人忧郁。《北方》表述了他对北方的悲哀,也穿插了他的个人忧郁、悲哀。孤单的行人/上身俯前/用手遮住了臉颊/在风沙里/困苦的呼吸/一步一步地/挣扎着前进……”。诗歌《灯》,以天边的灯为意象,表达内心的绝望;而1938年的诗中,正面情感代替了前期诗歌中的消极颓废,忧郁绝望也多与反抗等情感相伴出现。艾青“渴望有人燃起愤怒的大火,烧亮当时的中国”,《北方》就隐藏了这样的火种,《北方》对现实苦难的叙述,显示了他内心由苦难现实激发的悲愤,但抒发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土地/---这土地/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因为对土地的热爱,他号召人民反抗侵略。
艾青目睹了侵略者对北方的摧残:房屋被炮火炸毁,人民流离失所……中途的见闻增添了他诗歌的悲哀与忧郁。艾青在诗中对北方的描述是“补衣妇坐在路旁/行人走过路/路扬起沙土/补衣妇头巾上是沙土/衣服上是沙土”,妇人旁边,孩子“可怜的眼/瞪着空了的篮子”,通过这对母子的形象描述,艾青将战乱中的北方百姓的生活状态投射到众人的目光之下,他在诗歌结尾写到“她给路人补好袜子/行路人走上了路”,行路人穿上补好的衣袜,继续逃难,但这对可怜的母子呢?他们该去往何处?内心的悲哀与愤怒浸润了他诗歌的悲愤情感。
二.苦难大地激发的呐喊
从小寄养在大堰河家中的“地之子”,对广大人民怀有深厚的爱,也对底层百姓的苦难“耳濡目染”,故乡畈田蒋村饥荒中的乞丐乞讨尚且可以归因于某一次天灾和地主剥削,但陇海线上如此多的逃难乞丐指向何处呢?民族灾难与战争导致的饥饿使北方人民沦为乞丐,为了果腹活下去,“乞丐们”向过路人伸出乌黑的手,期盼能够得到食物,“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事物/和你用指甲剔牙的样子/”,因为饥饿,乞丐们“伸着永不缩回的手/乌黑的手/要求施舍一个铜子/向任何人/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士兵”。满身黄土的补衣妇母子、陇海铁路线上的乞丐,艾青用诗歌动态呈现了灾难的深化。战争加剧了北方的悲哀,也加剧了艾青内心的悲愤。这也解释了艾青这段时间诗歌中的忧郁、愤怒的情感,这段特殊国情中的诗歌创作,抒发了大地之子的深重情感。
北上的影响渗透到诗歌中,表现为诗歌景物叙述的变化,也影响了艾青这一阶段的诗歌理论,面对北方的苦难,他在《诗论》中写道,“诗实具体表现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②战争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在失去“生命的绿色”的大地上艰难的活着,这让艾青深感忧愤。在草原诗人端木蕻良“北方是悲哀的”话语的激发之下,写下了长诗《北方》。“不错/北方是悲哀的/从塞外吹来的/沙漠的风/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与时日的光辉。”黯淡原野,荒凉杂乱的景象在艾青的诗歌中较多的出现,诗开头便在自然环境上呈现出北方的悲哀;接着艾青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上,表现北方的深重苦难,“北方的土地和人民/在渴求着/那滋润生命的流泉啊!枯死的林木与/与低矮的房屋/稀疏地,阴郁地/三步在灰暗的天幕下;天上/看不见太阳/只有那结成大队的雁群/惶乱的雁群/击着黑色的翅膀/叫出它们的不安与悲苦/从这荒凉的地域逃亡/逃亡到/绿荫蔽天的南方去了……”
艾青将自己主观感受,通过诗歌中的意象加以表现。塞外的沙漠风,漫天黯淡的沙雾,荒漠的原野,寒冷冬日里的村庄,山坡、河流,风沙中的孤单行人,波涛浑浊的黄河等意象描绘出战争中人民的悲凉生活。“绿荫蔽天的南方”是艾青原生记忆中的祖国,北上的地域差异让艾青的漂泊感再次涌现,但“这来自南方的旅客”仍旧深爱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他们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先祖的抗争书写传递了抗争的信念,被压迫的北方民众,也要坚决的反抗斗争,借祖先抗争自然,艾青在诗歌中激励大众反抗侵略。
三.空间迁徙生发的创作转变
北上是艾青了解北方的入口,中途的见闻刺破了他记忆中对北方的美好想象,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北方的想像叙述。他在寄托情感的《怀临汾》中写道,“在北方的夜里”,望着眼前这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疏落的枣树的枝桠支撑着的”灰蓝色天空下平展的无边原野。萧瑟的景物勾起他对旧友的想念,他们有的已在战争中死去,“但死了和活着的/一样使我们亲切啊”。再联想北上,艾青慨叹要“把人生看作浮萍的古人/慨然地接受/明天的离别。”叹息自己与友人昔日匆忙离别,也预示即将的离别。日军进军山西,炮火蔓延到临汾,艾青再次成为“漂泊”的游子。
“意象:翻飞在花丛,在草间,在泥沙的浅黄的路上,在寂静而又炎热的阳光中……”③地理迁徙,战火洗礼影响了艾青的诗歌,让他诗歌意境更加开阔,夹杂的情感内容更加丰富。以“独轮”在灰黄土层留下辙印的手推车、伸着黑手的乞丐、满身黄土的补衣妇、孩子等意象都深度表现了北国的悲哀。《驴子》中的驴子是个浑身披满沙土、眼睛瞌睡、脚步疲乏的意象,透过这一“走着那/广漠的土地上的/不平坦的荒凉的道路”的牲畜,艾青表达了对风沙笼罩的北方土地、原野上奔走的人民的深切忧思。“迈着这样笨拙的脚步,跨越过风雨尘土统治之国,在坚忍里消磨岁月”,艾青借骆驼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这批来自北国的“骆驼”,是失去土的北方农民的代表,是广大北方农民困苦生活的写照。
艾青以“过客”的身份亲历了南北的巨大差异,站在“看客”的视角目睹了饿殍遍地,人民流离失所,《北方》《乞丐》《补衣妇》等一系列诗歌是他在这一连串视觉冲击之下的情感表达。诗歌“直抒胸臆”色彩更明显;在意向的选用上也都带有明显的北方特色,“乞丐”、“补衣妇”、“孩童”、“乌黑的手”等意象,源自艾青北上途中的亲历亲闻。此行创的一系列诗歌,“在艺术上,采用了细致地刻画现实与巧妙地象征、喻比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诗歌的语言上,更加追求朴素与自然的风格,而在内容与情感上,则突出地露出作者深深的悲哀与忧郁。”④色调苍凉的意象,愤怒的内心情感,集结成诗歌中对反抗民族压迫的大声疾呼。
伴随心境变化、地域迁徙与抗战形式变化,象征着光明、希望的意象“太阳”显现出更加强烈的希望、光明意味。“《向太阳》以磅礴的气势、炽烈的情感和絢丽的色彩歌唱了民族的奋起与抗争,歌唱了波澜壮阔的抗战浪潮以及诗人对战争的必胜信念和美好憧憬。”⑤“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⑥《火把》中,太阳“以难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向它奔去”。“苦难中挣扎的人们”,心胸仍有对人类再生之确信。“早期诗歌中,阳光、灯光都是反复使用的意象,但阳光、灯光只是诗人的心喻,还没有和太阳或光明代表着民族国家的希望的意蕴相融合。”《向太阳》中,艾青完成了太阳意象与家国命运的融合。“太阳”“照在我们的久久地低垂着/不曾抬起过的头上”,“照着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照着我们久久地住着/屈服在不正的权利下的城市和村庄”“照着我们的从很久以来/到处蠕动着痛苦的灵魂的田野、河流和山峦……”,阳光耀眼的光芒把人民“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刺醒城市与村庄,刺醒“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的田野、河流和山峦。“太阳”是光明的象征,太阳的光芒“带来了灿烂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预示民族抗争最终的胜利。相比最后才出现“我”的《太阳》,《向太阳》以“我”的情感走向和视野结构全诗,从“我”的角度展开情感抒发、愿望表达阐释人民的愿望,抒发大众的情感,诗歌的境界进一步提升。
北上沿途的苦难让艾青更加深入的了解人民的苦难,扭转了他前期诗中的个体忧郁,扩大了他的诗歌视野,沿途的诗歌创作形成了艾青诗歌中的两类常用意象,意象的审美叙述也影响了七月派诗人的自然意象叙述。
参考文献
[1]骆寒超.艾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周红兴.艾青的跋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3]艾青.艾青诗歌全编[M](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艾青.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5]艾青.艾青全集[M](第三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叶橹.诗歌艺术宝藏的发现与开掘——艾青诗歌研究综述[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
[7]王泽龙.走向融合与开放:艾青诗歌意象的艺术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1).
[8]申洁玲,亲情及其超越——论艾青诗歌中大地与太阳意象的双重内涵[J].江苏社会科学,1999(2).
[9]李蓉.土地、经验和想像——论中国现代诗歌“土地诗学”变迁的三种路向[J].文学评论,2016(6).
注 释
①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②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③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④周红兴《艾青的跋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⑤周红兴《艾青的跋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⑥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作者介绍:葛宏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