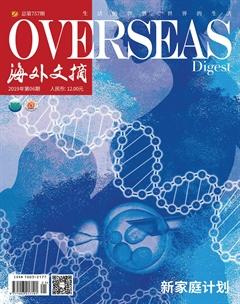用基因技术“计划”生育
爱丽丝·帕克
| 通过线粒体引入第三方的DNA |
当诺亚·舒尔曼在2016年圣诞节几天后出生时,他的父母克里斯特勒和埃文丝毫不为他的健康担心。因为孕期一切顺利,分娩也是如此。
但出生没几天,诺亚就开始出状况。他不吃东西,体重开始往下掉,还整天昏昏欲睡。几位儿科医生都劝舒尔曼夫妇放宽心,说他们可能对诺亚的症状过于敏感了,因为克里斯特勒是一名护士而埃文是一名医师助理——他们的表现在首次当父母的人群中很是典型。“我们都被归入神经质的父母那一类。”埃文说。
但当诺亚出现喘不上气的迹象时,惊慌失措的舒尔曼夫妇还是决定赶紧带他去看急诊。接下来的几个月,诺亚一直待在医院里。有一个月,他多次突发紧急状况,包括癫痫发作和心脏病发作,身体饱受摧残。在那之后舒尔曼夫妇得知,他们的儿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线粒体受到侵袭。
在全球范围内,每4000人中就有一人(在美国是每两万人中有一人)患线粒体疾病。人体的几乎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线粒体,作为人体的“分子电池”,它们为细胞的一切活动提供能量。线粒体也有自己的DNA,如果DNA变异,可能导致听力丧失、糖尿病、肌肉无力、癫痫发作和心脏病等病症。目前医学界对线粒体疾病束手无策,尚无法运用基因疗法来修复或改变受侵袭的线粒体基因。在出生3个月后,诺亚离开了人世。
就在他们尽量去接受儿子的死亡时,舒尔曼夫妇在情绪上再遭重创。医生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不要再想着生一个生理上健康的孩子了。线粒体变异的发生方式使得每次怀孕就像是玩生育轮盘赌,变量是他们的孩子受到的影响有多严重。“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语气平静地说我们不会再有一个亲生孩子了。”埃文说。医生建议他们考虑领养孩子或使用捐献的卵子来孕育孩子。
虽然也考察了这些选项,但他们仍不打算放弃拥有自己孩子的念头。“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要再生一个孩子,”克里斯特勒说,“还记得诺亚出生后,我们抱着他——那种感觉与众不同,是一种情感的联结与纽带。”
也就在那时,他们得知了线粒体替代疗法(MRT),这是一种很被看好的创新性生育疗法,可以让像舒尔曼夫妇这样的人生育健康的宝宝。包括使用来自供体的健康线粒体DNA来替代变异的线粒体,同时保持亲生父母的DNA完整无缺。传统的体外人工受孕(IVF),结合了来自父母二人的遗传物质,在这一疗法中再进一步,通过线粒体引入了来自第三方的少量DNA。
“我们正在跨越一道此前从未跨过去的障碍。”哥伦比亚大学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医学主任平野道雄博士说。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打算把线粒体替代疗法用在舒尔曼夫妇身上,“很显然,(用这种疗法孕育的)胚胎或生下的宝宝,生理上有3种不同的DNA来源,这种构想堪称独特或者说新颖。”

在年仅3 个月的儿子诺亚因线粒体疾病去世后,舒尔曼夫妇希望再生一个孩子。
像平野道雄这样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和舒尔曼夫妇这样的家庭更容易接受线粒体替代疗法。在他们眼里,这是一项被迫切需求的生育措施;而在伦理学家和立法者眼里,它则是一个棘手问题,事关如何界定为人父母的权利,以及永久性改写某人的遗传密码是否合乎道德等。目前基因疗法正被用来治疗癌症及其他一些疾病,以测试其疗效。因为在这种治疗中,改写遗传密码只影响到接受治疗者本人。但有些研究涉及修改卵子、精子或胚胎的遗传密码,这时科学家们面对的规则要严格得多,因为这些修改会一代代传递下去,而伦理学家和立法者还没作好准备来接受这种科技飞跃带来的社会影响。
| 新疗法拓宽了人类繁衍的边界 |
线粒体替代疗法被认为是基因编辑的一种形式。1978年,随着受孕的阵地从子宫转移到实验室——全球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体外人工受孕重新定义了生育。同样地,线粒体替代疗法——更广泛地说是它所代表的修改胚胎基因的新时代,拓宽了人类繁衍的边界。研究者表示,尽管引起了一些担忧,但该技术值得去追求,因为对线粒体的更广泛了解可以为不孕不育症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即便是不受线粒体疾病影响的人也可能从中受益。例如,有证据表明,重新激活线粒体可以改善衰老卵子的质量和功能,这使那些想方设法排出足够多的健康卵子,以便运用体外人工受孕法怀上孩子的大龄女性,成功受孕的几率增加了将近80%。
“我们真正改变了人们成功受孕并顺利生产的几率。”美国东北大学生物系主任乔纳森·蒂利说,他正是这个项目的开创者。
诺亚生病后,舒尔曼夫妇才了解了线粒体疾病以及这种疾病为何常常由母亲遗传给孩子。因为胚胎通常会保留卵子的線粒体,同时却只保留精子的一小部分线粒体。诺亚一被确诊,克里斯特勒就去检测了基因,发现自己70%至80%的线粒体发生了变异,尽管她没出现任何病症。
每个卵子含有数十万至上百万个线粒体——没有人真正计算过到底有多少——研究人员最近才发现,每个线粒体在细胞中的功能各异。虽然细胞的长链DNA被紧紧地缠绕在其细胞核中,但线粒体作为一种存在于细胞内的独立细胞器,自身有着由37个基因构成的DNA。作用于线粒体的变异次数和类型会对细胞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可预测的症状。
“对于患有线粒体疾病的女性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知道她们的孩子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生殖生物学教授玛丽·赫伯特说,她正在领导开展一个项目,在受疾病侵袭的人群中测试线粒体替代疗法。“一名女性会产生变异负荷波动很大的卵子,所以她可能怀上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也可能怀上一个不健康的孩子,这很难说。”
控制这种不可预测性的一种方法是体外人工受孕,并进行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GD),这通常用于多种遗传性疾病的检测,包括唐氏综合症和肌肉萎缩症。在这些病症的治疗中,医学专家可从一个几天大的胚胎中提取出一颗细胞,分析其DNA携带的变异量。同样的策略可应用于线粒体DNA,医生只会把那些线粒体的变异量少于18%到20%的胚胎植入其母体内,他们认为这种变异量不会导致衰弱症状。PGD可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做,但在美国,这种诊断只能出于研究目的,所以舒尔曼夫妇只得求助于国外的PGD项目,以进行基因筛查。
PGD只能降低下一代患线粒体疾病的风险,而线粒体替代疗法由于引入了捐献者的健康线粒体,可以消除风险,所以舒尔曼夫妇也决定尝试线粒体替代疗法——至少尽可能多地尝试美国法律目前允许的步骤。不仅美国联邦出台政策,阻止科学家利用政府资金进行人类胚胎研究(理由是这些研究会导致胚胎受到伤害或被销毁),国会甚至还禁止美国药监局接受考虑批准这一程序的申请——后者负责对包括线粒体替代疗法等在内的新疗法作出评估。这就是平野道雄为其研究拉来私人赞助的原因,舒尔曼夫妇和其他5对夫妇加入了他的研究。可即便如此,他也只能实施线粒体替代疗法,不能将胚胎植入母体进行妊娠。在政策变化之前,只能先将它们冷冻起来。“目前我们暂停了研究,”他说,“在获得批准之前,我们没法往前一步。”
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家迪特·埃格利是在卵子内操控DNA的行家里手,当前他正在进行关于基因交换的研究,将含有健康线粒体的捐赠卵子中的DNA移除,代之以女性线粒体疾病患者的卵核DNA。由此产生的卵子包含女患者的DNA和捐献者的非变异线粒体,它可以与父亲的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并产下一个几乎不会患线粒体疾病的孩子。

|“他们担心我们正在定制婴儿”|
正在等待捐献的卵子,以运用线粒体替代疗法创造胚胎的舒尔曼夫妇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忧心忡忡,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讲,这样创造出的胚胎不同于将父母的卵子和精子相结合而产生的胚胎。改变卵子、精子或胚胎中的基因,让准父母们挑拣他们看重并希望孩子具备的特征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从眼睛的颜色或身高等物理特征到更复杂的特征,如智力或运动能力。但舒尔曼夫妇希望他们参与的那类研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此种基因干涉的方式其实是在普度众生,并真正了解线粒体替代疗法。
“人们反对它的理由千奇百怪,”埃文说,“他们担心我们正在定制婴儿,但人们不理解的是,这不是在创造我们想要的东西,而纯粹是为了消除危及人们生命的疾病。”
对于受线粒体疾病困扰的家庭来说,这是唯一的道德使命——运用任何一种可行方案产下自己的健康孩子的权利。线粒体疾病患者、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心理学家谢莉·贝弗利表示,她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即便她像哥哥和母亲那样因为此病过早离世,她的生命也会得到延续。“我非常想要一个遗传了我和丈夫基因的孩子,因为就算有一天我遭遇不测,我也希望丈夫能看着我们的孩子想:‘你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你的眼睛像她的。”她说,“我们没想着要定制婴儿,也不想扮演上帝,我们只想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消除对很多人来说都堪称致命的疾病,而非定制婴儿。”——埃文·舒尔曼
贝弗利夫妇尝试过PGD,但经过5个周期的体外人工受孕后,他们得知他们的胚胎因受到线粒体变异的严重影响,已经不适合转移到母体内进行妊娠。“我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她说,“线粒体替代疗法是我们降低风险的唯一选择。”
与美国一样,线粒体替代疗法在澳大利亚尚未获得批准。然而在去年夏天,该国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放行线粒体替代疗法,听证会还邀请受线粒体疾病侵扰的家庭前来作为他们的例证。听证会后,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表示支持线粒体替代疗法的研究,前提条件是它被用来帮助像贝弗利这样的人怀上一个健康宝宝。如果立法通过,澳大利亚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批准线粒体替代疗法的国家。2015年,英国成为第一个批准此种疗法的国家,去年该国研究人员开始使用线粒体替代疗法进行一项研究,以帮助遭线粒体疾病侵袭的两个人怀上健康宝宝。包括赫伯特在内的研究团队正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研究,以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并确保研究结果在科技出版物中准确呈现,以供医生进行参考。目前他们的研究对象仅限于英国本土夫妇,这有便于在婴儿出生后对他们给予密切关注。按照计划,以后其他国家的夫妇也会成为研究对象。
| 修改胚胎基因引发公众担忧 |
他们保持谨慎是有原因的。2016年,纽约市不孕不育专家约翰·张(音译)博士发布报告称,首个运用线粒体替代疗法孕育的婴儿在墨西哥出生,是一名男孩。此后陆续有此类婴儿诞生,包括在乌克兰出生的。但由于这些都是个案研究,该程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存在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技术人员到底能多精确地从微小的卵子中去除受线粒体疾病影响的母体核DNA,以及她变异的线粒体DNA有多少可能被无意间带到供体卵子中。张在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表示,在婴儿的不同组织中,这一可能性介于“检测不到”到9%之间。约翰·张说他打算定期追踪这名男孩,直到他18岁,以评估捐献的线粒体对其健康有何影响(如果有的话)。
参与平野道雄研究的舒尔曼夫妇和其他夫妇意识到,为了怀上孩子,必须对美国法律作出修改。在这个国家,研究胚胎的任何尝试都会陷入关于堕胎的争论,争论胚胎是否应该被认为是有生命权的人,即他们是否应该被当作试验对象,考虑到这些,成功修改法律的希望很是渺茫。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禁止任何涉及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比如线粒体替代疗法,都是对疾病新疗法研发的限制和阻碍。但他们也承认,在美国之外,一些动作快的科学家已经在对胚胎进行永久性的基因修改,这就走得太远了,因为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些干预措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018年11月,一位中国生物工程师宣布,他使用一种功能强大却未经测试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对一对双胞胎女孩的胚胎进行基因改造,使她们对艾滋病天然具有抵抗力。消息公布后,科学界和公众为之震惊。CRISPR的开发人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编辑人类基因组的长期影响,并重申应该暂停修改过基因的人类胚胎移入子宫内孕育的研究。
即使在英國,线粒体替代疗法也只能在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使用。在决定使用之前,政府会邀请公众讨论该疗法的利弊,并且像澳大利亚那样,听一听受线粒体疾病侵扰的家庭怎么说。它也不会批准要求执行该程序的任何申请,而是仅仅向纽卡斯尔大学的一个小组发放许可证,这个小组将在研究中收集数据并报告结果,以便医学界从中学习。
美国东北大学生物系主任乔纳森·蒂利支持这种逐步的、有条不紊的方法。2012年,蒂利粉碎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关于女性生育能力的真理——女性一生中排出的卵子数量在刚出生时便已确定,她们不会再产生新的卵子。蒂利则发现了一种造卵干细胞,或者说是成熟卵子的“前身”,在实验室条件下确实可以产生新的卵子。如此,从理论上讲,女性一生中各个年龄段都可以产生新的卵子。
光有足够的卵子还不行,它们还得品质优良。蒂利发现,线粒体对产生有活力的卵子至关重要,蒂利对于小鼠的早期研究以及在实验室中对人体细胞的研究表明,使用激素激活这些线粒体可以恢复卵子功能。用动物作试验,培育成胚胎后能产下健康的小狗。
对于一些伦理学家来说,蒂利的研究会在生育需求方面导致“滑坡效应”,因为如果卵巢能够继续产生新的、可受精怀孕的卵子,势必会导致女性更年期的推迟。不过他坚称:“我们不是要让一颗40岁的卵子看起来像20岁,而是要确保,在我们竭尽所能帮助那些不孕的女性之后,这颗40岁的卵子能够自行受精,最终怀孕产子。”
他还在等待更多的研究结果,以观察这些影响是否也会出现在人的身上。但他和舒尔曼夫妇都相信,如果能让人们享受到天伦之乐,花时间等待也是值得的。克里斯特勒和埃文希望继续生孩子。诺亚在世上走的这一遭,以及他们参与的试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会让他们自己受益,也会让其他人受益。想到这些,他们便深觉欣慰。“即使现在我们还没受益,但仍希望终有一天它会让线粒体疾病患者受益。”克里斯特勒说道。